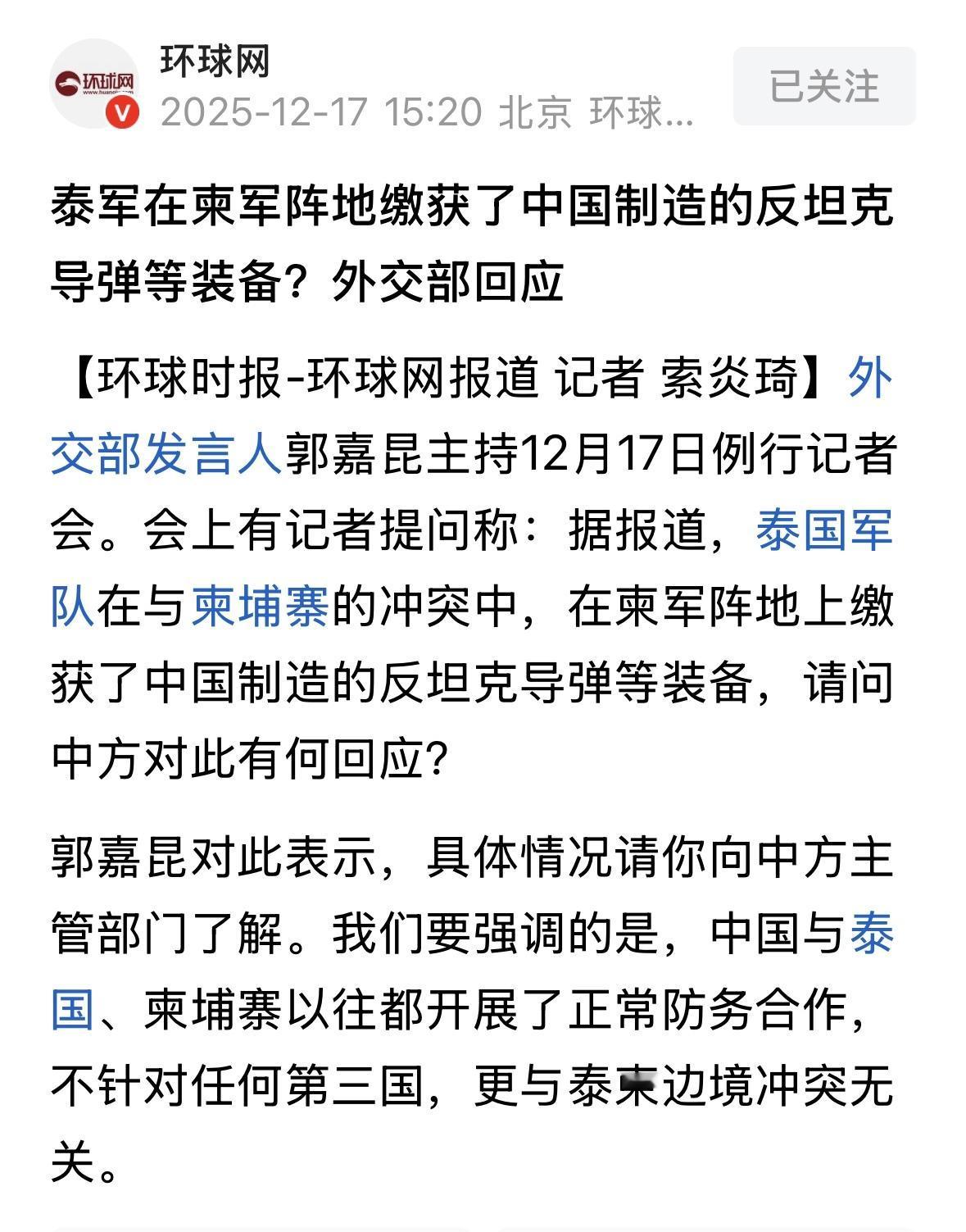我们生产队每年春夏种瓜地几十亩地,一般都包给队里一个王姓光棍汉,这人虽然是老光棍,但在农村做什么象什么,他不仅种得一手好瓜,还会修农机、编筐篓,连给牲口看病都有一手。村里人都说老王是个"全挂子"本事,可就是四十多岁了还没成家,住在村头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灶台上永远只有一副碗筷。 队里那几十亩瓜地,每年春夏都交给老王。 不是因为他光棍闲,是他手里的活计拿得出手:瓜苗破土时他蹲在地头看芽尖,农机咔嗒响他摸两下就知道哪颗螺丝松,连张婶家下崽的老母猪,都是他捏着耳朵灌药救回来的。 村里人喊他“全挂子”,说他啥都会,可谁也没提过,他村头那间土坯房的灶台上,搪瓷碗和竹筷永远摆成一条线,像早就量好了距离,多一分都嫌挤。 那年春上,小李家的黄牛不吃草,耷拉着脑袋淌口水,兽医站的人还在路上,小李他爹急得直搓手,最后还是往村头跑——老王正蹲在门槛上编筐,柳条在他手里绕成圈,听见动静头也没抬:“牛槽边的砖缝里,撒把灶灰。” 傍晚小李他娘端着碗热汤面往村头走,土坯房的烟囱刚冒完烟,门没关严,她扒着门缝往里瞅——老王正对着灶台发呆,手里拿着那双竹筷,轻轻摩挲着碗沿,像是在数上面的豁口。 “王大哥,趁热吃。”她把碗搁灶台上,原来的搪瓷碗被往里推了推,两只碗并排着,倒像是早就该在那儿。 老王手顿了顿,接过筷子时指节有点红:“……谢了。” 你说,一个把日子过成“全挂子”的人,心里会不会也藏着个缺口? 小李他娘看着那两只并排的碗,忽然觉得,老王不是不需要,只是等了太久,忘了怎么伸手要。 后来小李他娘才跟人说,那天老王吃着面,忽然叹了句:“年轻时也想过,灶台上摆两副碗筷,可那会儿穷,人家姑娘等不起。” 原来不是不想,是怕了——怕自己这双手能侍弄好瓜苗,却侍弄不好日子;怕刚摆上的碗筷,转眼又只剩一副。 那副碗筷就像他的界碑,提醒自己别越线,可他给张婶家修农机时,顺手把她家松了的篱笆也扎好了;给瓜地浇水时,总多绕一段路,把村西头的老井也淘干净——这些事他从不提,就像灶台上的碗筷,沉默着,却藏着温度。 现在村里人路过土坯房,会喊一嗓子:“王大哥,新摘的豆角吃不吃?” 他还是蹲在门口编筐,头也不抬,手里的柳条却慢了半拍:“……给我留点嫩的。” 灶台上的搪瓷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个蓝花碗,是小李他娘落下的,他没还,也没摆回原来的位置,就那么歪着,像在等个人来,把它摆端正。 日子嘛,有时候就像老王种的瓜,看着皮糙,里头甜着呢。
我们生产队每年春夏种瓜地几十亩地,一般都包给队里一个王姓光棍汉,这人虽然是老光棍
凯语乐天派
2025-12-19 13:31:41
0
阅读: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