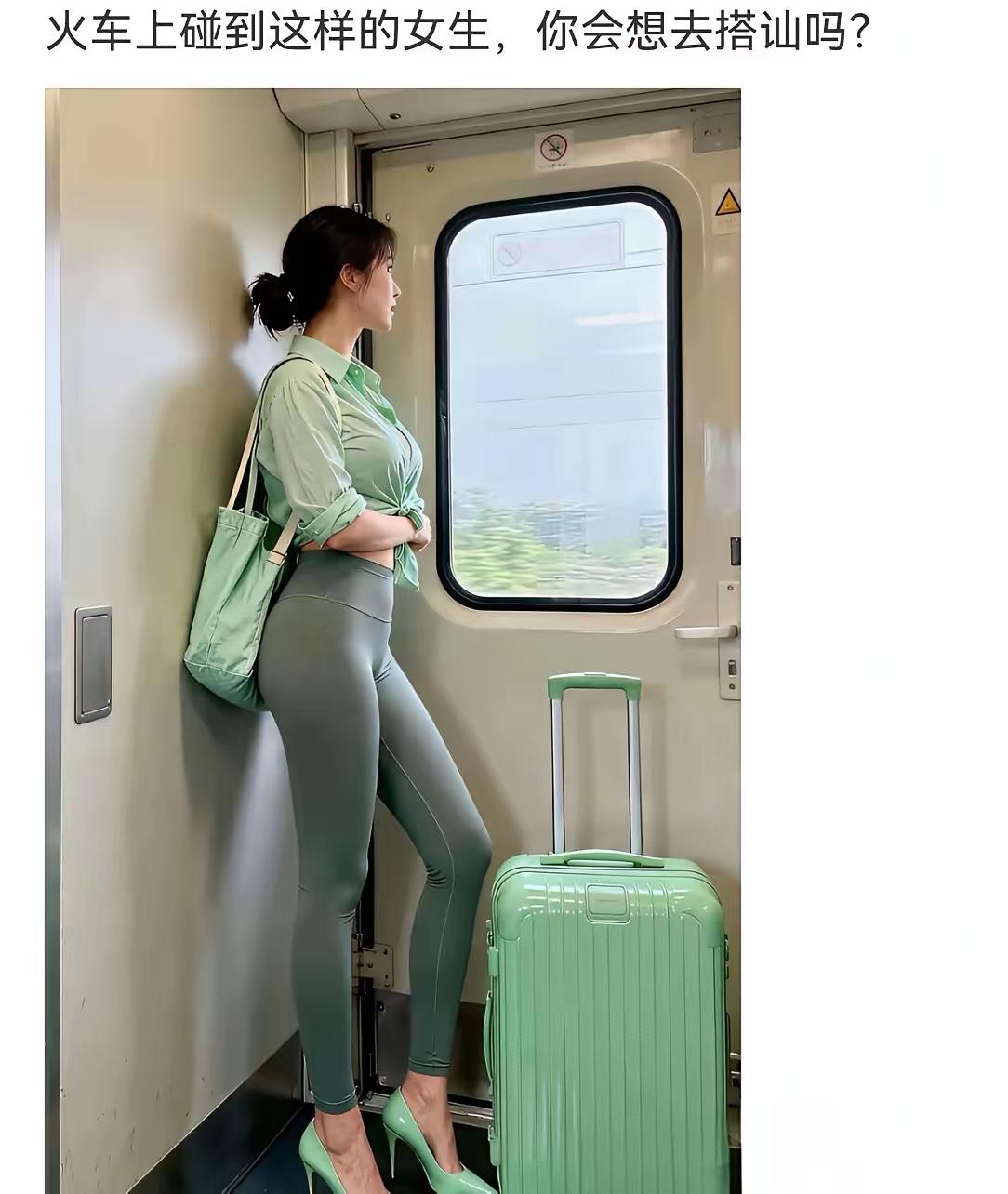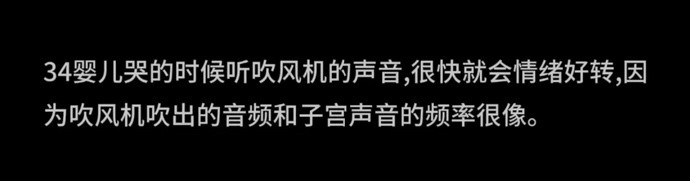解放前的一天,我们村有个地主门前来了一要饭的叫花子,人几天都没讨到吃喝,已经饿晕了。地主家的长工发现他时,人蜷在石狮子旁边,脸蜡黄得像秋收后的稻秆,嘴唇裂着血口子,怀里还紧紧揣着个破布包。 那天日头毒得很,晒得土路直冒烟。 我蹲在地主家石狮子旁歇脚,就瞅见墙根下蜷着个人。 脸黄得像晒焦的苞米叶子,嘴唇裂得能看见红肉,怀里还死死搂着个破布包,一动也不动。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饿晕过去了——那年头,饿死在路边的叫花子,不算稀奇。 我是地主家的长工,姓李,村里人都叫我老李。 地主王老爷平时话不多,鞭子却比谁都狠,我们这些下力人见了他,大气不敢喘一口。 可那天我鬼使神差地,还是跑去后院禀报了。 王老爷正摇着蒲扇喝茶,听我说完,眼皮都没抬:“拖到乱葬岗去,别脏了门口的地。” 我脚像钉在地上,盯着他茶杯里飘着的龙井茶叶——去年新贡的,听说一两银子才能换一小撮。 “老爷,”我声音发颤,“他怀里揣着个布包,攥得紧着呢,说不定是……” 王老爷这才放下茶杯,斜了我一眼:“哦?什么宝贝?” 我没敢再说,转身回了前院。 蹲在叫花子旁边,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解开他勒得死紧的腰带,想看看那布包到底藏着啥。 布包三层裹着,解开最后一层时,我愣住了——里面根本不是什么金银细软,是半块干硬的麦饼,还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梳辫子的女人和一个穿开裆裤的娃娃。 叫花子忽然哼唧了一声,眼睛没睁开,手却摸索着抓住我的胳膊,气若游丝:“水……水……”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跑去厨房舀了瓢水,掰开他的嘴一点点喂进去。 就在这时,王老爷背着手过来了,看见我手里的照片,突然停下脚步。 他蹲下身,拿过照片仔细瞅了瞅,又看了看叫花子干裂的嘴唇,突然说了句:“老李,把他抬到柴房去,找个大夫来。” 我差点把瓢掉地上——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 叫花子醒过来是第二天晌午。 他知道是王老爷救了他,挣扎着要下床磕头,被王老爷拦住了。 “你怀里的照片,”王老爷指了指桌上的布包,“是你婆娘娃?” 叫花子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家乡遭了灾,俺带着她们逃荒,路上失散了……俺想留着麦饼,万一哪天找着她们了呢……” 王老爷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个小布袋子,塞到叫花子手里:“这里有点碎银子,你拿着,去找她们吧。” 叫花子哭得更凶了,跪在地上砰砰磕头,嘴里喊着“大恩人”。 王老爷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停住,背对着我们说:“这年头,活着都不容易。” 那天下午,叫花子揣着银子和布包走了,一步三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王老爷年轻时候也逃过荒,他婆娘就是那时候病死在路上的。 谁能想到呢?平时对我们狠巴巴的地主,也有过这样的伤心事。 那半块麦饼和一张旧照片,竟让两个身份天差地别的人,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有了一瞬间的共情。 这事过去没多久,王老爷还是那个王老爷,该收租收租,该打人打人。 但我心里看他,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藏着点不为人知的东西,就像那个叫花子怀里的布包,你不打开看看,永远不知道里面是苦是甜。 那天的阳光照在石狮子上,暖烘烘的,可我知道,这世道的冷,不是一点阳光就能焐热的。 但好歹,还有人愿意给那点暖不是?
许愿池的王八看见都得连夜跑[捂脸哭]
【12评论】【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