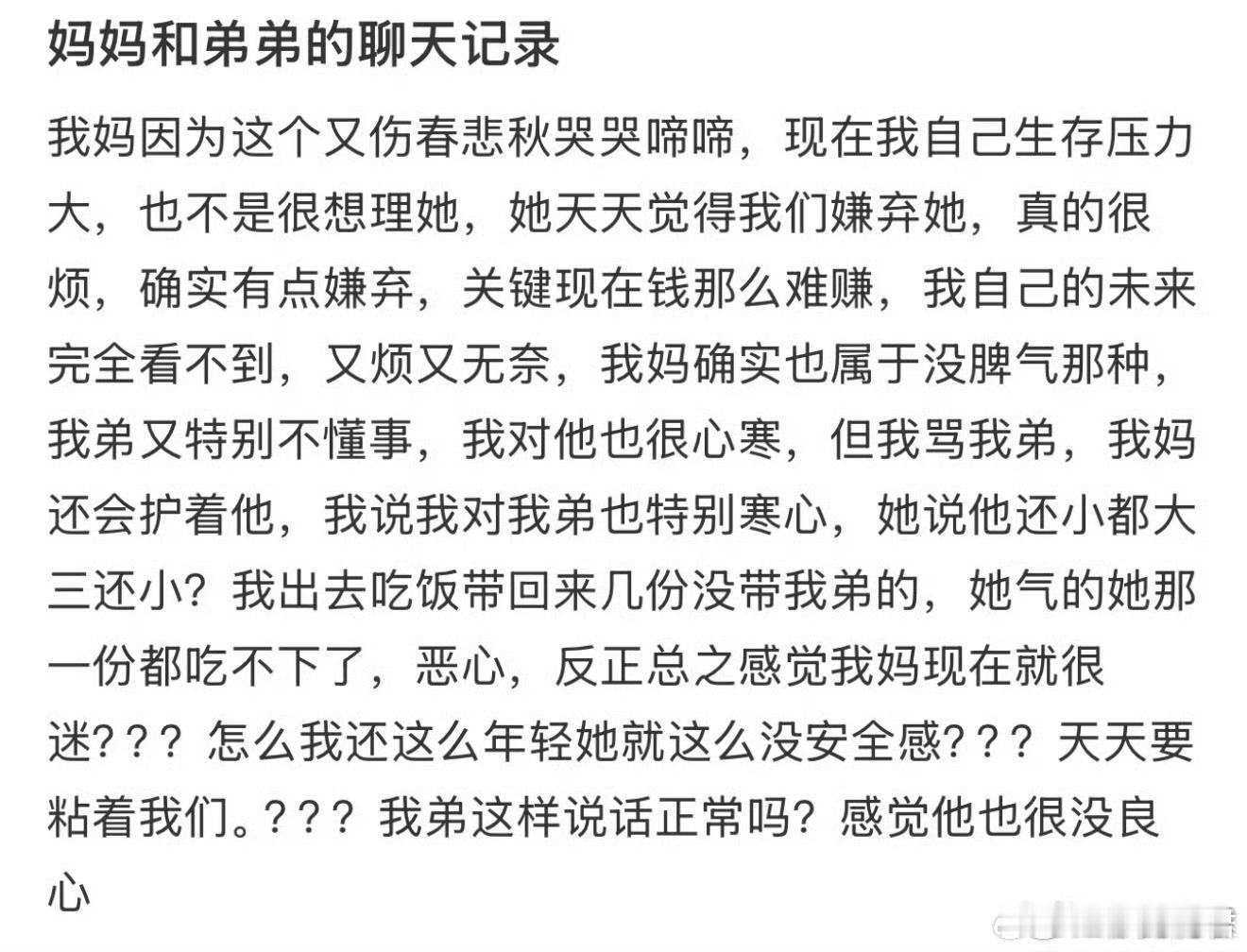我弟弟,已经两年没干活了,之前上班时好像攒了两三万块钱。一个人在外头住,城中村每月房租五百。为了省生活费,买特别便宜的菜和肉。第一次发现他不对劲,是去年冬天我顺路去看他。城中村的巷子像被冻住的墨汁,黑黢黢地蜿蜒,墙根堆着冻硬的垃圾,风卷着塑料袋打在我裤腿上。他住三楼,楼梯扶手积着层灰,我攥着扶手往上爬,每走一步都能听见木板在脚下呻吟,像谁在暗处叹气。 我弟两年没正经干活了。 上次见他领工资还是2021年冬天,揣着三万块现金,在面馆里数给我看,说要攒着娶媳妇——现在那笔钱大概还剩多少?他从不提,我也不敢问。 他一个人窝在城中村三楼,月租五百的单间。我去过三次,每次楼梯口都堆着邻居扔的旧家具,这次是张破沙发,弹簧从烂布里戳出来,像只断了腿的狗。 去年冬天顺路去看他,下午四点多,巷子就暗透了。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露出里面的红砖,风裹着煤炉味和油烟味撞过来,眼睛涩得发疼。 三楼的门锁是坏的,虚掩着。我推开门时,他正对着墙发呆,背影比上次瘦了一圈,旧毛衣后领磨出了毛边,像只被雨淋湿的鸟。 “姐?”他猛地回头,手忙脚乱把桌上的东西往抽屉塞——我看清了,是几张画纸,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小人,举着剑,旁边写着“奥特曼打怪兽”。 小时候他总在作业本背面画这个,被老师撕了本子,躲在楼梯间哭,还是我把自己的图画本给他。 “吃饭没?”我假装没看见,放下手里的菜——超市打折的五花肉,冻得邦邦硬,还有两把蔫了的上海青。 “刚吃过。”他指了指桌角,半碗冷米饭,旁边是个豁了口的搪瓷碗,里面盛着酱油水,飘着两片没熟的白菜叶。 我去厨房烧水,锅沿结着层黑垢,水龙头拧开,铁锈味的水哗哗流,盆底沉着泥沙。他跟进来,靠在门框上,脚尖碾着地板缝:“姐,你别忙了,我这儿挺好的。” “好?”我关了水龙头,转身看他,“你衣柜顶上那箱泡面,过期三个月了。” 他突然红了眼,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诊断书,字小得看不清,只认得“中度抑郁”几个字。“去年在厂里,我画板报被主管骂‘不务正业’,说我画那些没用的东西影响产量,扣了我半个月工资……” 原来他不是懒,是怕了。怕自己喜欢的事被人踩在脚下,怕连那点可怜的念想都保不住。 你说人为什么会把喜欢的东西藏起来呢?是怕被说不值钱,还是怕连自己都养不活? 我没提工作的事,只是把五花肉放进冰箱——那冰箱嗡嗡响,门封条都掉了一截,得用夹子夹着才能关紧。“明天我带饺子过来,你不是爱吃韭菜馅的?” 他没说话,却伸手碰了碰我带来的画纸——我在超市顺手买的,A4纸,一包十块钱。 第二天去时,他把画纸铺在桌上,小人旁边多了个扎马尾的女孩,举着个碗,碗里画着个歪歪扭扭的“饺”字。 现在他还是没找工作,但每天会画两小时画,画完拍给我看。我从不问“什么时候上班”,只说“这个小人的剑画得比昨天亮”。 上周路过城中村,巷子的雪化了,墙根的垃圾被扫到一边,露出小块青石板。三楼的窗户开着条缝,飘出点泡面味——这次是新日期的,香菇炖鸡味,他以前最不爱吃的那种。 原来有些时候,能好好吃一碗泡面,也是一种往前走的勇气。
我弟弟,已经两年没干活了,之前上班时好像攒了两三万块钱。一个人在外头住,城中村每
凯语乐天派
2025-12-19 13:31:41
0
阅读: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