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姐回村就带一盒月饼、两盒茶叶,没给公公买酒,公公一整天闷闷不乐,吃饭时大姑姐还问“爸,你咋不高兴”。公公手里攥着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半天没夹一口菜。听见大姑姐问,他头也没抬,只含糊地“嗯”了一声,筷子在碗沿上轻轻磕了两下,像是有心事没说出口。 大姑姐回村那天,日头斜斜地挂在西厢房檐角,晒得院门口的老槐树影子缩成一团。 她手里拎着个红布包,进门就喊“爸,我回来了”,包里露出半盒广式月饼,两盒茉莉花茶——都是城里时兴的玩意儿,却独独少了公公酒柜里常空着的那个二锅头瓶子。 饭桌上,搪瓷盘里的炒青菜蔫蔫的,腊肉片泛着油光,公公面前的酒杯空着,像个张着嘴的哑葫芦。 大姑姐把月饼往他跟前推了推,“爸,尝尝这个,蛋黄的,甜而不腻”,他没接,筷子在碗里扒拉着白米饭,米粒黏在筷子上,又簌簌落回碗里,半天没夹一口菜。 “爸,你咋不高兴?”大姑姐终于察觉到不对劲,夹菜的手停在半空,眼里带着点困惑。 公公这才抬起头,眼角的皱纹被灯光照得像老树皮的纹路,他张了张嘴,想说啥,又把话咽了回去,只含糊地“嗯”了一声,筷子在碗沿上轻轻磕了两下,瓷碗发出“叮”的一声轻响,惊得桌角的茶罐都晃了晃。 其实大姑姐走之前在超市转了三圈,二锅头货架前站了好久——她记得爸年轻时顿顿离不开酒,可上个月打电话,妈说他血压高,医生不让喝了,她怕买了反而让爸忍不住,才换成了茶叶。 只是这些话,她没来得及说,或者说,她以为爸会懂。 公公攥着筷子的手背上,青筋像蚯蚓似的鼓着,他不是气女儿没买酒,是气自己这身子骨不争气——连女儿想孝顺都得偷偷摸摸,连句“我想喝口酒”都不敢说出口,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那空酒杯就那么戳在桌上,像在提醒他,自己已经老得连喜欢什么都要藏着掖着了。 他想起去年此时,大姑姐也是这样拎着酒回来,爷俩坐在门槛上,就着一碟茴香豆,他喝一口,她抢过去抿一下,呛得直咳嗽,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丫头片子,这酒哪是你喝的”——那样的日子,好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轻飘飘地,就没影了。 可他怎么说得出口呢?总不能告诉女儿,爸不是不高兴你买了茶叶,是不高兴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大大方方地跟你喝一杯酒吧? 这顿饭吃得像嚼蜡,大姑姐几次想开口,都被公公低头扒饭的动作堵了回去。 饭后,她把茶叶拆开,泡了杯给公公,茶水上飘着几朵茉莉花,香得有点呛人,公公喝了一口,说“好茶”,声音却哑哑的。 夜里,公公躺在床上,听见大姑姐在东厢房跟妈小声说“妈,爸是不是嫌我没买酒?”,妈叹了口气,“你爸他呀,是怕你知道他想喝酒,又担心他身体”。 他翻了个身,听见窗外的虫鸣一声接一声,突然觉得,明天早上,或许该跟女儿说一句“其实,少喝点没事”。 第二天一早,大姑姐要走了,红布包空了,月饼盒敞着盖,剩了半块蛋黄的。 公公从床底下摸出个小酒壶,塞到她手里,“这个你拿着,城里不好买,下次回来,陪爸喝一小口——就一小口”。 酒壶是粗陶的,带着他手心的温度,大姑姐愣了愣,突然笑了,眼里亮晶晶的,像落了星星。
大姑姐回村就带一盒月饼、两盒茶叶,没给公公买酒,公公一整天闷闷不乐,吃饭时大姑姐
勇敢的风铃说史
2025-12-19 11:20:58
0
阅读: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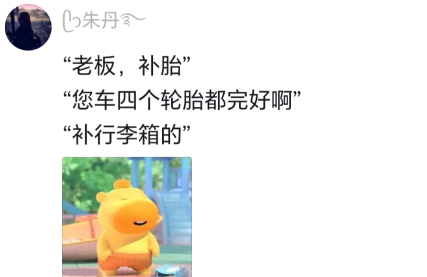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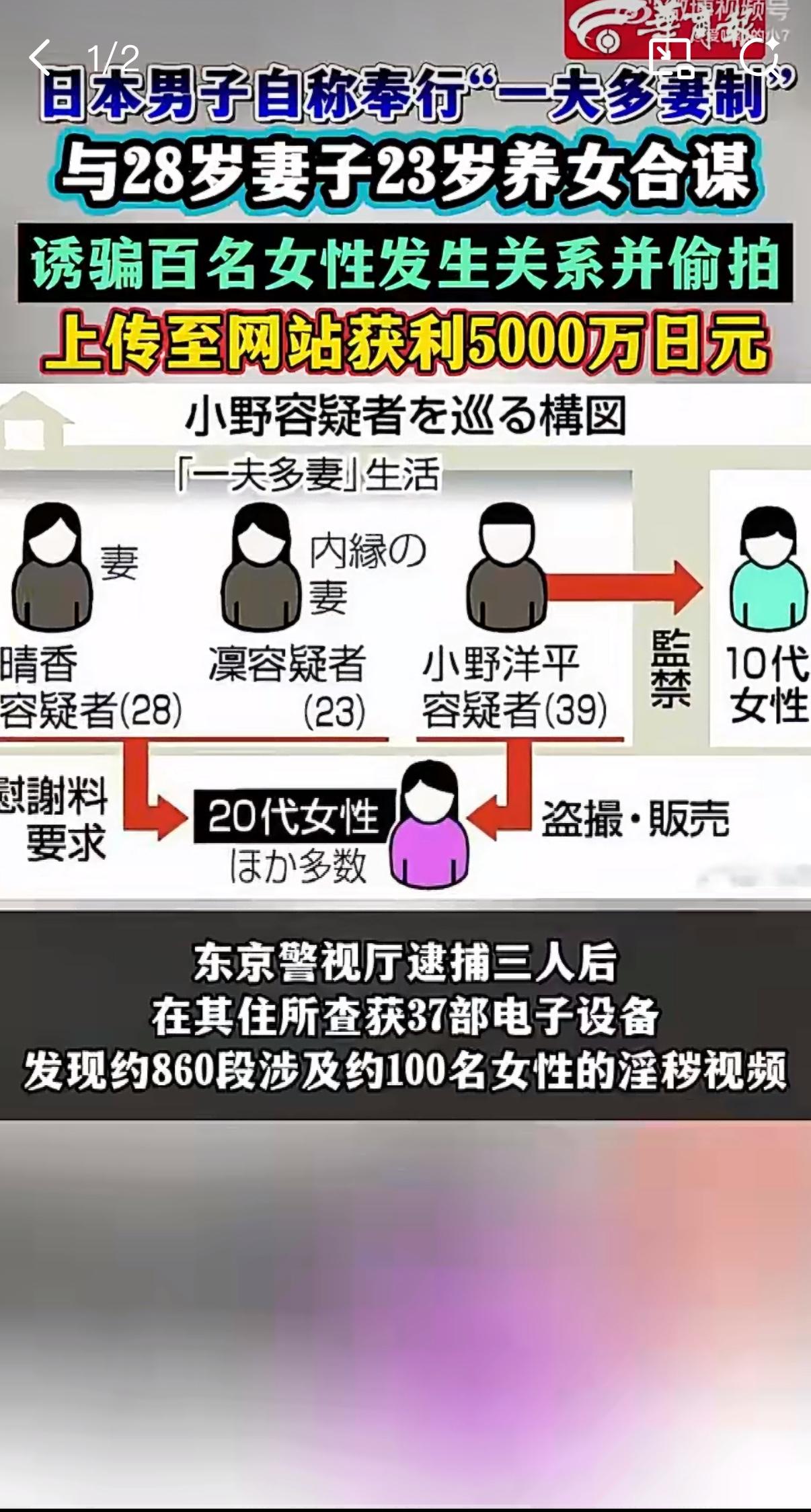


一锤定音
狗屁不通,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