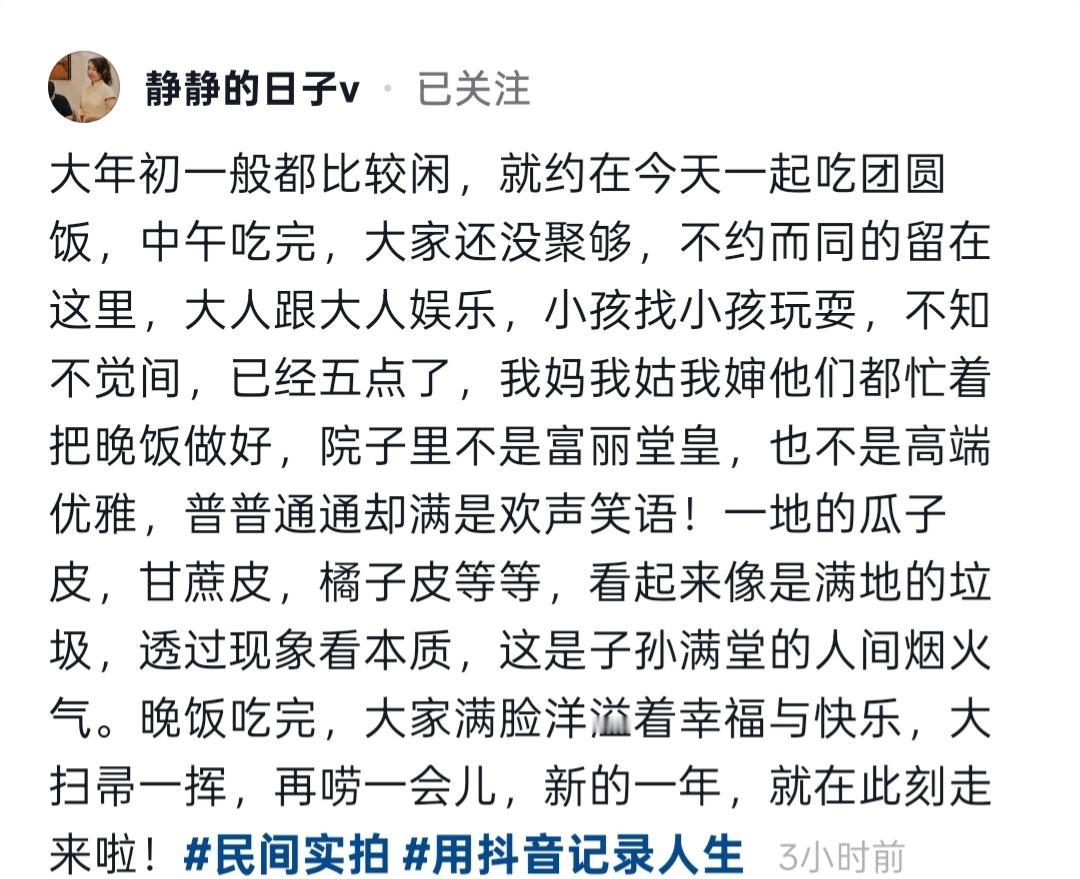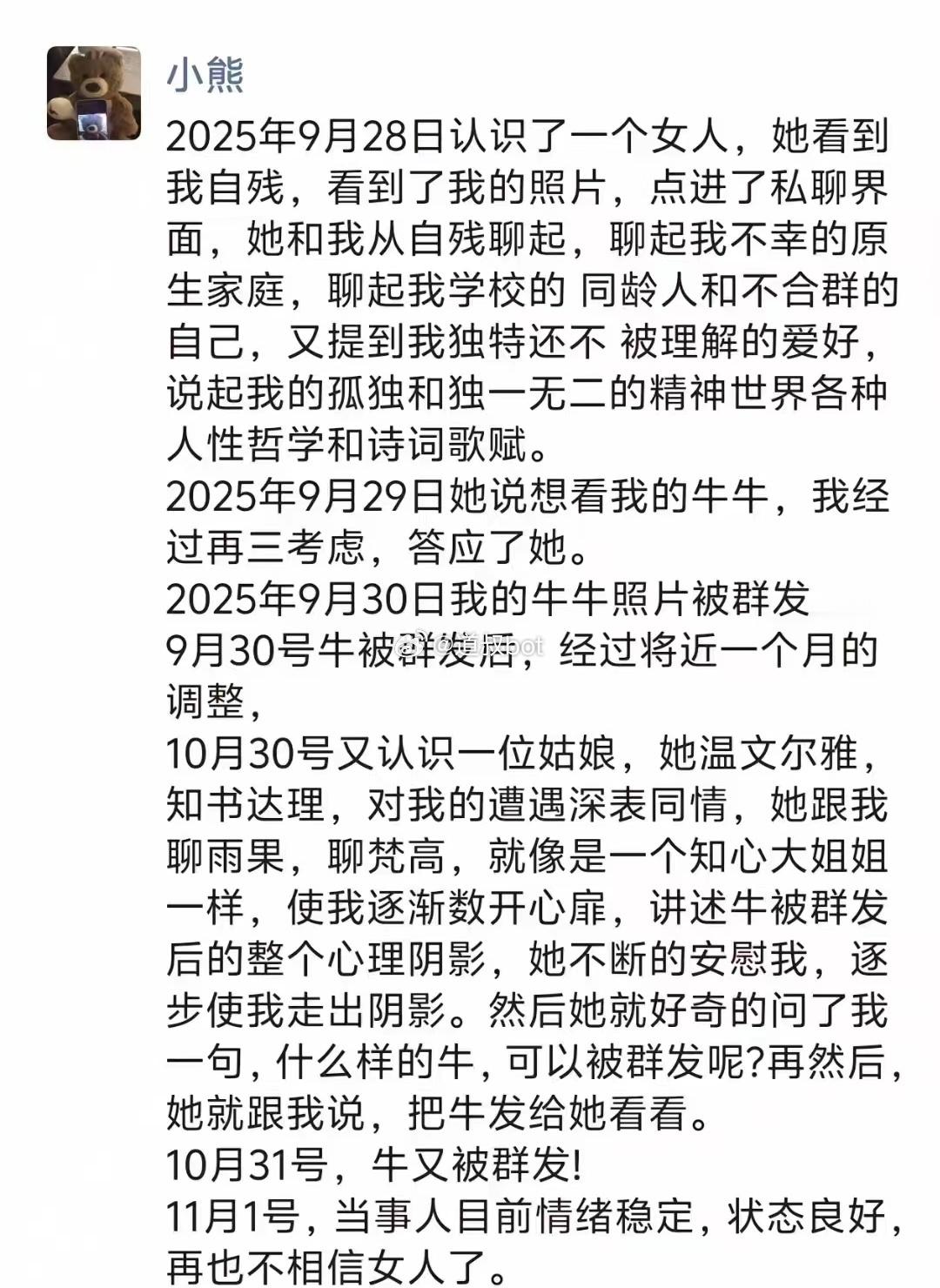我堂哥是地陪,他说晚上露营的时候,多的是自愿钻男人帐篷的女人。
我不信。
一个个有钱又漂亮的女人,能看得上地陪这样的粗人?
后来,我陪堂哥带了一次团。
我信了。
那是个深秋的团,去西北的戈壁。团里有个穿驼色大衣的女人,话少,总坐在大巴最后一排,看窗外的胡杨。
堂哥跟我说,她是个做外贸的,每年都出来走几趟,就爱往没人的地方钻。
那天晚上扎营在戈壁滩,风大得能把帐篷吹得哗哗响。我和堂哥在篝火边烤土豆,她裹着大衣走过来,蹲在火边,手拢着,像只怕冷的猫。
她问我,你哥是不是跟你说过,晚上会有女人钻他帐篷?
我愣了一下,点头。
她笑了,说,我钻过。
我手里的土豆差点掉在地上。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火里跳动的光,说,那年我刚离婚,公司也黄了,揣着最后一点钱出来散心。在戈壁上走了三天,手机没信号,人也快疯了。那天晚上风特别大,我一个人在帐篷里哭,哭到没力气,就听见外面有人敲帐篷,是你哥。他说,妹子,出来烤烤火吧,风大,别冻着。
我出去了,就坐在篝火边,跟他说了一整夜的话。他没劝我,也没说什么大道理,就听着,偶尔递过来一块烤红薯。
后来我就钻他帐篷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太怕一个人待着了。戈壁滩的黑,能把人吞了。
我看着她,火光照在她脸上,没有妆,眼角有细纹,却很亮。
她又说,你哥是个好人。他知道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就给了我一点暖。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暖,是有人在你快沉下去的时候,伸手拉了你一把的暖。
那天晚上,我没再回自己的帐篷,就在堂哥的帐篷边,裹着大衣坐了一夜。风还是很大,篝火也灭了,但我不觉得冷。
第二天早上,她走了,没跟任何人告别,只在堂哥的帐篷外留了一包烟,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
团里的人都在议论,说她肯定跟你哥有一腿。堂哥只是笑,把烟揣进兜里,说,人家是个好女人。
我看着堂哥的背影,突然明白,他说的那些“自愿钻帐篷的女人”,其实不是什么轻浮的人。她们只是在某个深夜,太需要一点依靠,太怕一个人面对无边的黑暗。
而堂哥,就是那个在黑夜里,愿意给她们递一块烤红薯的人。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穿驼色大衣的女人,也没再陪堂哥带过团。
只是每次想起戈壁滩的风,和火里跳动的光,我都会想起她蹲在火边的样子,像一只怕冷的猫,却又在黑夜里,找到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