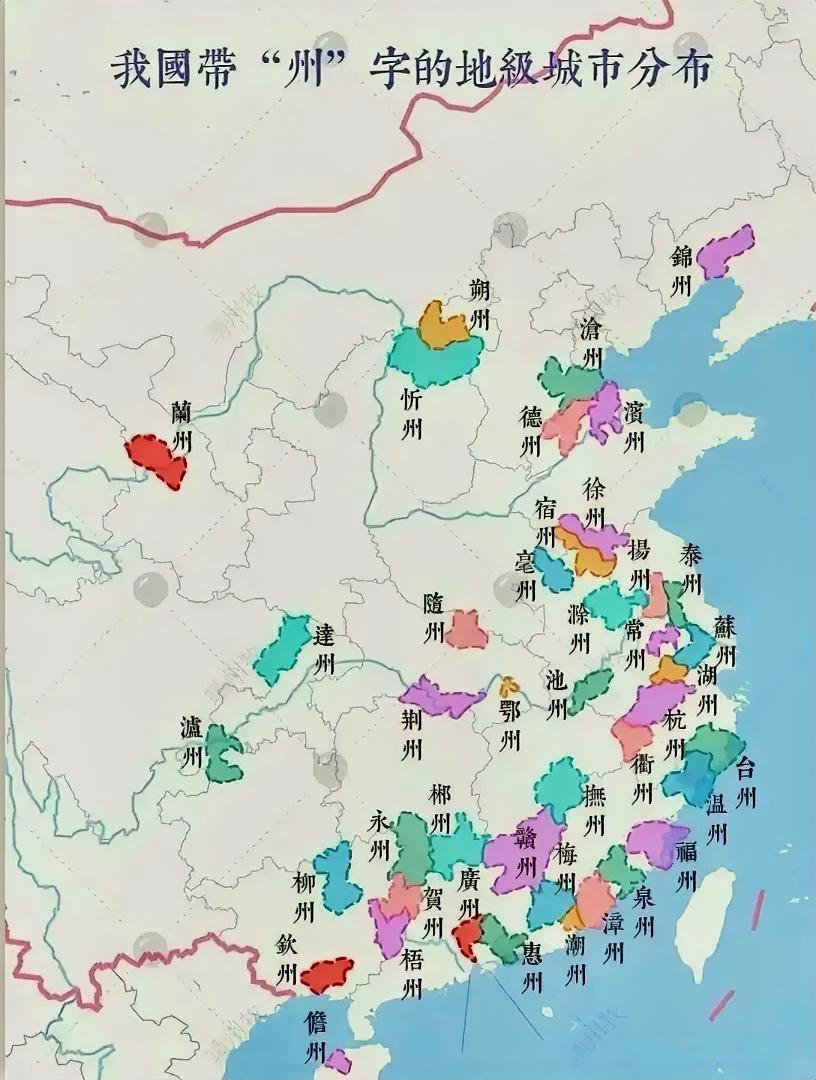1987年“气功大师”严新声称,他用气功灭了大兴安岭的火灾,其声名瞬间如日中天。盛名之下严新去清华应聘教授,清华校长却说:“聘书就在抽屉里,你用气功将盖章的图章取出来,我就批准你的教授申请。” 1987年,大兴安岭的山火把北方夜空烧得发红,全国都在看前线扑火的进展,北京西单的一角却突然贴出一张海报,说气功大师严新要在中国剧院发功,远程帮忙灭火,落款醒目写着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雨水把纸边淋得卷起,围观的人仍举着相机拍照,期待奇迹发生。 严新本是四川江油的普通青年,早年读卫校,后来在中医学校教书,赶上武打片和气功潮,他把所谓外气和治病挂钩,很快在民间积累起一批信徒。 大兴安岭起火后,三省力量上山扑救,火势在人工增雨和天气变化作用下转入可控,而他选择在这个节点出现在电视上,宣称自己闭关发功,使得森林大火被压下。 那年他38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在中国剧院连开带功报告会,把一杯自来水说成火场信息的接收器,台下挤满军人医生和普通市民,门票不便宜,现场却有人当场哭笑,有人递纸条求治病。 几天后前线通报明火基本控制,他立刻把《人民日报》头版剪下来,贴在宿舍门后,用红笔圈出基本控制四个字,当成自己功力的证据。 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念出他参与发功的简讯,没有任何评价,但在气功热浪翻涌的八十年代,这样的报道已经足以让无数人把他视作国家认可的奇人。 沈阳小楼里不吃不喝的出关故事,被说成能让树叶枯黄、灯光熄灭,连改天气都算在他头上,连带着连邓稼先病情和导弹轨迹都被编进他的传奇。 风越吹越大,终于吹到清华园。校办收到匿名信,建议破格聘请严新为教授,还夹着那条电视剪报。没多久,他亲自打电话来,说要做一场气与熵的学术报告,还背着人造革包、提着印有四川省政府慰问字样的搪瓷缸和所谓大兴安岭火场信息水走进工字厅。 面对这位被社会追捧的大师,张孝文校长没有跟着热闹,而是准备了一场最简单也最难糊弄的测试。 他当着对方的面在聘书上盖好校章,又把纸放进抽屉锁上,提出一个条件,如果真有隔空移物的本事,就请把聘书从抽屉里移到桌上,清华立刻为他敞开校门。 严新摆出惯常的发功姿势,五指张开对着抽屉,左手托肘,额头渗出汗珠,屋里只剩钟表走动的声音。几十秒过去,抽屉纹丝不动,再多的故事也变不出一张纸。 最终,他只能以磁场不合、电气屏蔽太强为由收场,带着搪瓷缸和那瓶浑水,踩着吱呀作响的木地板离开。那份盖好章的聘书,被校长当成草稿纸写满了基建预算。 清华这一锁,让玄而又玄的气功第一次在顶级学府门口直面最朴素的实验要求,而真正撕开这层神话外衣的,是科学界更直接的追问。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公开发文,指出所谓远程灭火只是踩准了火势自然回落的时间点,所谓奇迹不过是巧合加包装。 气功被吹得神乎其神,不少伪中医借他名义四处招摇,群众的正常判断被搅乱,中医整体声誉也跟着受损。 国家随后下文整顿气功社团,大兴安岭火灾的总结报告里只剩下气象数据和扑火数字,严新之名再未出现,邓稼先的治疗也被还给了正规医疗。 一年后,这位曾经在中国剧院前摆水杯、在电视上圈红字的大师,提着贴有远程灭火纪念字样的硬壳箱,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自称要去斯坦福做生物场实验。 国内的狂热渐渐退潮,清华校史馆偶尔会翻出当年那张被写满算式的聘书,有学生问印章是不是假的,讲解员只会笑着说,章是真章,纸是真纸,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回答。 在那场集体迷信和理性回归的拉锯里,一边是贴在西单墙上的气功海报和排队买票的剧院,一边是工字厅里锁上的抽屉和一句平静的请你先做个实验。 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谁曾经把自己讲得多神,而是当热浪席卷时,还有人愿意把手里的钥匙握紧,用最简单的办法,替科学守住一条看得见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