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结婚那两年,我大姑姐三天两头的来我家,是我和我老公的家,不是我婆婆的家。她来从来不会提前说一声,有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门“咔嗒”一声就开了,她拎着个布袋子走进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喊“弟媳,给我倒杯水”。 刚结婚那年的秋天,我和老周搬进新家,七十平的小房子,厨房的窗户正对着小区的香樟树,风一吹,叶子沙沙响,总带着点潮湿的土腥味。 那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家”——直到大姑姐的布袋子,第一次出现在玄关。 她来从不按门铃。通常是我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手里的锅铲刚碰到热油,门锁“咔嗒”一声转开,她就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蓝布袋子走进来,径直往沙发上一坐,布袋子往茶几上一放,里面的苹果撞出闷响,然后扬声喊:“弟媳,给我倒杯水。” 第一次我愣在灶台前,锅里的葱花已经焦了边。老周从卧室跑出来,搓着手笑:“我姐,她就这样,自家人不客气。”大姑姐白他一眼:“跟你客气什么?倒是你媳妇,站着干嘛?水呢?” 后来我试着在她可能来的周末提前发微信:“姐,今天过来吃饭吗?”她从不回。下一次,她依然会在我切菜时突然出现,布袋子里有时是刚烙的饼,有时是给老周织了一半的毛衣,有时什么都没有,就空着袋子来坐一下午,看我们看电视,听我们说话,像个沉默的影子,却又无处不在。 那时候我总在想,她到底把这里当谁的家?是她弟弟的,还是我们俩的?有次我忍不住跟老周吵,声音压得低低的,怕客厅的她听见:“你就不能跟她说一声,来之前打个招呼?”老周叹口气:“她离了婚,一个人住,除了这儿,她还能去哪?” 转折是在一个雨天。我淋了雨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老周上班前熬了粥,说中午回来。迷迷糊糊中听见门响,以为是老周,结果看见大姑姐站在卧室门口,头发湿了一半,手里的布袋子敞着口,露出里面的保温桶。“我听老周说你病了,”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声音比平时低,“熬了点姜粥,你喝点发发汗。” 我没力气说话,她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我一勺一勺喝。粥熬得很烂,姜味不冲,带着点甜味。她突然说:“以前老周小时候发烧,我也是这样看着他喝。那时候家里穷,就一个暖水瓶,我端着碗在炉子边守着,怕粥凉了。” 布袋子被她脚边的雨水打湿了一小块,我才发现里面除了保温桶,还有一包退烧药,和一小袋话梅——是我上次随口说喜欢的牌子。 后来我慢慢知道,她那个蓝布袋子,装的从来不是“打扰”。离婚后她租的房子在老城区,冬天没暖气,弟弟家的地暖总让她觉得踏实;她织的毛衣永远是老周的尺寸,却会偷偷问我穿多大码;她从不按门铃,是因为以前在老家,她和老周的房间门永远敞着,喊一声就能听见。她只是没学会,弟弟的家,已经多了一个“弟媳”,多了一道需要轻轻敲的门。 现在她来之前,会发个微信:“弟媳,我包了饺子,给你们送点?”我回“好呀”,然后把厨房的窗户打开一条缝,让香樟叶的味道飘进来。她进门时不再直接坐沙发,会先探头往厨房看:“要不要我帮忙?”布袋子放在玄关柜上,拉链拉得整齐,里面有时是饺子,有时是给我买的护手霜——她说“看你老洗碗,手该糙了”。 上周我又在厨房做饭,听见门铃响,是她。我擦着手去开门,她站在门口笑:“今天带了你爱吃的红枣,煮甜汤喝?”阳光从她身后照进来,蓝布袋子上的褶皱里,还沾着点路上的草屑。 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响,我突然觉得,原来所谓“家”,从来不是一道需要紧锁的门。有些笨拙的亲近,像那锅慢慢熬着的甜汤,刚开始可能烫嘴,晾一晾,倒也暖。
我刚结婚那两年,我大姑姐三天两头的来我家,是我和我老公的家,不是我婆婆的家。她来
正能量松鼠
2025-12-19 19:41:38
0
阅读: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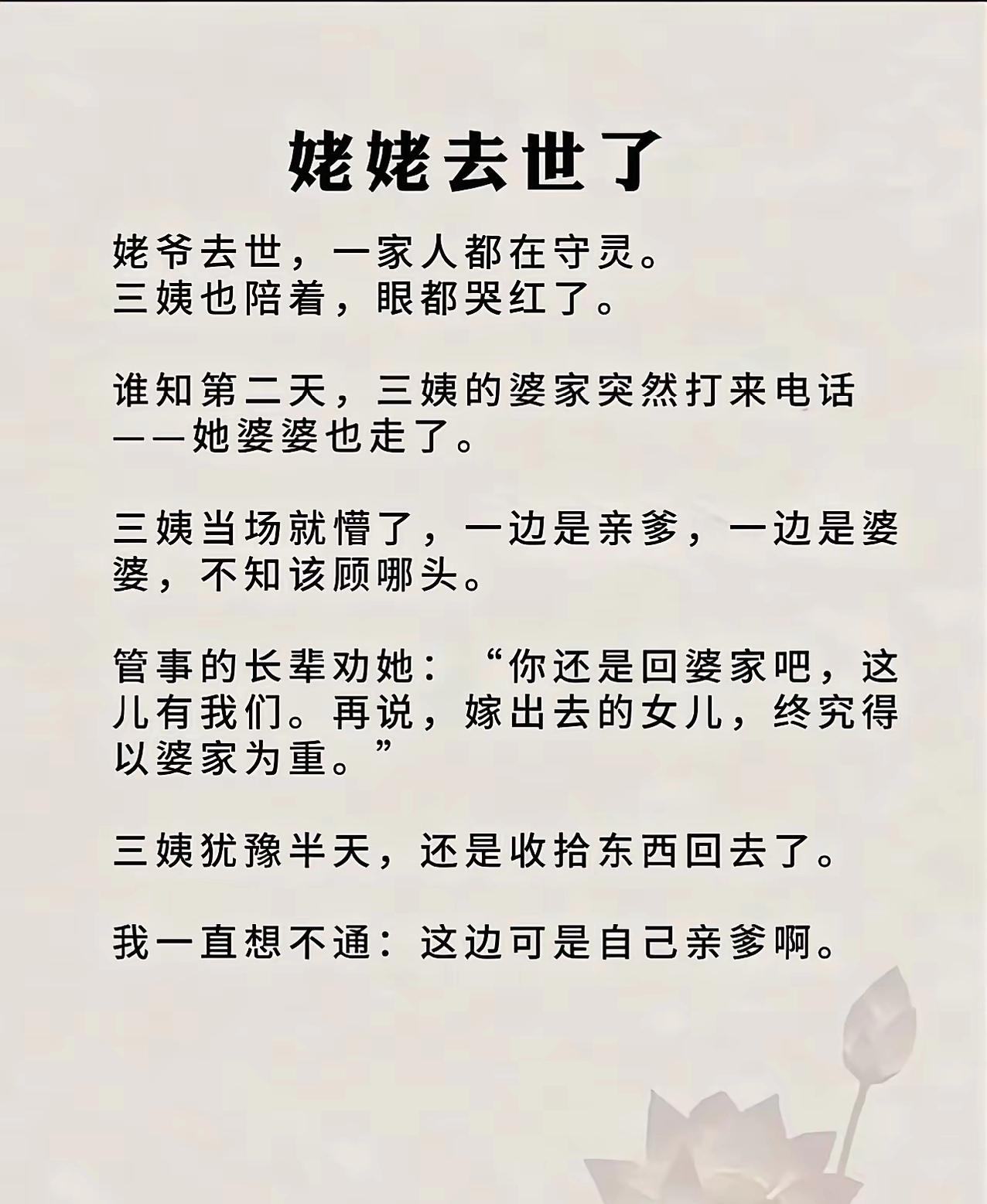




![“男人对媳妇,情人,态度差距就那么大呢”[笑着哭][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3895322271359063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