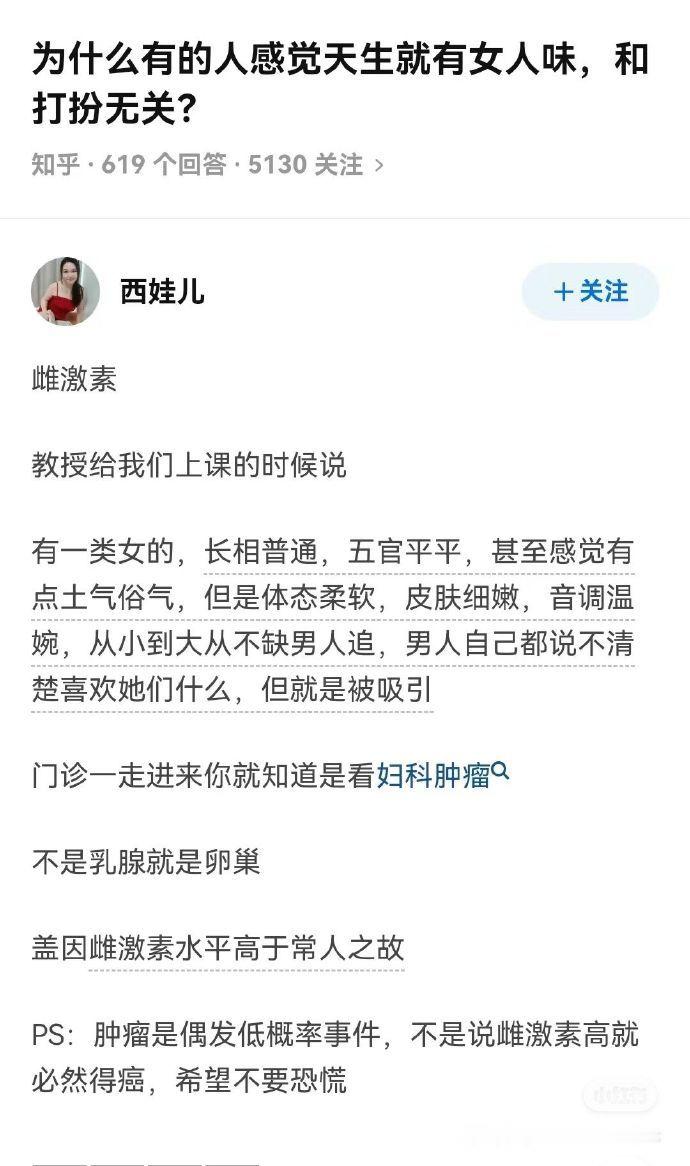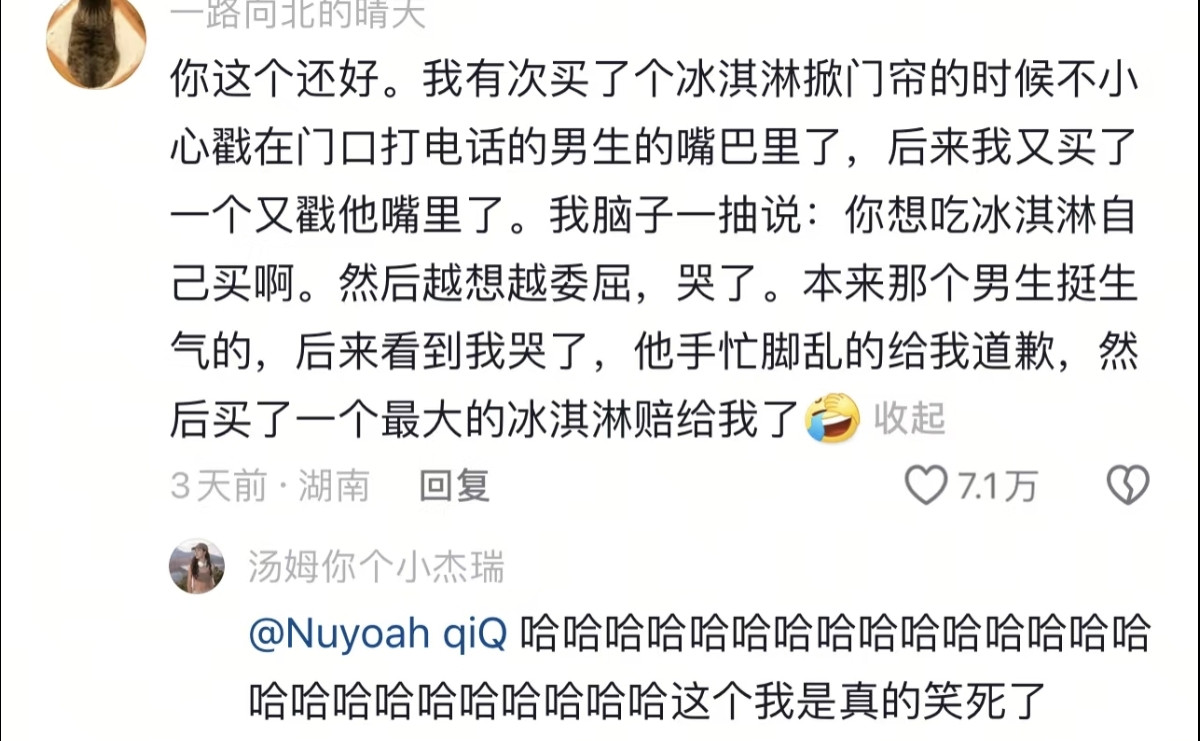今天早上,我和媳妇开车去办事,突然电话响了,一看是比我小两岁的同村同姓乡伦侄子。 他说:三叔,我看见你了。他就在我们车后面,让我住一下。 我们停下来,下了车。他也停下来,下了车。我和他10多年未见了,我们亲切握手,热情聊着。 今天早上,我和媳妇开着那辆半旧的白色SUV,正赶去城东办手续,车窗开了条缝,风裹着路边槐花香钻进来——这味道总让我想起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想起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跑的小屁孩们。 突然手机在中控台上震动起来,屏幕上跳着“小勇”两个字,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不是比我小两岁的同村侄子吗?他怎么会打电话来? 他电话里的声音有点急,带着乡音的尾调:“三叔!三叔你等会儿!我看见你车了!就在你后面第三个车位,黑色的小轿车!” 我透过后视镜往后看,果然有辆黑色轿车打着双闪,正慢慢往路边靠。媳妇也探头看:“是熟人?”我点头,打了右转向灯,慢慢把车停在路边,心里却在翻涌——上一次见小勇,还是他娶媳妇那年,我回去喝喜酒,一晃,是不是有十三年了? 我们刚下车,后面那辆黑色轿车的门也开了,一个穿着蓝色工装夹克的男人快步走过来,头发比记忆里稀疏了些,眼角有了细纹,但眉眼间还是小时候那股机灵劲儿。 他走到我面前,手已经伸了过来,掌心带着薄茧,握得很紧:“三叔!真是你!我刚才看车牌就觉得眼熟,跟我妈说‘这不是三叔家的车吗’,她还说我眼花,我赶紧打你电话试试——没想到真打通了!” 我也用力回握,能感觉到他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这用力里,有久别重逢的局促,也有怕认错人的小心。 媳妇在旁边笑着说:“快别站着了,上车说?”小勇摆摆手:“不了不了,我送我妈去医院复查,顺路看见你们,就想打个招呼——三叔,你头发也白了不少啊,”他伸手想碰我鬓角,又缩了回去,挠挠头,“小时候你总揪我头发,说我‘黄毛小子没个正经’,现在倒过来了。” 一句话让我笑出声,那些被时间模糊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夏天傍晚,他端着碗蹲在我家门口,看我修自行车;过年时抢我的红包,跑出去老远又回头做鬼脸;后来他去城里打工,走的那天我去送,他红着眼圈说“三叔我混好了就回来”——原来那些以为被日子冲淡的细节,都好好地藏在心里。 我上下打量他,工装夹克袖口磨得起了毛边,鞋子上沾着点泥,想来日子过得不算轻松,可他脸上没一点愁容,说起村里的事,谁家盖了新房,谁家添了孙子,哪个老人去年走了,语气里都是熟稔,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我原以为,城里人待久了,心会变远,可小勇身上那股热乎劲儿,还是跟村口的老井水一样,清凌凌的,甜。 为什么明明十几年没联系,他看见我车就能认出来?为什么一个电话,就能让两个被生活推着往前跑的人,站在路边像傻子一样笑?或许就是因为那声“三叔”,那声刻在骨子里的称呼;或许是因为我们血管里流着同一片土地的血,那些一起爬过的树、摸过的鱼、挨过的骂,早就把我们的根缠在了一起,就算隔了再远的路、再久的时间,也断不了。 最后他要走,塞给我一袋刚从地里摘的草莓,说是他媳妇种的,“甜着呢,三叔你尝尝”,我推辞不过,接过来时袋子还带着湿土的凉气。 看着他开车走了,媳妇说:“耽误了半个多小时,手续怕是赶不上上午了。”我却不觉得急,手里的草莓袋子温温的,心里也温温的——有些相遇,比准时赶到的手续重要多了,不是吗? 重新发动车子,槐花香好像更浓了些,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仪表盘上,映出小勇刚才塞给我的草莓袋子的影子。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从兜里掏出一颗偷摘的野枣,硬塞给我,说“三叔你吃,甜!”——原来时间带走了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它带不走,就像这声“三叔”,就像这袋带着土味的草莓,就像我们站在路边,笑着笑着眼里就有点湿的瞬间。
卧槽…真的假的?
【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