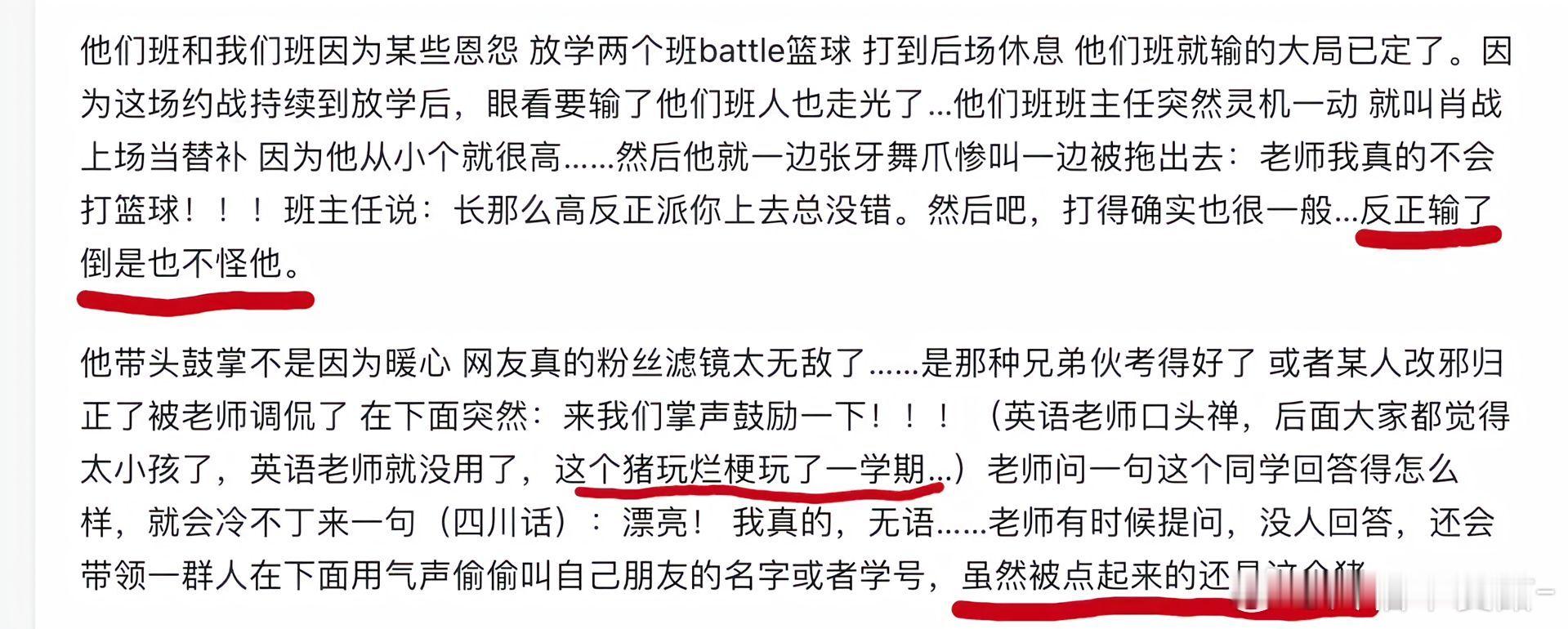我想我是疯了。我竟然想在这个欲壑难填的世界里,找一个与自己灵魂相契的人。原来天水共一色,只待鱼与鸟齐飞。可碰得头破血流才明白,山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曾以为只要捧着一颗真心往前闯,总能在人潮里撞见那个眼神交汇时,彼此都懂“月亮与六便士”的人。 我想我是疯了。 在这个连刷短视频都要两倍速的世界里,偏要找个能一起盯着落叶飘十分钟的人。 书桌上的《月亮与六便士》摊着,夹页里夹着片银杏书签——去年秋天在颐和园捡的,边缘已经蜷了,带着旧书的霉味和没喝完的冷咖啡香,像个不肯醒的梦。 第一次见他是在街角读书会。 傍晚六点,夕阳把玻璃窗烧得通红,他坐在我对面,手指敲着桌面打拍子,哼的调子刚好是我手机里那首循环了三个月的冷门民谣。 “你也听陈鸿宇?”我没忍住开口,声音比刚煮好的咖啡还烫。 试探是从那本书开始的。 他指着我翻开的《月亮与六便士》说“斯特里克兰德真是疯得可爱”,我几乎要把藏在书脊里的银杏书签抽出来递给他——那瞬间以为终于撞进了同一个频道,连呼吸都跟着轻了半拍。 “你觉得他抛家弃子是对的?”我故意问,想确认那点“疯”是不是和我同个质地。 “忠于自己永远没错。”他笑起来,眼角的细纹里盛着光,“总比困在六便士里强。” 转折来得比秋雨还急。 第三次见面,他约我去798看画展,指着一幅抽象画说“这和我家沙发一个色,改天拍给你看”,我提起斯特里克兰德临终前让烧掉所有画,他突然皱眉:“太矫情了吧?画画不就是给人看的?” 我握着热可可的手顿了顿,杯壁的水珠滑到手腕,像突然泼下来的冷水——原来他说的“疯”是热闹的、要被看见的,我守的“月亮”是孤僻的、宁愿烂在心里的。 可灵魂的频道,真的能靠几句共鸣就对上吗? 我以为我们都懂“六便士”的世俗与“月亮”的孤绝,却忘了每个人的月亮都挂在不同的夜空;山鸟爱栖在悬崖的松枝,鱼群习惯沉在深潭的卵石,方向从一开始就写好了答案。 那天之后,我把银杏书签夹回书的最后一页。 短期里,再没去过那家读书会,路过街角咖啡馆会绕着走;长期来看,倒也学会了和自己的“月亮”独处——毕竟没人懂的时候,月光的清辉也不会少半分。 当下能做的,或许就是接受山鸟与鱼不同路,至少我们都曾抬头看过同一片天,不是吗? 昨夜整理书架,《月亮与六便士》掉在地上,银杏书签滑出来,在月光下泛着浅黄。 我想起他说“画画要给人看”时眼里的笃定,突然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他有他的观众,我有我的月亮,山水不相逢,可月光总还会落在我们各自的路上。
我想我是疯了。我竟然想在这个欲壑难填的世界里,找一个与自己灵魂相契的人。原来天水
嘉虹星星
2025-12-14 02:06:56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