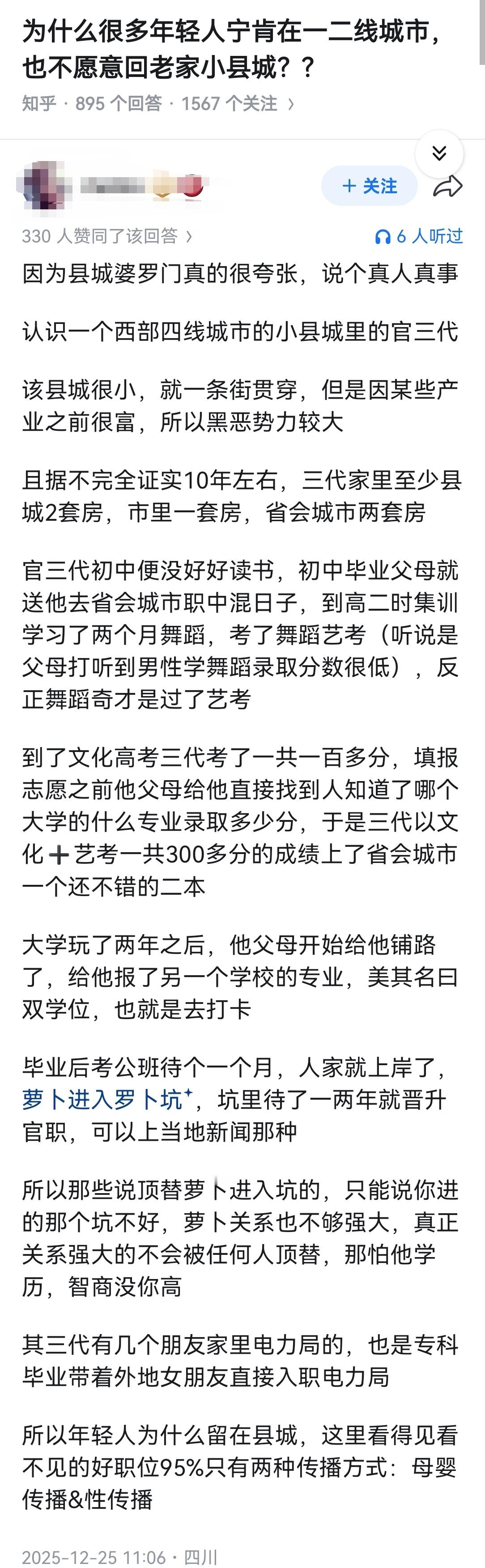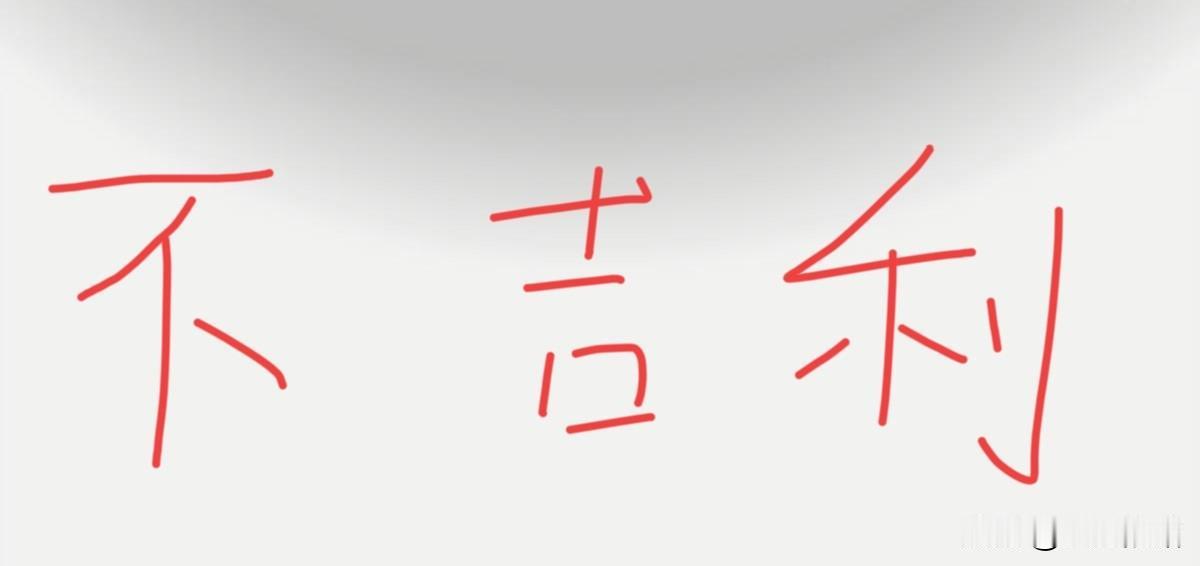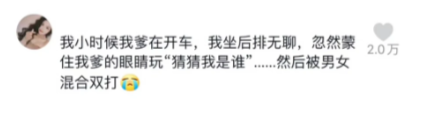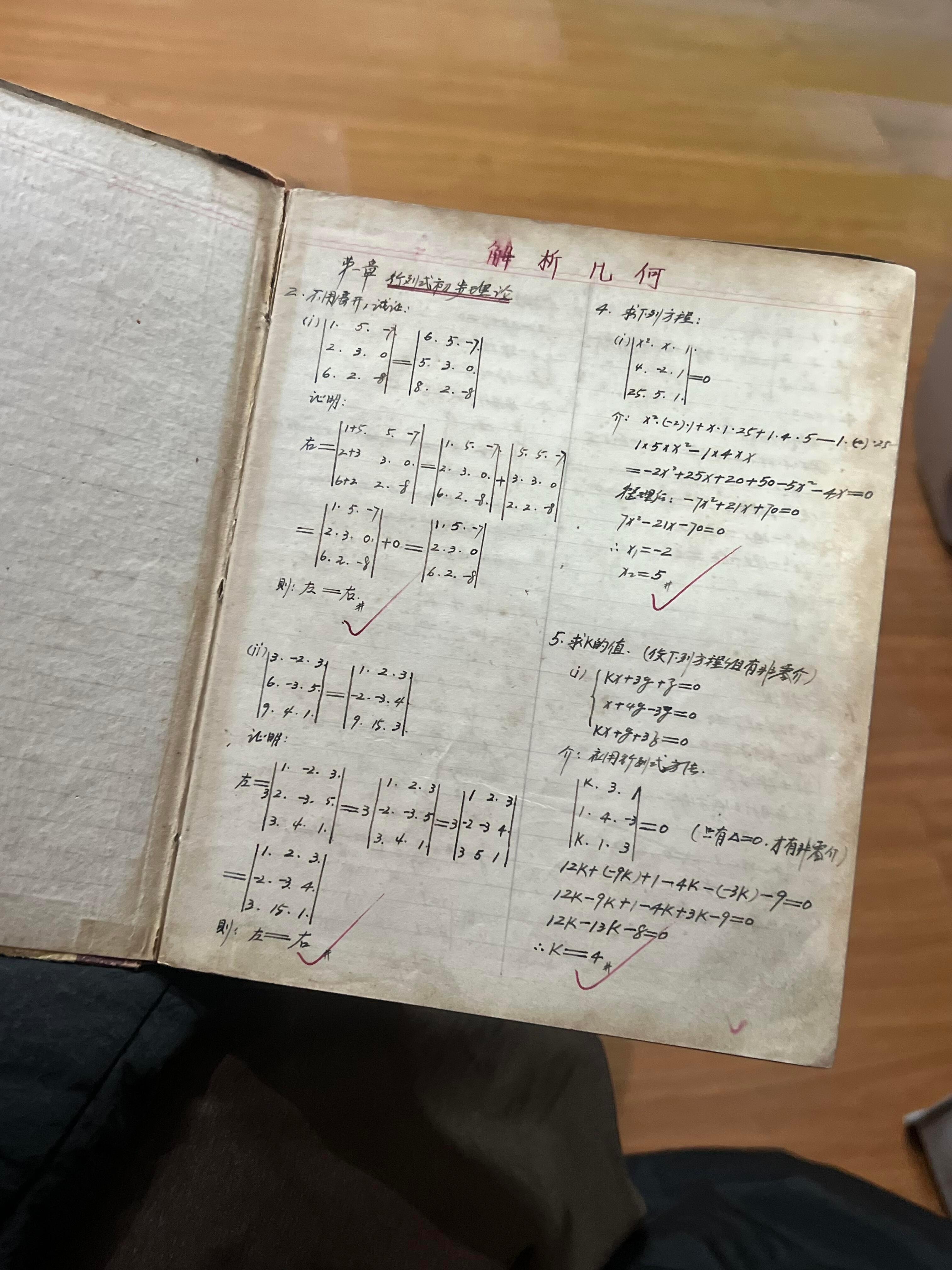俺们村的老支书,那时候可风光了。我22岁刚退伍回来,在乡里当个临时工。那天老支书把我叫到大队部,拍着我肩膀说:"建军,你是部队里出来的,办事牢靠,村里的苹果园缺个带头人,我看你行。" 这话听着是风光,可我心里打鼓。 大队部靠窗的桌子上,摊着张泛黄的图纸,是村西头那座旧小学的,墙皮都掉得露出了砖。 老支书用他那根磨得发亮的铜烟杆,戳着图纸上的裂缝:"别瞅苹果园了,那园子有老李盯着呢,我是想让你把这破学校拾掇拾掇。" 我当时就愣了,手里的搪瓷缸"哐当"磕在桌腿上,茶水溅出几滴。 "支书,学校?"我嗓子有点干,"村里娃不都去镇上上学了吗?那破屋都空五年了。" 老支书没接话,从抽屉里摸出个红布包,打开是本皱巴巴的作业本,字歪歪扭扭的,最后一页写着"王石头,三年级,总分58"。 "这是你小时候的,"他指尖在"58"上摩挲,"那时候教室漏雨,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木板,你爹为了让你去镇上复读,把家里唯一的老黄牛都卖了。" 我心口猛地一揪,想起爹牵着牛走时,牛尾巴扫过我手背的感觉,糙得像砂纸。 "现在不一样了,"老支书把烟杆在鞋底敲了敲,"水泥路通到村口了,可镇上小学远,娃们天不亮就得走,冬天冻得手都握不住笔。你要是把学校修好了,哪怕先招几个娃,也比让他们遭这罪强。" 我望着墙上那张褪色的"教育先进村"奖状,边角都卷了,突然想起退伍前在哨所,教导员说的"守边防是守国,守家乡是守根"。 第二天我去看旧学校,门框上还刻着"好好学习",砖缝里长着半尺高的草。 刚扒拉掉门口的杂草,就听见背后有人咳嗽:"建军,这破房梁都朽了,你真要折腾?" 是村东头的李大叔,扛着锄头站在土坡上,草帽沿压得很低。 "大叔,支书说修修还能用。"我捡起块碎玻璃,"你家小孙子不也在镇上上学?天天骑车来回,多危险。" 李大叔"嗤"了一声:"危险也比在这漏风的屋里强,再说了,修学校不要钱?村里账上那点钱,留着给老人们买煤不好?" 我没接话,掏出卷尺量教室尺寸,阳光从破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格子,像张没画完的棋盘。 接下来半个月,我天天泡在学校,清垃圾,换房梁,请镇上的瓦匠来看。 老支书每天都来,提着他那个豁了口的保温桶,里面是婶子熬的玉米粥。 "昨天去乡文教办了,"他喝着粥,米粒粘在胡子上,"张主任说只要咱把教室修好,他给派个代课老师,工资乡里出。" 我正钉钉子的手顿了下:"真的?" "那还有假,"他掏出张纸条,"这是申请报告,我签了字,你也签一个,咱爷俩联名。" 纸条边缘都磨毛了,老支书的签名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 没想到签完报告第三天,李大叔领着三个村民来了,手里都拿着家伙——锯子、锤子、撬棍。 "建军,你别一个人扛着,"他把锯子扔在地上,"我问过小孙子了,他说镇上教室挤,老师顾不过来,要是村里学校能开课,他愿意回来。" 我看着他们手上的老茧,突然想起部队里一起扛枪的弟兄,心里热乎乎的。 动工那天,老支书非要爬梯子刷墙,我不让,他急了:"我年轻时刷过戏台子,比你懂!" 结果刚爬两步,梯子"咯吱"一响,他晃了晃,我赶紧扶住,他手里的刷子掉在地上,红漆溅了我一裤腿。 "老了,老了,"他拍着大腿笑,皱纹里都是红漆点子,"还是你们年轻人行。" 刷完墙的第二天,县上拉来了新课桌,锃亮的,蓝白相间。 李大叔的小孙子第一个跑来,趴在桌上摸了又摸:"爷爷,这桌子真滑,比镇上的好!" 老支书蹲在门口看着,掏出烟袋想点,手抖得划不着火柴。 我给他点上,他吸了口,烟圈慢慢散开:"你知道我为啥非要修这学校不?" 我摇摇头。 "我爹当年是私塾先生,"他望着教室,眼神飘得老远,"后来私塾拆了,他就病了,临走前说'村里没了念书的地方,根就断了'。" 那天下午,有辆面包车停在村口,是在外打工的王婶,她抱着女儿下来:"建军,听说学校修好了?我不走了,让妞妞在村里上学。" 妞妞扎着羊角辫,跑到教室门口,踮着脚往里望,眼睛亮得像星星。 九月一号开学,三个孩子,一个代课老师,老支书非要升国旗,把家里过年挂的红灯笼拆了,做了面简易的红旗。 国歌响起时,李大叔的小孙子突然举起手,敬了个不标准的礼,妞妞跟着学,小胳膊歪歪扭扭。 老支书站在国旗下,腰杆挺得笔直,像棵老松树。 升旗结束,他走过来拍我肩膀,跟第一次在大队部一样,可这次他的手有点抖:"建军,你看,这根没断,咱村的根,没断。" 我望着孩子们跑进教室的背影,突然觉得,老支书说的风光,不是苹果堆满仓,是看着这些小不点儿,在咱自己修的教室里,把书念出声来。 现在每次路过学校,都能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像春天的雨,一点点浇在村里的土上,我知道,总有一天,这土会发芽,长出新的希望来。 只是不知道,等明年春天,会不会有更多的孩子回来,让这读书声,再响亮点,再响亮点。
1957年,浙江发现疑似“野人”的生物,攻击小女孩。村民发现后将其打死,并吃掉,
【9评论】【8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