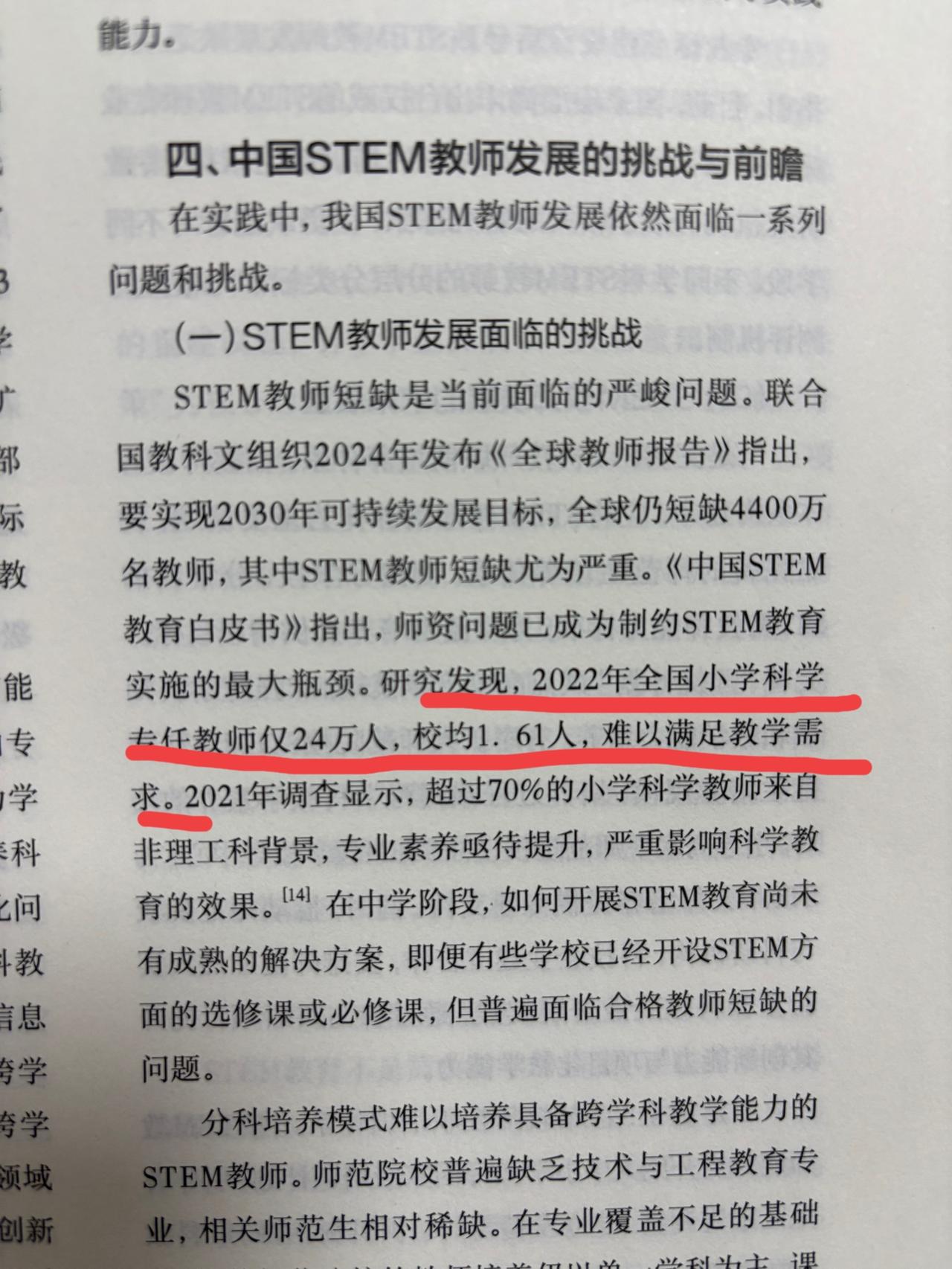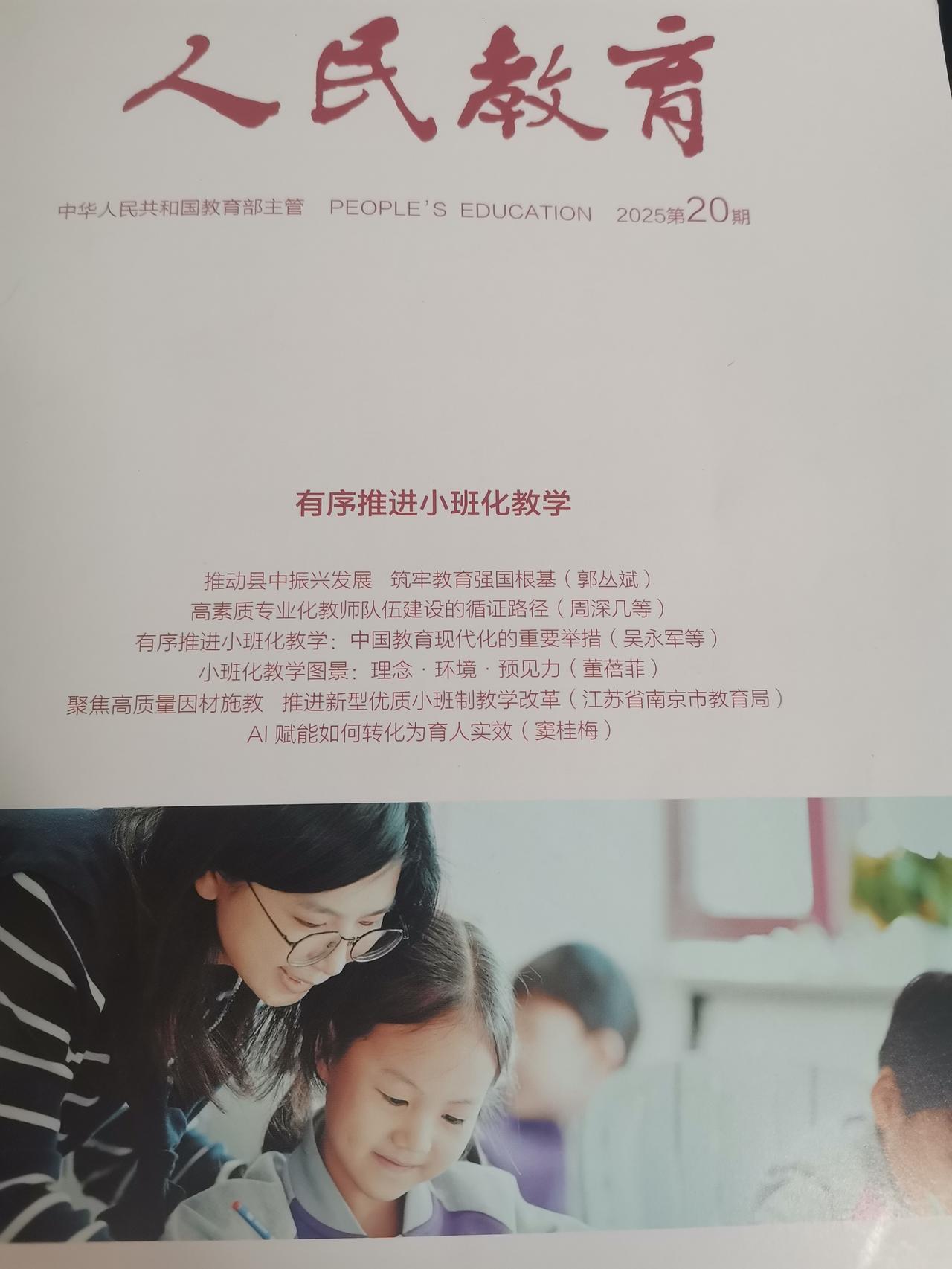儿媳突然要辞掉公司中层的工作,去考教师编制,让我非常费解! 我当时正蹲在厨房择菠菜,手里的菜叶子 “啪嗒” 掉在水盆里,溅了一裤腿水也没顾上擦。推开客厅门时,儿媳正趴在茶几上写东西,面前摊着好几本封皮印着 “教育知识与能力” 的书,旁边还放着个计时器。我走过去敲了敲茶几,她抬头看我,眼镜滑到了鼻尖上,伸手推了推才开口:“妈,您择完菜了?” 我没接话,指着那些书:“你跟我说说,好好的班不上,捣鼓这些干啥?你们公司那个张总,上次吃饭还说要给你升副总,这节骨眼上辞工,你脑子咋想的?” 她把手里的笔放在笔帽里,又把写满字的草稿纸往我这边推了推,上面全是圈划的重点,有的地方还用不同颜色的笔标了注释。 “妈,我不是一时兴起。” 她伸手捋了捋额前的碎发,指尖沾着点墨水印,“上个月我不是胃出血住院吗?隔壁床住了个小学老师,每天放学都有学生来看她,带的苹果上还画着笑脸。有天晚上我疼得睡不着,看见她给学生改作业,改到错题就用红笔轻轻圈出来,旁边写着‘再想想呀’,那语气比跟她自己儿子说话还耐心。” 我想起她住院那阵,确实每天都有孩子来,叽叽喳喳的,倒让冷清的病房热闹不少。可这也不能当辞工的理由啊,我往沙发上一坐,掏出手机翻出她上个月的工资条:“你看看这数,比我跟你爸加起来还多,当老师一个月能有多少?再说你当中层当惯了,去管一群半大孩子,能适应?” 她没反驳,起身去厨房给我倒了杯温水,杯底还放了两颗枸杞。“妈,我上个月跟客户谈合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回家时孩子都睡熟了,书包还扔在门口没收拾。有天早上他醒得早,拉着我衣角问,妈妈能不能去开一次家长会,我才想起他上幼儿园半年,我一次都没去过。” 她说到这儿,声音低了点,伸手摸了摸茶几上孩子的照片,那是上周幼儿园拍的,孩子站在最边上,笑得有点拘谨。 从那天起,我就看着她钻进了考编的堆里。每天早上五点半,客厅的灯准会亮,我起来做早饭时,总能听见她小声背知识点,怕吵到我们,还特意把窗户关严,嘴里含着块薄荷糖压着声音。晚上下班回来,她不看电视也不刷手机,吃完晚饭就钻进书房,门底下的缝里总透出灯光,有时候我起夜,凌晨一点那灯还亮着,门口放着杯早凉透的白开水。 有次我偷偷进她书房送牛奶,看见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头枕着厚厚的笔记本,手里还攥着笔,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黑点。笔记本上记着她总结的答题技巧,旁边写着 “儿子说想当科学家,以后要教他写实验报告”。我放轻脚步把牛奶放在桌边,看见她眼角有淡淡的黑眼圈,发梢里还藏着两根白头发,才三十多岁的人,比我四十多岁时看着还累。 考试那天她起得格外早,穿了件米色的外套,是孩子说好看的那件。出门前她蹲下来给孩子系鞋带,孩子把攥了半天的幸运星塞给她:“妈妈加油,当老师了就能给我讲故事了。” 她捏了捏孩子的脸,转身时跟我对视了一眼,眼里有我从没见过的坚定。 成绩出来那天,她下班回来没像往常一样直奔书房,而是举着手机跑到我面前。我凑过去看,屏幕上是合格线和她的分数,高出一大截。她没笑,反而红了眼眶,伸手抱住我:“妈,我不是要丢了中层的工作,我是想换个能陪着孩子,也能对得起自己心的活儿。” 后来她去学校试讲,我跟着去了。站在教室后门,看见她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生字,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身上,底下的孩子举着小手抢着回答问题,她笑着点一个扎小辫的姑娘,那语气软和得像春天的风。我突然就懂了,她辞掉的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应酬和缺席的陪伴,要的不是编制的安稳,是站在讲台上时,眼里藏不住的光。
目前学校最缺的学科老师不是心理健康教师也不是思政教师更不是体育教师而是科
【1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