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带小三回家,婆婆不敢吭声,可我是出了名的泼妇:我来处理。 那天我刚从幼儿园接完孩子,还没进门就听见客厅里传来陌生女人的笑声,脆生生的,裹着一股子刻意的甜腻。推开门的瞬间,我手里的菜篮子差点砸在地上——玄关处摆着一双亮闪闪的细高跟,不是婆婆的风格,鞋跟尖得能戳破地板。客厅里,公公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正中间,旁边依偎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染着栗色卷发,指甲涂得通红,正拿着牙签给公公递水果。婆婆呢?她缩在角落的单人沙发里,头埋得低低的,手里攥着块抹布,指节都泛了白,听见开门声也没敢抬头。 幼儿园门口的桂花还没散尽,我牵着孩子的手往家走,菜篮子里躺着刚买的新鲜排骨,想着给婆婆炖汤。 可还没到三楼,就听见家里传来女人的笑声,不是婆婆那种温吞的,是甜得发腻的,像裹了层糖衣。 我心里咯噔一下,钥匙插进锁孔都在抖。 门一开,玄关那双亮闪闪的细高跟先扎了眼——跟尖细得能戳破地板,鞋跟还沾着片枯黄的落叶,不是婆婆的风格。 客厅里,公公居然没像往常那样看报纸,他翘着二郎腿陷在沙发里,旁边偎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栗色卷发搭在公公胳膊上,红指甲捏着牙签正往他嘴里送水果。 我扫了一圈,婆婆呢? 她缩在角落的单人沙发里,头埋得快碰到膝盖,手里攥着块湿抹布,指节白得像要嵌进木头里,连我开门都没敢抬头。 空气里飘着股陌生的香水味,混着公公身上的烟草味,熏得我嗓子发紧。 那姑娘抬眼看见我,非但没起身,反而往公公身边靠得更近了,声音嗲得发酥:“叔叔,这是您儿媳妇吧?真年轻。” 公公清了清嗓子,不自在地咳了声,没接话,眼神却瞟向我手里的菜篮子,带着点警告的意思。 我把孩子往身后一藏,菜篮子“咚”地放在茶几上,排骨撞得塑料袋沙沙响。 “爸,家里来客人了?”我故意拖长了音,目光扫过那姑娘的红指甲,“也不提前说声,我好加双碗筷。” 姑娘似乎没听出弦外之音,笑着说:“不用麻烦嫂子,我跟叔叔说说话就走。” “说话?”我走到婆婆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妈,您这抹布都快攥出水了,要不先去厨房歇会儿?” 婆婆身子一僵,还是没抬头,只是摇了摇头。 我直起身,走到那姑娘面前,没等她反应过来,伸手就把她手里的果盘端走,“啪”地放在茶几另一边。 “姑娘,我们家有规矩,客人得坐在客人该坐的位置。”我指了指对面的小凳子,“这沙发,是我妈跟我爸坐了三十年的地方。” 姑娘的脸瞬间白了,求助似的看向公公。 公公终于沉下脸:“你这是干什么?没大没小的!” “我没大没小?”我笑了,声音却冷得像冰,“爸,您带个外人回家,坐在我妈常坐的位置,让她缩在角落擦灰,这就是您当长辈的规矩?” 我弯腰拿起那双细高跟,走到门口,直接扔了出去——“砰”的一声,鞋跟撞在楼道的水泥地上,在安静的午后格外刺耳。 “我的家,不欢迎穿这种鞋的人。”我盯着公公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要么您让她走,要么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回来评评理——看看是他爸带小三回家有理,还是我这个‘泼妇’儿媳妇护着婆婆没错!” 公公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 那姑娘吓得赶紧站起来,抓起包就往门口跑,连掉在地上的围巾都没敢捡。 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婆婆终于吸了口气,带着浓浓的鼻音。 我转身扶她起来,她的手冰凉,掌心全是汗。 “妈,以后他再这样,您别忍着。”我把湿抹布扔进盆里,水声哗啦响,“家是两个人的,不是他一个人的戏台。” 婆婆看着我,眼泪突然掉了下来,砸在手背上,像滚烫的水。 后来我才知道,公公最近总说单位发福利,其实是把钱都花在了那姑娘身上;婆婆不是不敢吭声,是怕我知道了生气,更怕儿子夹在中间为难。 可她忘了,有些退让换不来体谅,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那天晚上,老公回来后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给婆婆转了笔钱,又把公公的工资卡要了过来交给我保管。 现在家里的笑声,终于又变回了婆婆那种温吞的、带着烟火气的。 或许“泼”不是最好的办法,但面对欺负到头上的委屈,沉默从来换不来尊重。 你看,那双被我扔掉的高跟鞋,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像是从来没出现过——可有些裂痕,只有及时修补,才不会碎得彻底。
公公带小三回家,婆婆不敢吭声,可我是出了名的泼妇:我来处理。 那天我刚从幼儿园
卓君直率
2025-12-31 18:41:43
0
阅读: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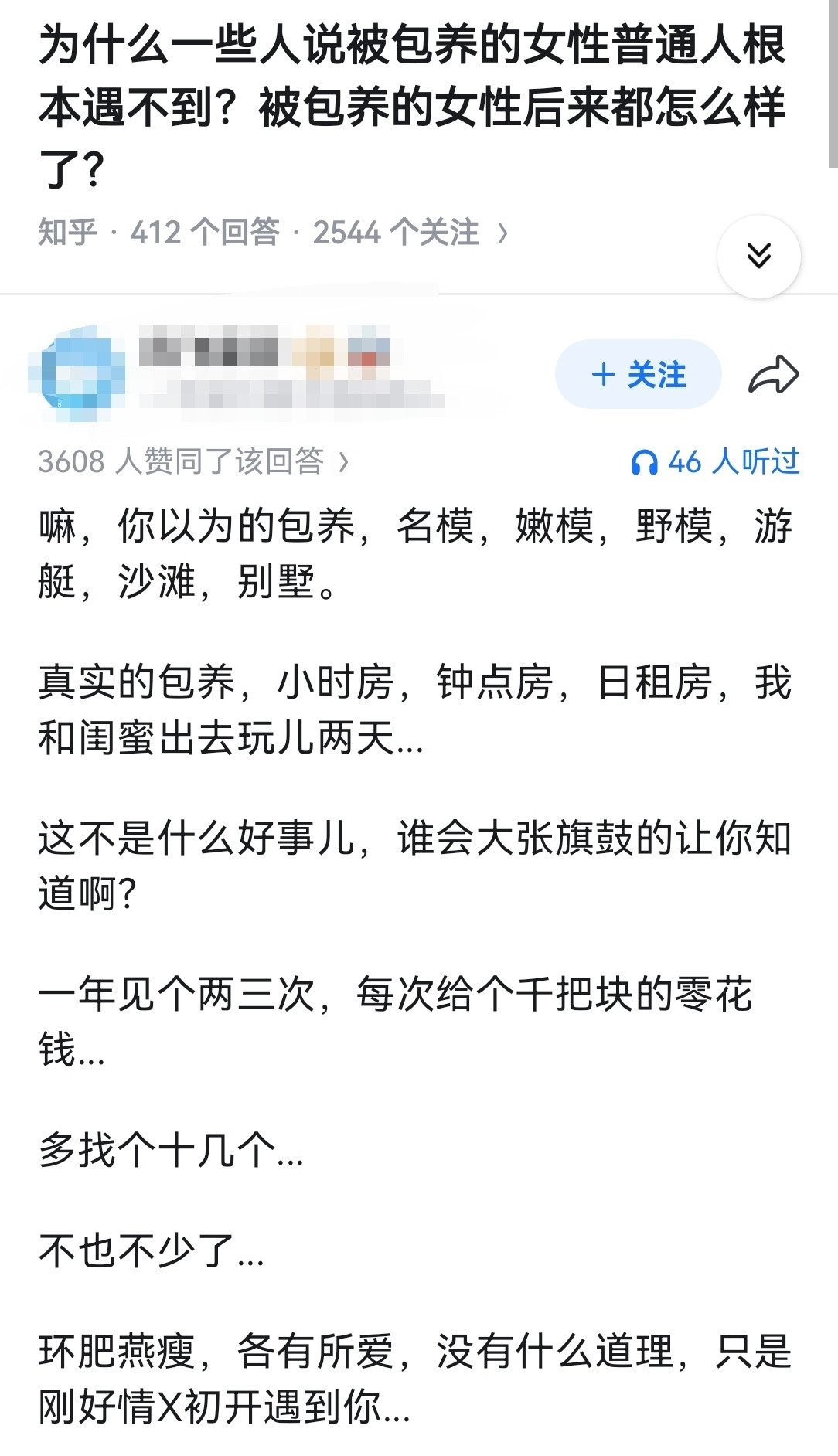




君子不争炎凉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