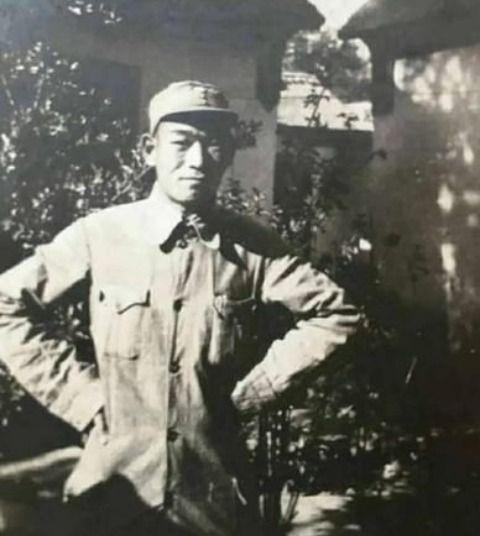和很多离开大陆的名人不同的是,张爱玲是在解放后才离开的,这也就是说她起初是打算留在大陆的,但为何最终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非要选择离开呢? 1952年7月的上海码头,穿着月白色旗袍的张爱玲提着皮箱站在人群里。 这个曾写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的女作家,此刻正低头整理着旗袍下摆,三个月前她还在《亦报》连载《十八春》,试图用沪上男女的悲欢离合贴合新社会的审美。 文代会会场的灯光至今晃得她眼晕。 那天全场都是中山装的灰蓝色海洋,唯有她坐着米白色旗袍配细跟皮鞋。 后排座位的冰凉透过薄薄的衣料传来,台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声里,她捏着发言稿的手指越收越紧,最终一个字也没说。 "复学"申请批下来时,她正对着镜子试穿新做的素色旗袍。 1939年未完成的港大课业突然成了救命稻草,海关人员翻看她的行李时,《金锁记》手稿夹在《新文学概论》里,纸页边角已经磨得起毛。 香港的湿热空气让旗袍黏在背上。 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前,她写下"秧歌队在月光下扭动"的句子,笔尖却悬在"红色"二字上方迟迟落不下去。 稿费换来得罐头摆了半桌,可翻开《秧歌》样书时,她突然想起上海寓所窗台上那盆没带走的茉莉。 洛杉矶公寓的衣柜里始终挂着三件旗袍。 赖雅去世后,她常在深夜对着镜子比划,布料摩挲声在空屋里格外清晰。 1995年警察推开房门时,书桌上摊着的信纸上,"上海"两个字被洇湿了一小片,像一滴迟迟未落的泪。 那些在文代会没说出口的话,最终都融进了《小团圆》的字里行间。 晚年接受采访时,她摸着旗袍盘扣轻声说:"文字是随身的避难所。 "镜中映出的身影,和1949年那个独坐会场后排的女作家慢慢重叠,只是眼角的细纹里,多了些回不去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