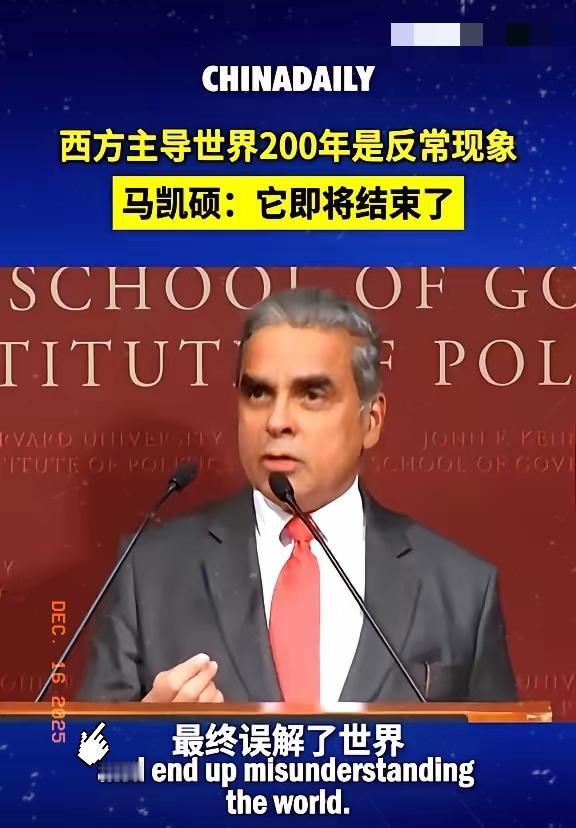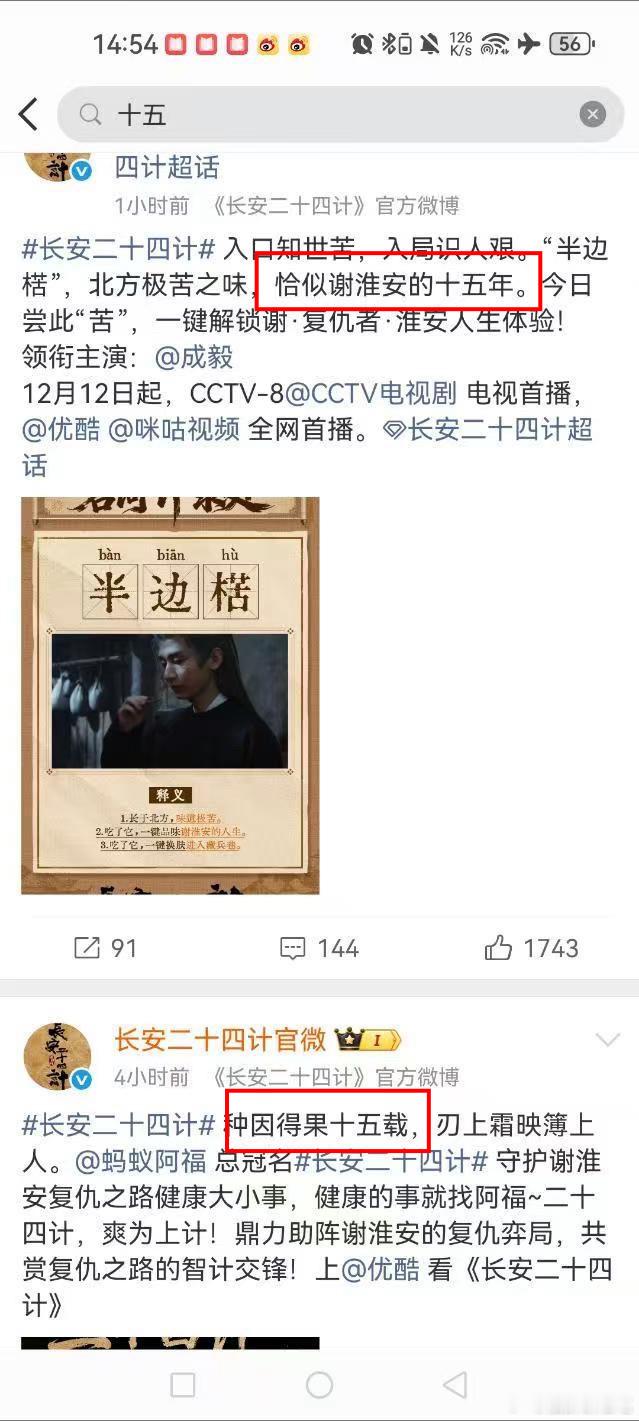1993年秋,刑场上的曹琳琳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手里攥着的旧手帕已经被泪水浸透。 这个20岁的农村姑娘,三年前揣着50块钱和一床碎花被来到城市时,从没想过自己会以杀人犯的身份离开。 她后来在狱中日记里写:“城里的灯真亮,亮得我以为能照见未来。” 谁也没想到,这束光最后会变成焚尸时的火焰。 1993年3月,曹琳琳把煤矿老板5岁的女儿骗到后山,用准备好的麻绳勒住了孩子的脖子。 孩子挣扎时扯掉了她袖口的纽扣,那个掉在泥土里的塑料纽扣,后来成了警方锁定她的关键证据。 她烧了孩子的衣服,以为能烧掉所有痕迹,却忘了自己鞋跟上沾着的煤渣,那是她在矿上打杂时蹭上的,怎么刷都没刷干净。 曹琳琳的老家在豫西山区,土坯房的墙缝里还塞着她辍学那年的奖状。 1991年,17岁的她把奖状一张张揭下来塞进箱底,跟着同村的婶子去了山西。 那时村里半数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她妈给她缝的碎花被里裹着煮熟的鸡蛋,说“挣了钱先给你哥娶媳妇”。 她在火车上啃着鸡蛋,看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觉得城里的工厂肯定比家里的田地好。 现实给了她一巴掌。 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一个开着摩托车的男人说矿上招仓库管理员,管吃管住还能预支工资。 她跟着去了才发现根本没有仓库,男人是煤矿老板,当晚就把她堵在宿舍。 她哭过闹过,男人塞给她一沓钱,说“跟我,以后让你当老板娘”。 她把钱寄回了家,却没敢说钱的来历。 后来男人的老婆找上门,她被赶了出来,说好的工资一分没给,连回家的路费都没留下。 她去派出所报案,接待的民警翻着台账说“没证据不好办”。 她想去法院,门口的保安看她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问她“请得起律师吗”。 她在矿上的工棚外徘徊,听见男人们说“一个乡下丫头,玩玩怎么了”。 那天晚上,她在河边捡了块石头,想砸死那个老板,举起手又放下了,她想起家里的爹娘,想起箱底的奖状。 本来想忍忍就算了,但后来发现,有些伤害不是忍就能过去的。 法庭上,曹琳琳把所有事都说了。 法官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盯着地面说“他毁了我的一辈子,我也让他不好过”。 判决书下来那天,她要了纸笔,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开头是“爹,娘,别等我了”。 执行死刑前,她把一直攥着的手帕展开,里面包着的是当年从家里带出来的那颗煮鸡蛋的蛋壳,她没舍得吃,后来干了,就一直收着。 看到卷宗里记载的她案发前曾去派出所却被劝“私了”,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弱势群体,手里攥着的从来不是法律武器,而是无处安放的绝望。 就像她鞋跟上的煤渣,想蹭掉却越蹭越牢,最后跟着她一起走向了绝路。 那颗被孩子扯掉的塑料纽扣,后来被法医收进了证物袋。 现在应该还躺在档案室的某个铁柜里,纽扣上的裂痕像一道永远合不上的伤口。 曹琳琳的故事过去三十年了,我们再提起她,不是要原谅她的罪行,而是要记得:每个揣着碎花被进城的年轻人,都该有一条能讨回公道的路,不用攥着绝望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