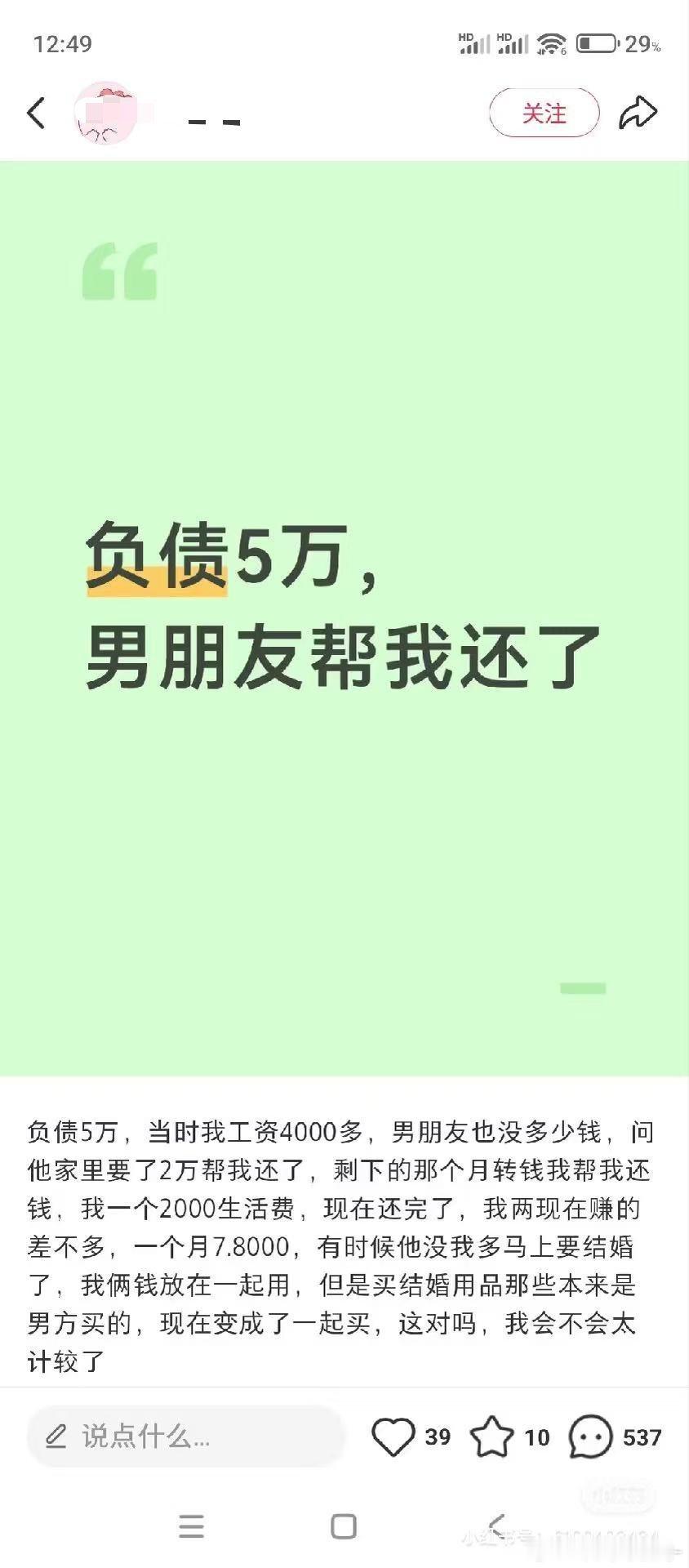1955 年我在部队刚提干,妹妹从老家坐三天火车来看我。我去营门口接她时,撞见了要去视察的师长。我立马立正敬礼喊 “首长好”,可师长的目光落在妹妹脸上后,手里的文件夹 “啪嗒” 掉在地上,眼睛直勾勾的,整个人都僵在那儿,那模样是真看傻了。 我捡起文件夹,手心有点冒汗。师长接过,眼神却没离开过妹妹的脸。他喉结动了动,声音发干:“你……叫什么名字?” 妹妹怯生生答了。师长又问:“你母亲,是不是叫李秀兰?” 妹妹眼睛一下子睁圆了:“您认识我娘?” 师长没答话,转身对警卫员摆摆手,示意视察推迟。他让我们跟他走,脚步很快,一路沉默。营部后面有棵老槐树,树下有石凳。他站定,从贴胸的口袋里摸出个东西,是张旧得发黄的照片,递给我妹妹。 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梳着两条长辫子,眉眼和妹妹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妹妹“啊”了一声:“这是我娘年轻时候!这照片家里都没有,您怎么……” 师长摸出烟,点了两次才点着。“四二年,在鲁中。我受了重伤,躲在你娘家的地窖里。她照顾了我一个多月。”他吸了口烟,烟雾笼住脸,“后来我被转移,走得急,只留下这张照片,托人指话,说等太平了一定回来谢她。” 妹妹捏着照片,指尖发白。风吹过,树叶子沙沙响。 “我找过。”师长声音很低,“四九年回去,村子没了,人都散了。打听不到,都说可能不在了。”他抬起头,看着妹妹,“你娘……她后来怎么样?” “娘挺好。”妹妹声音也轻轻的,“就是常念叨,说有个同志伤没好透就走了,不知道落下病根没有。她前年走的,走的时候挺安详。” 师长夹烟的手停在那儿,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好一会儿,他才“嗯”了一声,把烟按灭了。“挺好。”他说,“那就好。” 那天下午,他破例没去忙,就坐在树下,听妹妹讲老家这些年的琐事,讲收成,讲村里的变化。他听得很仔细,偶尔问一句。夕阳把影子拉长的时候,他站起身,对妹妹说:“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你哥在,有什么难处,让他告诉我。” 妹妹走的那天,师长没来送,但让警卫员捎来一个结实的布包,里面是几包白糖,两块新布料,还有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妹妹抱着布包,眼圈红了红,没说话。 后来我给家里写信,娘回信说,师长托人往村里指了东西,没留名,但她一看那包东西的打结方式,就认出来了。“是那位同志。”娘在信里写,“他手巧,打的结跟别人不一样。” 我把信折好,窗外传来训练的号声。阳光明晃晃的,有些缘分,断了线,又被风吹着,悄悄打了个旋,接上了。
1955年我在部队刚提干,妹妹从老家坐三天火车来看我。我去营门口接她时,撞见了
勇敢的风铃说史
2026-01-29 23:27:16
0
阅读: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