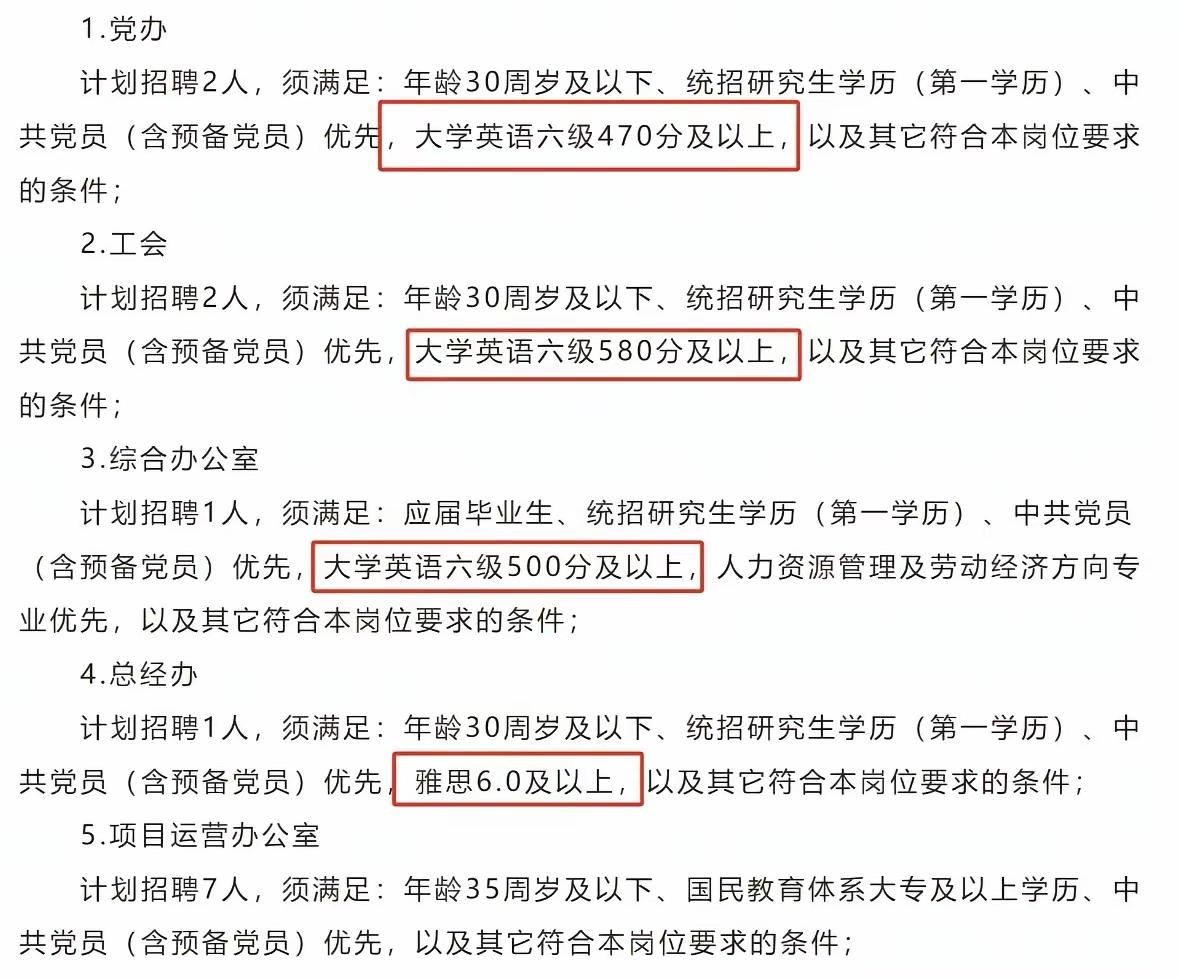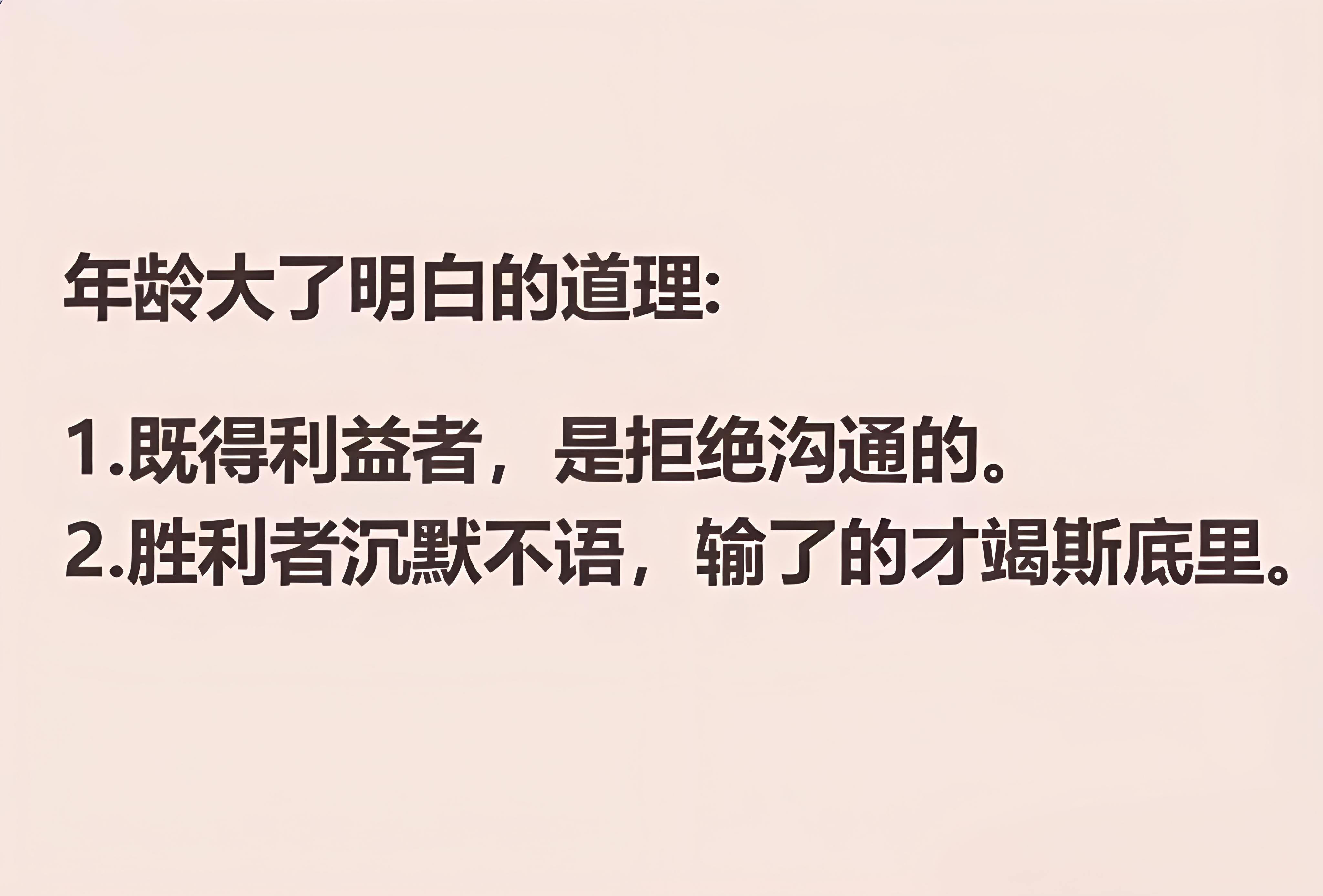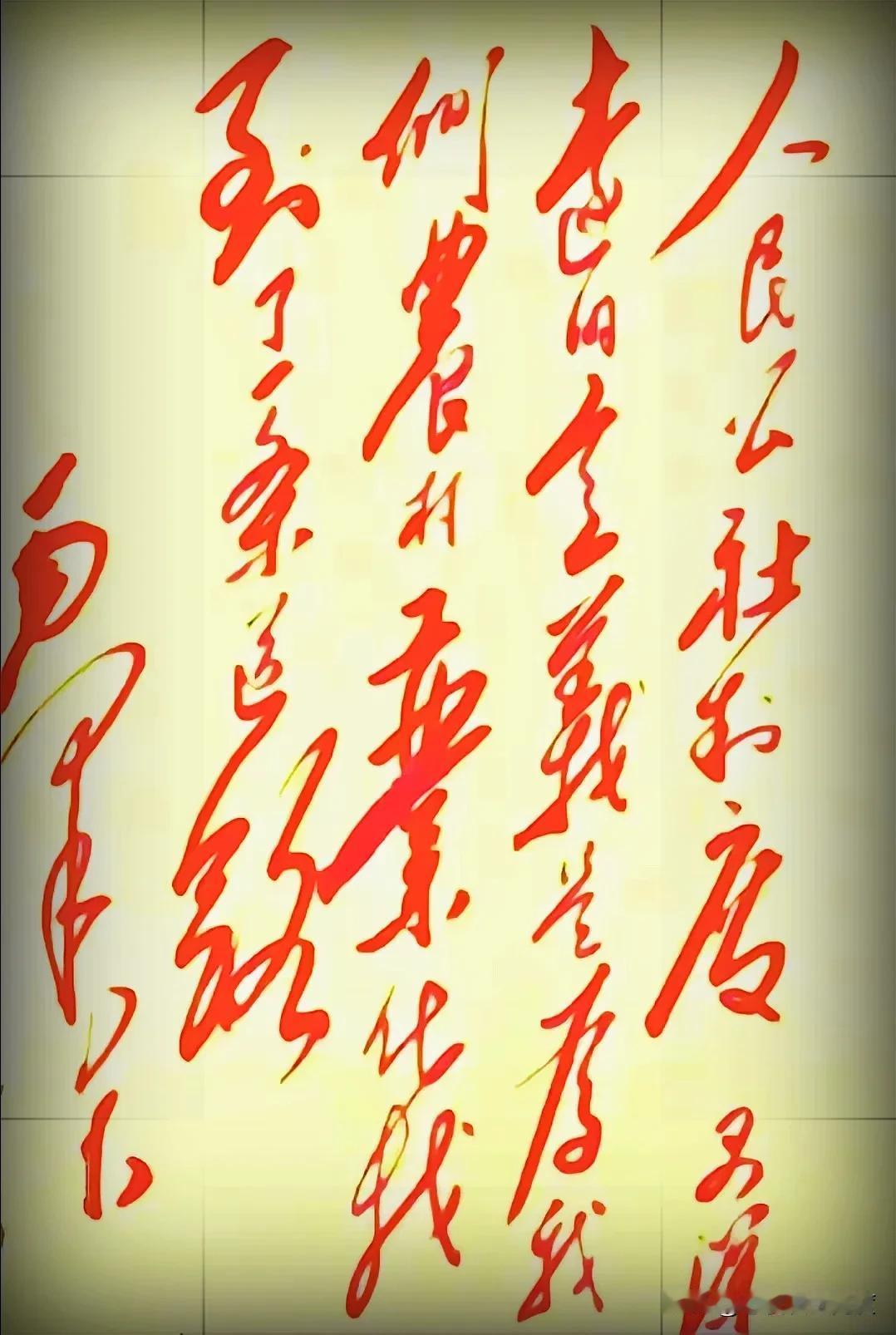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他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在这之前的很多个夜晚,他一遍遍在心里推演这一步。留在大陆,意味着与熟悉的山河和养育他的文化土壤不分离,却要面对不可预知的风浪;离开,则像亲手割舍掉一部分自己。作为画家,他离不开这片土地;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又必须为家人的安全筹谋。 有一晚,他把家人叫到一起,沉声说:“我们得走,是为了以后,也是为了让这些画还能活下去。”话不多,每个字却像压着千斤重。 徐雯波年轻、美貌,从前也曾因为种种龃龉离家出走,如今再站在命运关口,她同样没有十足底气。 但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从5岁起画到如今,从失去谢舜华时的短暂遁世,到拜曾熙、李瑞清门下,到远赴日本留学、游历名胜,又在敦煌洞窟里一笔一笔临写古画,她知道,他这一辈子是离不开画的。于是,她只是更用力地握紧了那只手。 真正让这次离开变得刻骨的,是那3张飞往台北的机票。 “心健怎么办,我不能丢下儿子。”在混乱的登机口,他一度红了眼眶。 最后,他还是咬牙,把年幼的张心健托付给相识多年的友人:“帮我照看他,就当是自己的孩子。” “你放心。”朋友郑重答应。他没再回头看,只在心里记下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亏欠。 飞机起飞时,他透过窗子,看着脚下的江山一点点缩小。那一刻,他感觉心被撕开,但他也清楚,画笔必须继续往前走。 离开大陆后的几十年,他几乎没有停下脚步。从台湾到巴西圣保罗,再漂泊到美国,真正安稳的日子少之又少。可无论身在何方,他都把敦煌临本带在身边,时常摊开,用指尖轻轻拂过,那是他与故土和传统保持联系的方式。 1941年在敦煌的那段时光,早已深深烙在他心里。壁画的色彩和气象,让他的用色和构图彻底打开。后来有人挑剔他的临本不够“原汁原味”,他说:“每个人心里有不一样的敦煌,我只画我看到的那个。”同样的固执,也支撑他在海外一次次重新开始。 流亡并没有削弱他的创作欲望,反而逼他不断突破。他一边扎根于中国画的传统,一边大胆吸收西方技法,在水墨、泼彩、甚至油画、水彩之间来回尝试。荷花画到极致,被称为“东方之笔”;在西方,评论界干脆用“东张西毕”来形容他与毕加索分庭抗礼的地位。 1969年,巴西的家园面临拆迁,他再度被迫迁徙。晚年,在宋美龄的帮助下,他终于回到台湾,在双溪盖起“摩耶精舍”。 那里不再是少年时的四川乡土,却成了他最后的落脚处。他把敦煌临本和一生心血整理出来,捐给博物院,算是为当年带画出关给出一个交代,也把自己嵌入到更长久的文化链条中。 到了生命后段,他体力每况愈下,病痛缠身,却仍几乎天天作画。客厅简朴,画案却从不空着。工作室对他来说,既是庇护所,也是小小的“敦煌”和“小四川”。 纵观他的一生,从四川贫家子,到与名门联姻、情感纠葛不断;从少年天才,到失婚、削发,再回尘世;从敦煌洞窟到海外漂泊,再到台湾的幽居,他的命运始终绕着两样东西打转:一个是画,另一个,是那条无论走多远都扯不断的中国线。 多年以后,国家文物局把他的书画列入限制出境名家名单,所有作品一律不得再出境。对张大千来说,这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家”。他的一生充满争议,却也凭着一管画笔,把自己的故事和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紧紧拴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