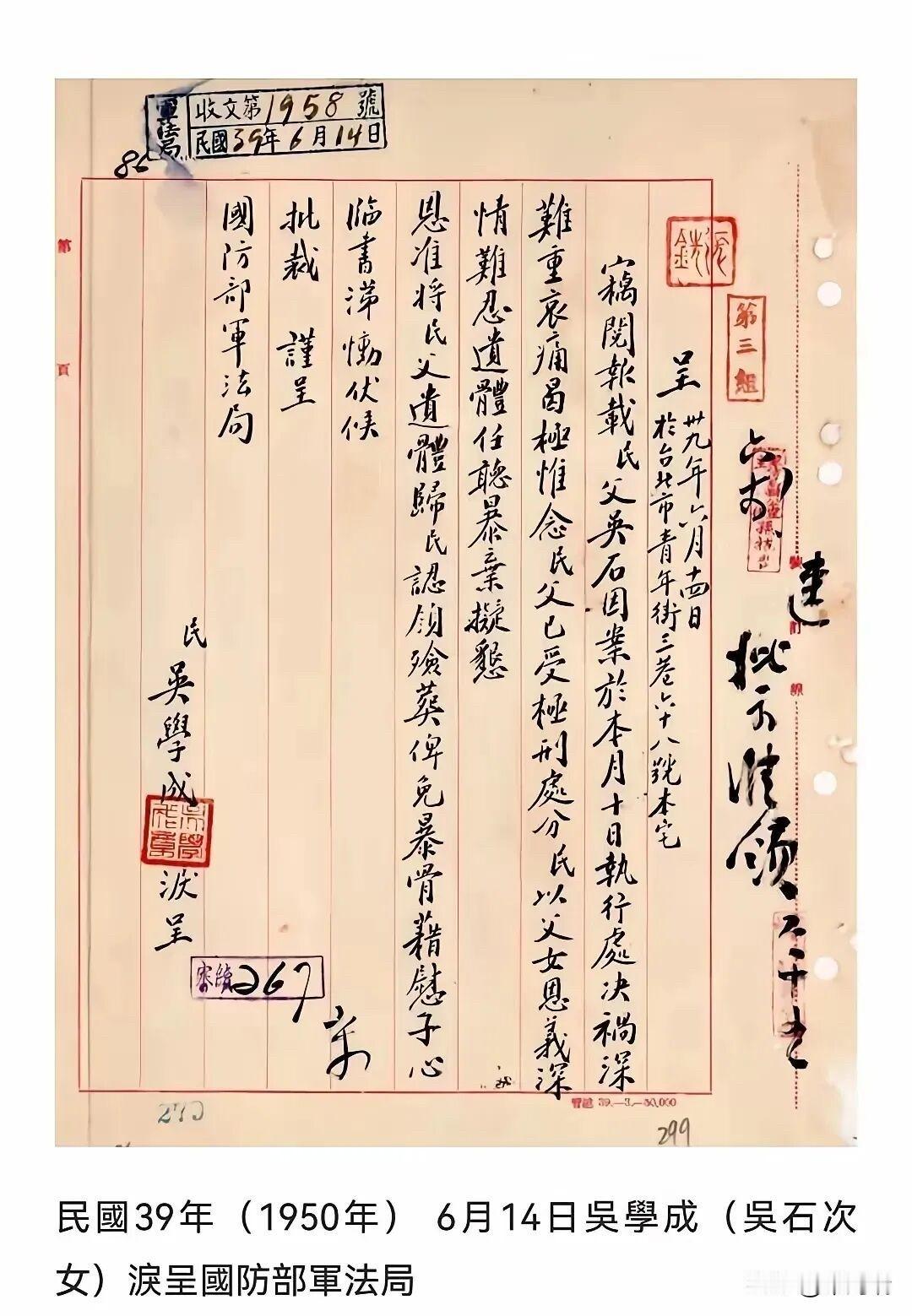1926年,19岁的杨蕴如嫁到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孙家,谁知,回门以后她死活不肯再回去:“白天斯斯文文的孙少爷,晩上怎么就变了样”? 天津有个大公主,叫杨蕴如。 父亲是天津银行行长,母亲出身名门。母亲怀过八胎,前面要么流产要么夭折,最后只活下两个孩子,她是老大,全家像供菩萨一样供着。 从小闯祸,父母舍不得骂,长辈帮着打圆场,下人收拾烂摊子。哄两句,事就过去。时间长了,脾气被惯得够呛,谁都让着,家里人叫她“大公主”,规矩没学几条,情绪倒是用得很顺。 那会儿有钱人家的姑娘都往学校送,她也坐着黄包车去上学。路上嫌颠,教室里嫌闷,书一翻就犯困。她赖在家里翻言情小说,把纸上的风花雪月当“人生教程”。 十七岁那年,父亲病重,心里明白这姑娘再这么养下去迟早要栽跟头,就在遗嘱里勒了条硬杠:不好好读书,就不许出门,不许嫁人,关在家里穿布衣。一个惯着女儿多年的父亲能写出这种话,是被现实吓透了。 父亲走后,家里说话算数的变成母亲。母亲心软,看着女儿掉眼泪,觉得遗嘱太重,慢慢就当没这回事。那个想拧方向盘的人不在了,大公主照旧想干嘛干嘛,书不读,脾气大。 一九二六年,她十九岁,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孙家的少爷。成亲那天,贺礼抬进抬出就有两百多担,孙家那条街被围得水泄不通,新娘一身婚纱,风光。 热闹散了,生活从洞房那间屋子开始。杨蕴如没人认真跟她讲过身体、婚姻这些事,只在小说里看过干干净净的爱情。新婚之夜,面对丈夫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她吓得浑身发抖,脑子里全是“肮脏”“野蛮”这类字眼,一个斯斯文文的孙少爷在她眼里成了怪物。 熬到回门那天,她扑在母亲怀里,哭着喊丈夫是禽兽,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孙家。后来孙家遇到经济风波,孙少爷到岳母家来借住,她当他是瘟神,不同屋,不同桌。危机过去,亲戚轮番劝,她勉强回到孙家,夫妻之间那道坎一点没填平,只要丈夫靠近,她就闹,闹到两家都受不了,只好登报离婚,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就此告吹。 婚离了,她心里还是憋着劲。妹妹考进燕京大学,成了人人夸的高材生,她不服,觉得自己凭什么矮一头。家里当银行行长的叔叔出面打招呼,给她弄到一个燕京大学的旁听名额。 她去宿舍看了一圈,嫌床硬屋挤,说住不了,非要住到叔叔家。寄人篱下谁都别扭,再加上她那点脾气,很快又搬出去,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房子离校园不近,她嫌坐黄包车灰大颠簸,索性租了汽车进出,教室里的课本还是进不去眼。 在燕京的日子,对她来说更像换了个地方遛弯。她经常在校园里溜达,走着走着,碰上了一位姓赵的学生。两个人很快成了情侣,干脆在她租的房子里同住。在那样的年代,姑娘跟人这样住在一起,就是一场不小的事,娘家只得赶紧给他们办婚礼,把这段感情包进婚姻的壳里。 娘家怕她在婆家受委屈,又给她陪嫁了一男一女两个仆人。 原本想着“有人照应”,落到日常却变了味。两个仆人常在她耳边嘀咕,说赵家的小伙子不过冲着钱来,人长得也不出挑,心思不见得正。这样的闲话,哪门婚事里没有几句,差别在当事人有没有自己的主心骨。 杨蕴如偏偏缺的就是这点。她不爱读书,从小听惯了别人哄她、顺着她的话,分不清哪句该听,哪句该当耳边风。仆人说一回,她心里添一层疙瘩,说得多了,她干脆认定丈夫靠不住,越看越不顺眼,最后把他告上法庭,起诉离婚,本该关上门处理的事扔到众目睽睽之下。 按道理,以她家的条件,就算两次婚姻都散了,衣食无忧还是不成问题。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跟钱只占一部分关系,剩下的看心性,看挨打时能不能站起来。她从小没遇过什么风浪,也没人教她怎么面对失败。两场婚姻像两记闷棍,把她砸得找不着方向,日子一天天塌下去,到了四十二岁,人彻底精神失常。 一个神志不清的中年女人,家里有佣人,照顾也谈不上温柔。打骂、嫌弃,很难躲开。母亲再爱她,也不可能一辈子守在床边,更挡不住自己年老离世。那些年少时“想干嘛干嘛”的潇洒,到这一步就只剩下苦味。 回头看她这一生,出身好,条件好,却没有学识,没有判断力,也没有面对挫折的筋骨。 父亲临终那纸遗嘱,说的就是不想让女儿被“快乐长大”的幻觉拖走,只可惜停在纸上。真正能护住一个人,不是“有钱就行”“开心就够”,而是懂点道理,能看清人心,遇见风浪不至于一跪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