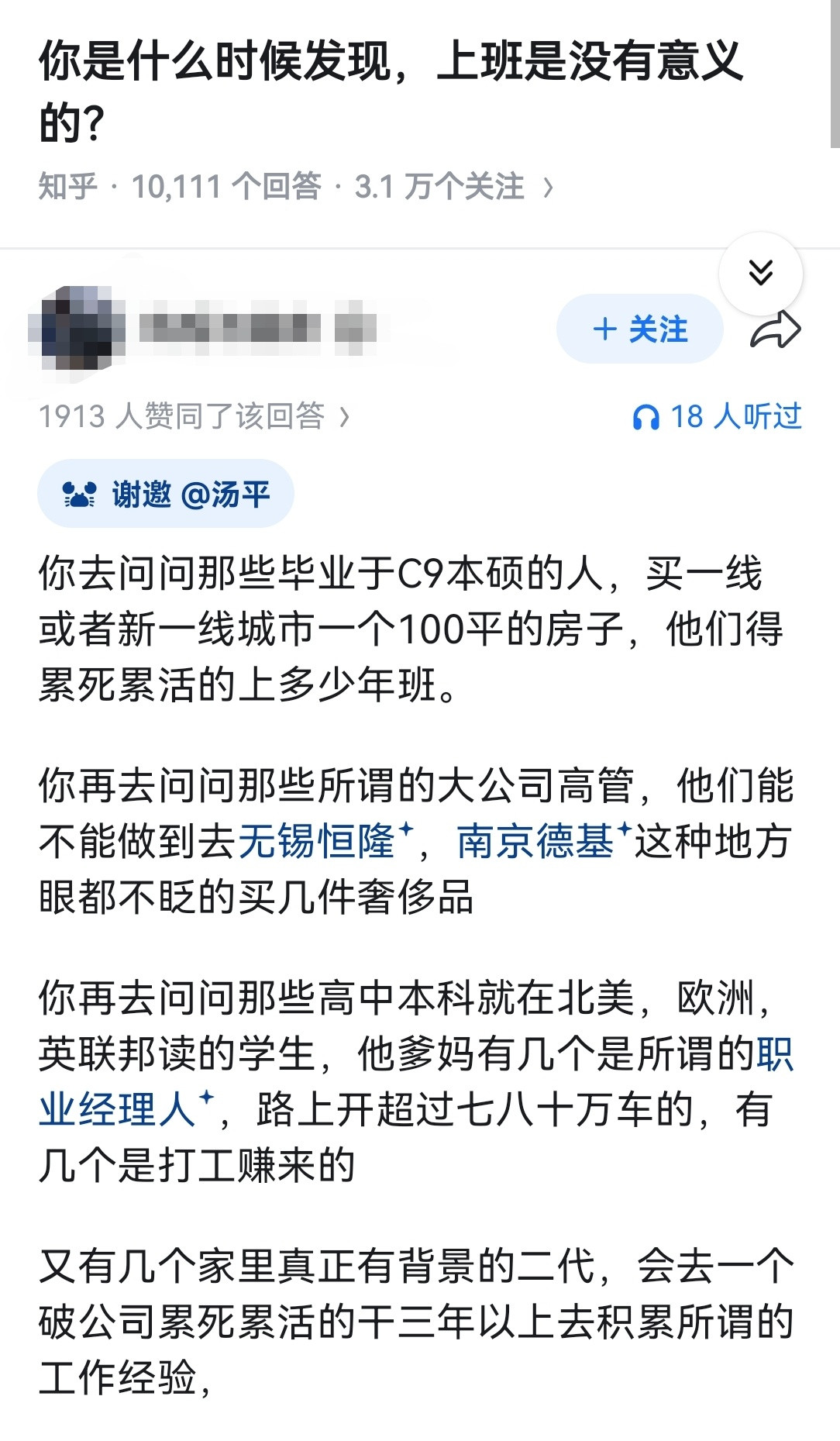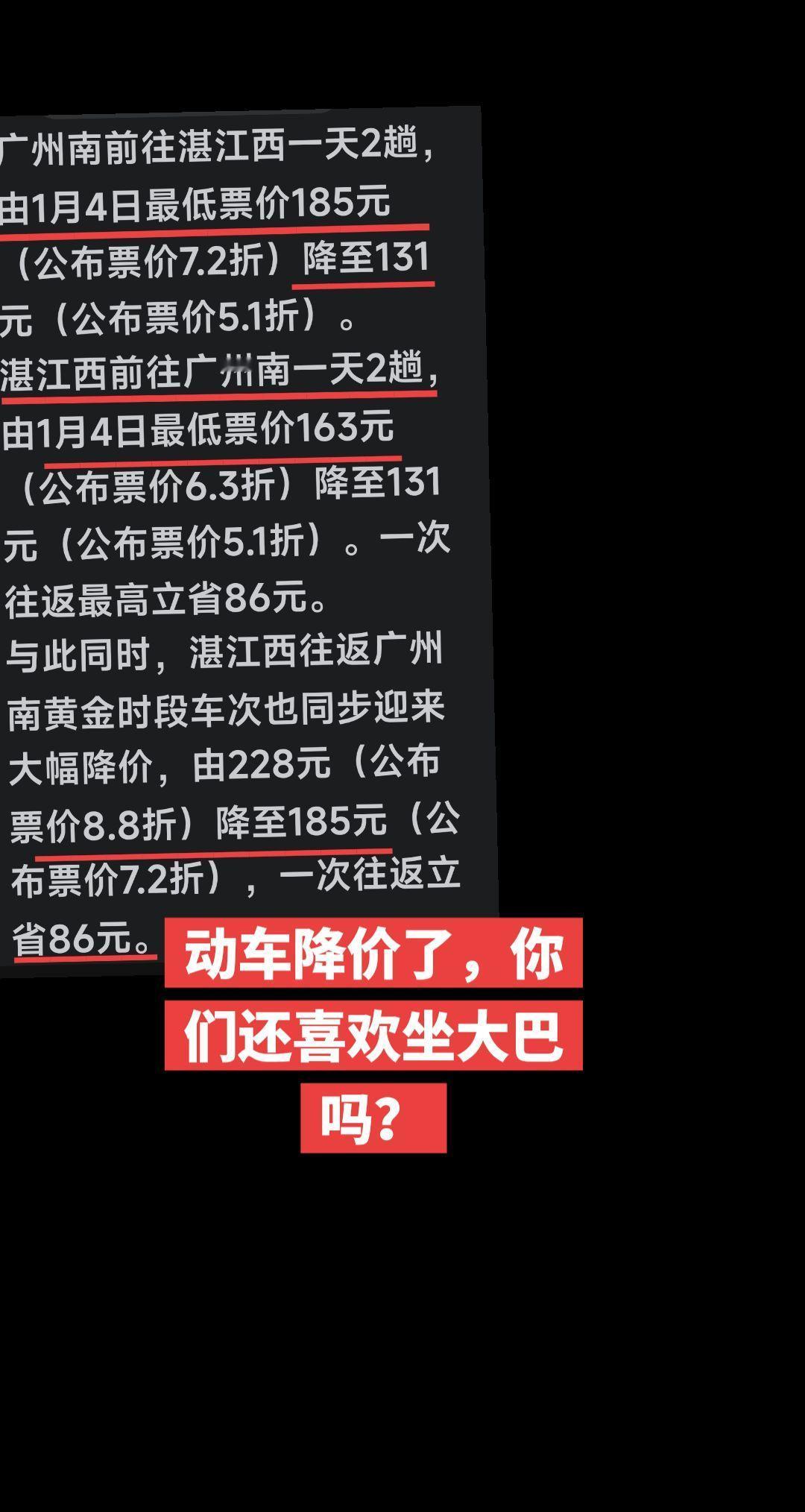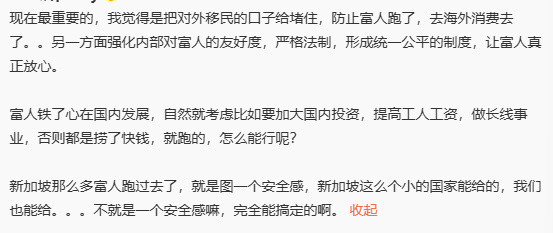我相信善有善报,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遗传了我外婆的中医术,但她不认识字,所以没当成医生,但却帮了很多人。 现在妈妈七十多了,膝盖不太好,爬不了山采草药,可她的手从没闲着,天天坐在堂屋的老藤椅上纳鞋垫。 窗台上那盆绿萝旁边,总堆着花花绿绿的碎布——都是街坊裁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有的带着小碎花,有的印着格子纹,被妈妈用碱水搓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码在竹篮里。 我劝过她:“妈,您眼睛都花成这样了,歇着吧,超市里十块钱三双的鞋垫多的是。”她却把银闪闪的顶针往手指上一套,手里的钢针穿着枣红色的线在布面上扎:“那能一样?你李婶脚底板有老茧,我给她纳双带艾草绒的,走路能软和点。” 其实我知道她是心里空——自从前年爸爸走后,她夜里总睡不着,直到开始摆弄这些碎布,床头的小夜灯才亮得晚了些。 刚开始送鞋垫时,真有人推托。对门王阿姨就笑着摆手:“嫂子,您这手艺是真好,可太费神了,我们哪好意思总拿。” 妈妈也不勉强,就把鞋垫用保鲜膜包好,放在人家门口的石阶上,上面压块小石子——怕被风吹跑,第二天早上再看,石阶准是空的,再碰到王阿姨,她脚上准踩着那双带蓝格子的,见了妈妈就拍大腿:“你做的鞋垫跟长在脚上似的,走二里地脚脖子都不酸!” 去年冬天特别冷,村东头的留守儿童小宇,爸妈在外地打工,跟着奶奶过,孩子的鞋薄,脚后跟冻得裂了口子,渗着血珠。 妈妈知道了,连夜翻出我给她买的羊毛衫拆了,又找出外婆留下的旧棉絮,纳了双厚厚的鞋垫,针脚比平时密了一倍,边边角角还绣了只小兔子——小宇属兔。 第二天一早她催我给小宇送去,我看着她眼角的细纹里还带着红血丝,心里有点发酸:“妈,您至于吗?买双棉鞋才多少钱,您这熬半宿眼睛还要不要了?” 妈妈没抬头,正用牙咬断最后一根线头,嘴里嘟囔着:“钱能买鞋,买不来这针脚里的暖和——你外婆以前给我做鞋,也是这么一针一线纳,说针脚里藏着心意,穿上的人能感觉到。” 这话我信,我小时候的鞋垫全是妈妈做的,冬天脚伸进鞋里,就像踩着团棉花,从脚底板暖到心口窝。 可那天我还是忍不住多嘴:“那您也不能天天这么熬着啊,上次体检医生都说您要少费眼。” 妈妈停下手里的活,从藤椅旁的木箱里翻出个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一沓纸——有的是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有的是画着小红花的卡片,最上面那张是小宇奶奶送来的,说孩子脚好了,还画了个咧嘴笑的太阳。 “你看,”她指着那些纸,眼睛亮得像盛了星星,“这些东西,比啥补药都管用,看着心里就热乎。” 上个月我回老家,发现妈妈的窗台上多了个新竹篮,里面堆着街坊送的东西——张叔地里刚摘的黄瓜,刘奶奶蒸的红糖馒头,还有小宇用攒的零花钱买的老花镜,镜框上还挂着个塑料小老虎挂坠。 我拿起那副老花镜,镜片擦得锃亮,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我总想着给她买贵的按摩仪、进口钙片,却忘了她最想要的,是这份被人惦记的暖。 妈妈见我对着眼镜发呆,走过来帮我把耷拉下来的碎头发别到耳后:“你外婆说过,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你对人好,人心里记着呢。” 现在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妈妈都会说“今天给你赵奶奶纳了双软底的,她风湿犯了,鞋底软和点能少疼点”,或者“小宇今天来家里了,说要跟我学纳鞋垫,说以后给他爸妈做”。 你说这一针一线的鞋垫,值几个钱呢?或许不值什么钱,但那份坐在藤椅上,眯着眼穿针引线的认真,那份把碎布头变成暖脚物的心意,比啥都金贵。 妈妈常说“人老了,别的帮不上,动动手还能行”,可我知道,她不是帮不上——她是把年轻时没当成医生的遗憾,都变成了手里的线,缝进了一双双鞋垫里,也缝进了每个人的日子里。 现在我的包里总放着一双妈妈做的鞋垫,摸着上面细密的针脚,就像能看见她坐在窗边的样子,阳光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钢针在碎布上闪着光,那一刻我突然懂了——善有善报,不是非要得到什么,而是你用心对别人,别人也会用心对你,就像这鞋垫,脚暖了,心也就跟着暖了。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
【1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