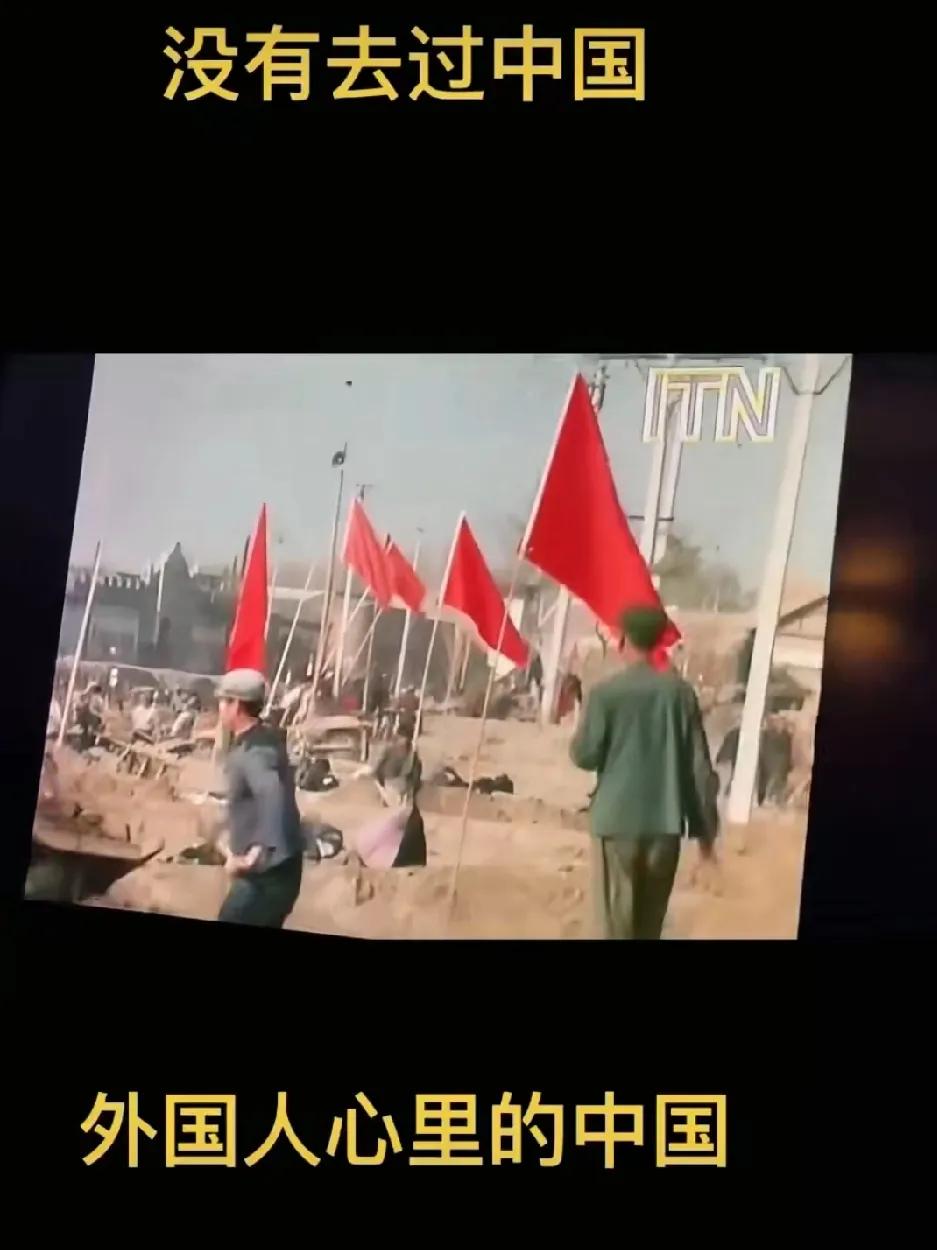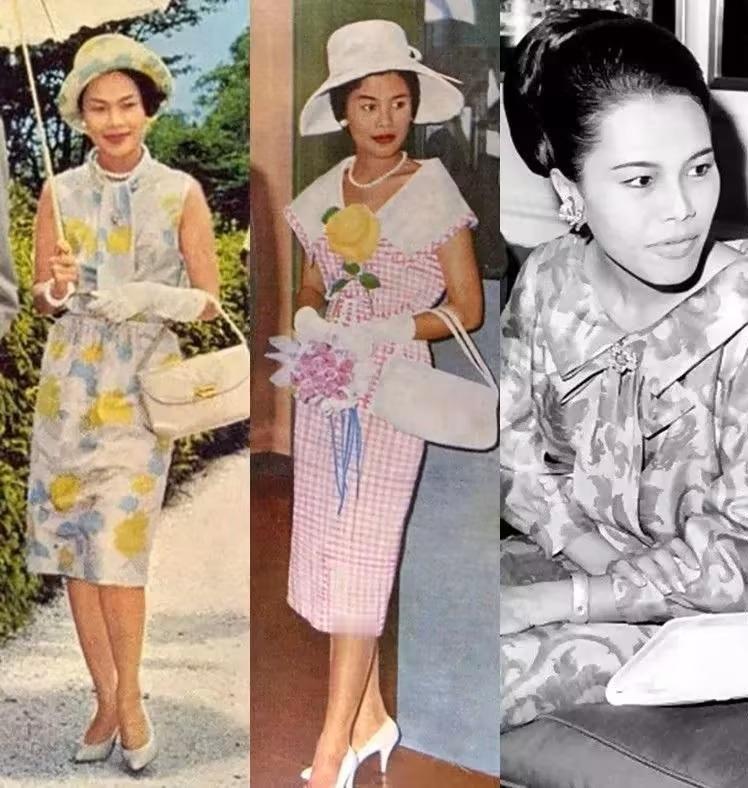1952年6月2日,25岁的伊丽莎白在伦敦西敏寺登基,成为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到2022年,9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在位70周年,这一时间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皇帝国王。 70年。这是什么概念?一个人从出生到古稀之年。而伊丽莎白二世,她把这70年,完完整整地“焊”在了女王这个位置上。 她去世的时候96岁,这意味着她生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女王”。这工作,没退休金,没下班点,全年无休,而且是全球直播。 说实话,这顶王冠,一开始都不是冲着她来的。 她爹是乔治六世,就是电影《国王的演讲》里那个口吃的国王。而他爹能当上国王,是因为他哥,也就是女王的伯父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娶辛普森夫人,愣是把王位给撂了。 所以,伊丽莎白10岁那年,命运的剧本突然改写。她从一个普通的公主,“被动”成了王位第一继承人。 正是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责任,让她对“职责”二字看得比天还大。她21岁生日时发过一个誓言,那句话成了她一辈子的注脚:“我的一生,无论长短,都将为公众服务。” 她说到,也做到了。 1952年,老国王乔治六世去世,25岁的伊丽莎白正在肯尼亚访问。她上山时还是公主,下山时,已经是女王。 她接手的英国,可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二战刚打完,国家穷得叮当响,“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一个个闹独立,眼看就要分崩离析。 她的加冕典礼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电视转播的。这事儿在当年特别前卫,也特别有象征意义——这个古老的王室,打算换个活法,得跟上时代了。 大家老说一句话,叫“流水的首相,铁打的女王”。 这话太对了。从她登基到去世,英国换了15个首相。她任命的第一个首相,是丘吉尔。那会儿丘吉尔都快80了,是看着她长大的“爷爷辈”,也是她的政治导师。而她任命的最后一个首相,是特拉斯。任命特拉斯两天后,女王就去世了。 从丘吉尔到特拉斯,这中间跨越了多少风风雨雨?冷战、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政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她,永远坐在那里,像个“定海神针”。 但你别以为她这个“针”好当。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女王,她最大的权力,就是“没有权力”。 她的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象征”国家。她必须保持绝对中立。每周跟首相开会,她可以提建议,可以给忠告,但绝不能干政。 这种“克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王室自己出事的时候。 女王这辈子,最大的坎儿,恐怕就是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 戴安娜车祸消息传来,举国悲痛。但女王做了什么?她待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没第一时间回伦敦,白金汉宫也没按规矩降半旗。 这一下,民意炸了。媒体和民众铺天盖地地骂她“冷漠”、“不近人情”。这是她70年统治里,最严重的一次公关危机。 为什么她会这么“迟钝”? 这就是她那一代人的“王室体面”。她受的教育是,王室成员要有距离感,不能轻易表露情绪。更何况,戴安娜当时已经离婚,不再是王室成员了。 但她没料到,时代变了。民众不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需要一个能共情的“大家长”。 最后,女王妥协了。她赶回伦敦,在成堆的鲜花前亮相,并且发表了那次著名的电视讲话。她用“祖母”的身份,安抚了民众,也挽救了王室。 从那以后,女王的形象也悄悄变了,开始变得更“亲民”。 她也不是没犯过错。比如1966年艾伯凡矿难,死了100多个孩子,她隔了8天才去现场。很多年后她自己都说,这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她这70年,就是不断在“古老传统”和“现代社会”之间找平衡。 她访问过100多个国家,是英国史上出访最多的君主。1965年,二战结束20年,她访问西德,那次访问被看作是英德“世纪和解”。1986年,她是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英国君主,还登上了长城。 她见证了帝国解体,却努力维系着“英联邦”这个松散的大家庭,让英国的“软实力”得以延续。 到了晚年,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又站了出来。 当时英国全国封锁,人心惶惶。90多岁的女王发表了一次特别演讲。她没说太多大道理,只是平静地回忆起二战,最后说了一句:“我们将和朋友重逢,和家人团聚,我们后会有期。” 她的一生,是献祭给了“王冠”的一生。她几乎没有“自我”,只有“女王”这个角色。她用70年的时间,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极致的“敬业”与“隐忍”。 她走了,也带走了一个时代。那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最后一块遮羞布,也算是落下了。至于她的儿子查尔斯,能不能接好这个班,那可真是个大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