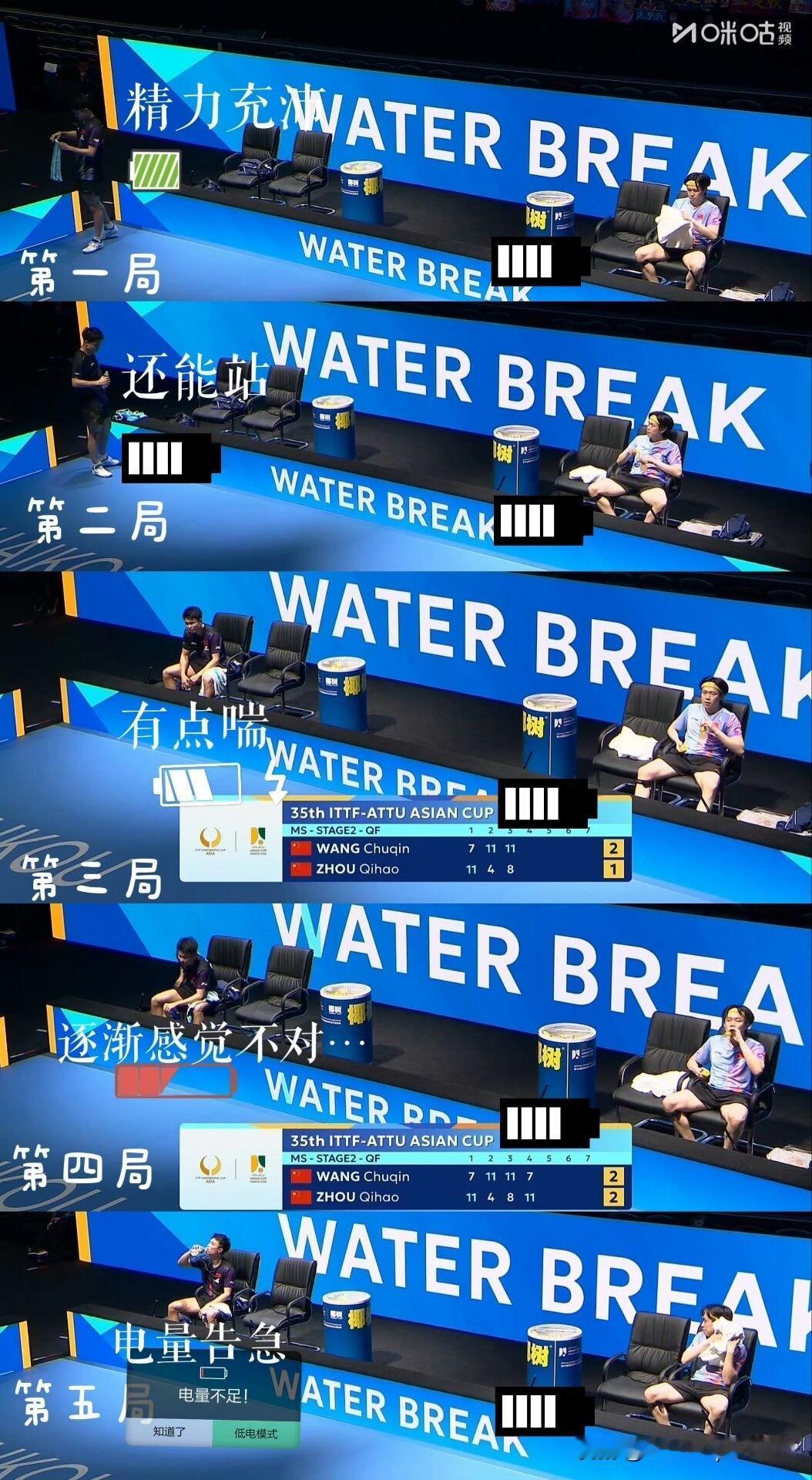我们船上有个水手,不是一般的坏,是坏到骨子里的坏,他的所作所为,让从不爆粗口的我,都忍不住骂他,畜牲不如。 他叫赵四。那天船过芜湖,江上起了点薄雾,厨房老陈炖了一锅红烧肉,满船都是香味。大家都挤在小小的餐厅里,说说笑笑。赵四扒拉完自己那份,眼睛就滴溜溜转,最后落在王姐碗里——王姐胃不好,肉没动几块。他嬉皮笑脸凑过去:“王姐,不吃可惜了,我帮你打扫了吧?”不等回答,筷子就伸了过去。王姐张了张嘴,没吭声,低头喝汤。 晚上我值夜班,驾驶台就我一个人,江风凉飕飕的。大概凌晨两点,我听见甲板上有动静,很轻。摸出去一看,月光底下,赵四蹲在缆桩旁边,不知道在捣鼓什么。我心里一咯噔,这孙子别又在破坏啥。我悄悄靠近,却看见他面前摆着个不锈钢饭盒,就是王姐平时用的那个。他正把一块块用干净塑料袋包好的红烧肉,仔细码进饭盒里。然后起身,轻手轻脚走到王姐住的舱室门口,把饭盒放在门边。 我愣住了,躲在阴影里没出声。他转身往回走,路过我这边时,嘴里还哼着荒腔走板的小调,差点跟我撞个对脸。他吓了一跳,手电光晃在我脸上。“哥……你、你在这儿啊。”他有点慌,下意识想挡身后的门。 “干嘛呢?”我问。 “没……没干嘛。”他挠头,那副惯有的嬉笑又堆上来,“晚上吃咸了,出来溜达溜达。” 我没戳穿他,点点头回了驾驶台。过了十几分钟,我透过窗户,看见王姐舱门开了条缝,一只手快速把饭盒拿了进去。 第二天早上,王姐眼睛有点肿,但精神头挺好。吃早饭时,她盛了碗粥,小声跟老陈说:“陈师傅,昨晚的红烧肉……我热了热当夜宵,味道真好。”老陈有点懵:“啊?你不是没吃几块吗?”王姐笑了笑,没再说话,低头喝粥。 赵四还是那副德行,上午偷喝了小杨藏在冰箱里的可乐,下午又把刘哥的烟灰弹进了花盆里。只是我偶尔会想起凌晨甲板上,月光照着他码放肉块的侧脸,那神情挺专注,甚至有点笨拙的认真。船继续在江上走着,风扇在驾驶台角落里吱呀呀地转,江水声一成不变。我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就像江上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雾气,看见了,也就散了。
我真没时间在这陪你胡闹了!
【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