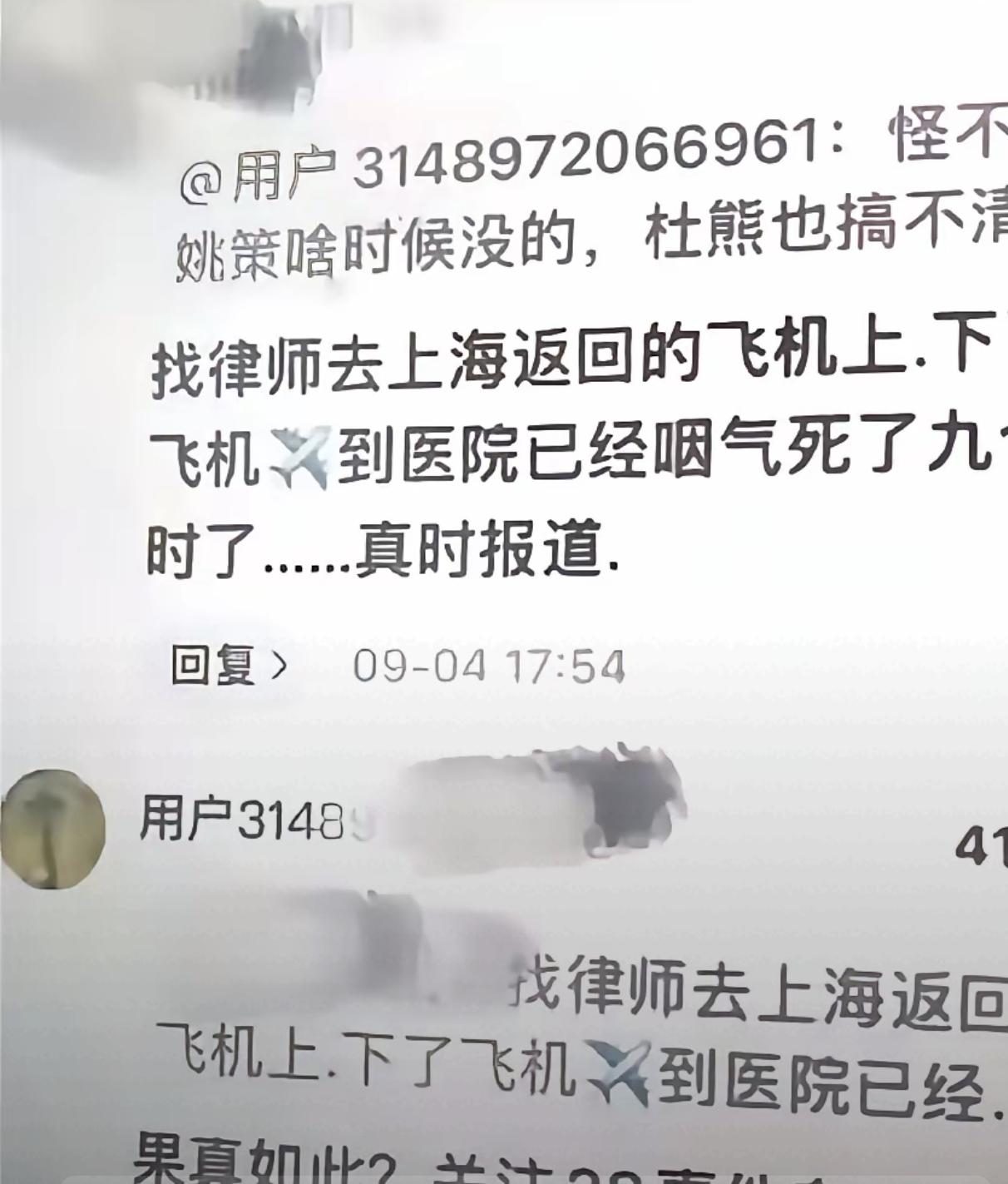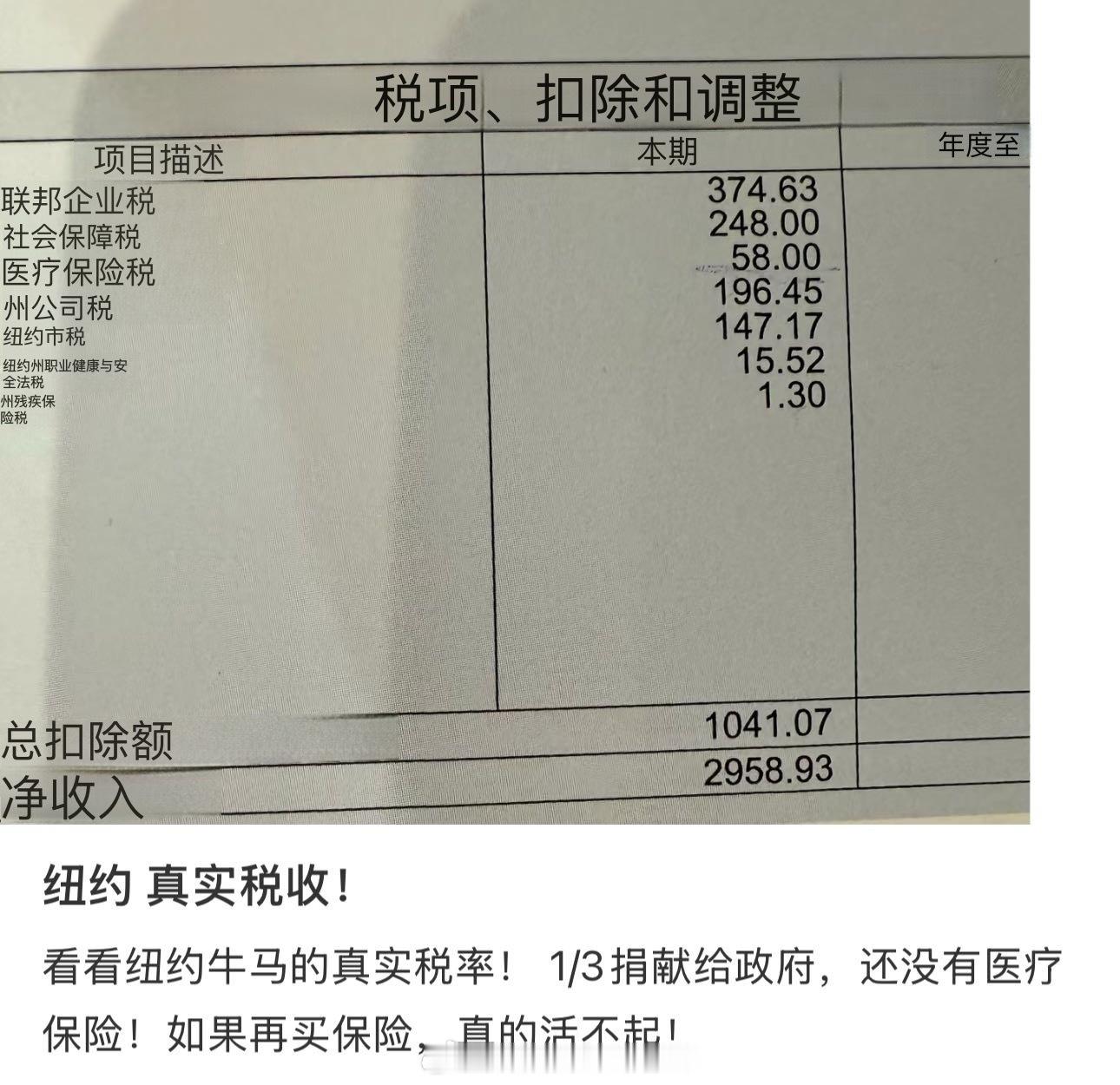我出生在1965年,打记事起就跟着父母在公社的生产大队里生活。那时候全村人都在一个集体里干活,挣工分换粮食。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要是没有公社的互助政策,光靠我爹娘俩,我们兄妹四个根本填不饱肚子。 我十岁那年的夏天,爹在修水渠时被石头砸伤了腰,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娘一个人挣的工分,根本不够换六口人的粮食。那个傍晚,我听见娘在灶房偷偷抹眼泪,心里跟针扎一样。第二天一早,大队长老李叔就扛着半袋玉米面来了,后头跟着会计王伯,手里拿着个小本子。“柱子家的,别犯愁。”老李叔把面袋子放下,“队里开了会,柱子是为公家受的伤,养伤期间工分照记,粮食先预支。孩子们正长身体,不能饿着。” 从那天起,我家院门就没冷清过。东头的张婶端来一碗她腌的咸菜,西院的赵妈送来几个刚摘的茄子。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邻居春生哥,他媳妇刚生了娃,自家也紧巴,却总在晚饭后溜达过来,从怀里掏出个还温乎的煮鸡蛋,塞给我小妹,“给娃补补身子。”我娘推辞,春生哥就瞪眼:“嫂子,当年我爹没了,要不是柱子哥帮衬,我们娘俩能活下来?再说,这蛋是咱公社鸡场下的,是大家伙的。” 爹养伤的那三个月,我们一家没饿过一顿肚子。秋收后,爹的腰好了些,虽说不能干重活,老李叔安排他去给队里看果园,活儿轻省,工分也不少记。爹每天早早出门,回来时,布兜里总装着几个被风吹落的、有点疤瘌的果子,那是队里允许带回来给娃们解馋的。我们兄妹四个,依然每天一起去公社小学念书,学费?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东西。 时间一晃就到了八十年代初,公社要解散的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村子。那天晚上,爹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烟,最后对娘说:“心里是有点空落落的。可你也别说,要不是那几年公社撑着,咱这个家早就散了。” 分了地以后,爹娘起早贪黑地伺候自家那几亩田。日子确实一天天好起来,饭桌上能见着荤腥了,我们也陆续长大成人。我后来进了县里的农机厂,厂里的医务室,我头一回进去就觉得眼熟,那格局、那味道,像极了小时候公社的卫生所。一打听,老医生笑着说:“咱们这儿,前身就是附近几个公社合并的卫生院啊。” 去年,老李叔过世了,全村能回来的人都去了。春生哥也老了,头发花白,他拉着我的手说:“现在日子是好喽,可咱不能忘了本。那会儿大家是真穷,也是真抱团儿啊。”我点点头,看着远处那片如今已承包给个人的果园,想起爹看果园时带回的那些有点歪扭却特别甜的果子。
我出生在1965年,打记事起就跟着父母在公社的生产大队里生活。那时候全村人都在一
好小鱼
2026-01-25 15:55:18
0
阅读: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