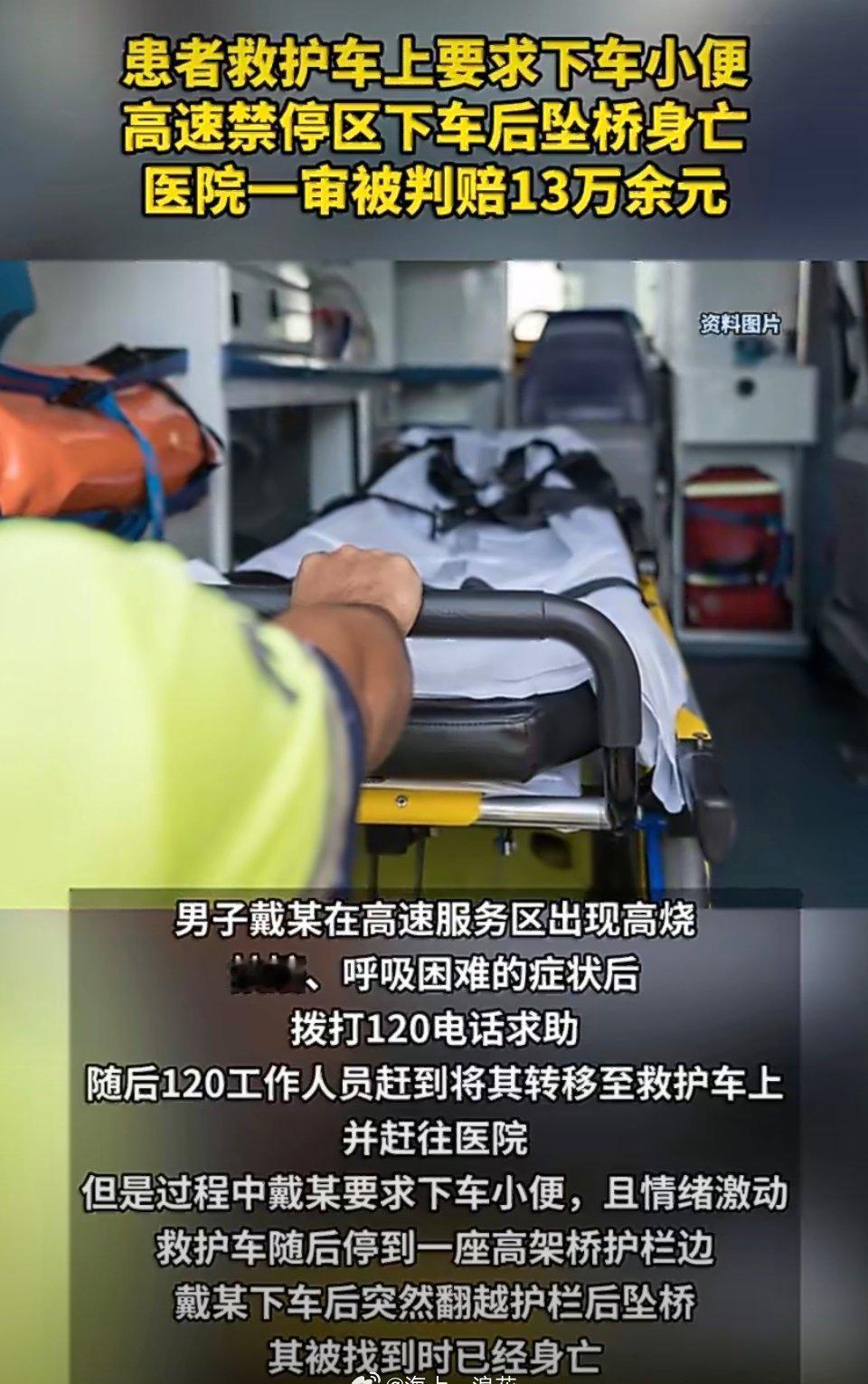从前,一和尚在一姓冯的人家借宿。半夜,和尚起来撒尿,竟一脚踩空,掉到了枯井里。待天亮冯家人将和尚救上来时,却发现儿媳竟也死在了枯井中。冯老爷顿时大怒。冯老爷看着井里的情景,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他指着和尚,手抖得厉害,唾沫星子喷了满脸。周围的邻居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眼神里全是探究和鄙夷。 那夜的月光,白惨惨地洒在冯家后院。 我是个云游的和尚,走了一天山路,便在山下冯家住了脚。 冯老爷五十来岁,脸上沟壑纵横,看我的眼神带着几分审视,倒也没多说什么,指了间柴房让我歇脚。 夜里起夜,院里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和自己的脚步声。 走到后院那棵老槐树下,脚下突然一空,我像个破麻袋似的摔了下去,还好底下是松软的泥土,只是头磕在井壁上,晕乎乎的。 不知过了多久,天蒙蒙亮时,我才被一阵嘈杂声惊醒。 “爹!井里有人!是……是和尚师傅!”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带着惊慌。 接着是辘轳转动的声音,绳子垂了下来,我抓着绳子,被七手八脚地拉了上去。 阳光刺眼,我眯着眼,还没站稳,就听见冯老爷一声凄厉的叫喊:“兰儿!我的兰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井里一看,我浑身的血瞬间凉透了——井底下,冯老爷的儿媳,那个昨天还端茶送水、低眉顺眼的年轻女子,静静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脖子上似乎还有勒痕。 冯老爷的脸“腾”地一下红了,不是害羞,是气的,红得像庙里的关公,又慢慢变成了猪肝色。 他指着我,手指头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话,唾沫星子倒是喷了我一脸:“你……你这个贼秃驴!我好心留你住宿,你……你竟敢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情!”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围的邻居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围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像看耍猴似的,对着我指指点点,那些眼神,有好奇,有鄙夷,有愤怒,像一根根针,扎得我浑身难受。 “啧啧,出家人怎么能干这种事?” “就是,看着人模人样的,没想到是个衣冠禽兽!” “冯家真是倒霉,好心没好报啊!” 我蹲在地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只有一个念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我半夜掉下去的时候,井里除了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掉下去之后就晕了,就算我想做什么,也没那个时间和力气啊! 冯老爷的儿媳,她为什么会在井里?她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 冯老爷气得浑身发抖,他冲上来就要打我,被几个邻居死死拉住了。 “爹!先别冲动!”冯少爷,也就是死者的丈夫,还算冷静,“报官吧!让官府来查!” 冯老爷喘着粗气,狠狠瞪了我一眼,对家丁说:“把他给我看好了!别让他跑了!” 我像个木偶似的被家丁绑了起来,扔在柴房的角落里。 阳光从柴房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地上,形成一道道光斑,可我却觉得浑身冰冷。 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都没人信。 一个和尚,半夜掉进井里,井里还有个死了的年轻儿媳,任谁都会觉得是我干的。 这事儿太蹊跷了。 我掉进井里是个意外,冯儿媳死在井里,难道也是意外? 还是说,她是被人推下去的?如果是被人推下去的,那凶手是谁?凶手为什么要杀她?又为什么要把她扔进这口枯井里? 难道凶手早就知道我会掉进这口井里?这不可能!我自己都是不小心才掉下去的。 那就是,凶手杀了人,刚好把尸体扔进了这口枯井,而我又刚好掉进了这口井里,成了替罪羊? 这个可能性很大。 可谁又能说得清,这深不见底的枯井,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冯老爷因为女儿的死,悲痛欲绝,又因为我这个“嫌疑人”的存在,愤怒不已,他现在只想让我为他女儿抵命,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 邻居们呢?他们大多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或者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我就是凶手,他们的指指点点和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 我一个出家人,四大皆空,本不怕这些流言蜚语,可我不能背负这样的污名,毁了佛门的清誉。 很快,官府的人就来了。 县太爷带着几个衙役,勘查了现场,验了尸,又把我和冯老爷、冯少爷以及几个邻居都问了一遍。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从借宿,到起夜,到掉井,再到被救上来发现尸体。 县太爷捋着胡须,眉头紧锁,也没说信,也没说不信。 他让人把我押回县衙大牢,等候发落。 我知道,我的麻烦还没结束,这口枯井里的秘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揭开的。 这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看似一目了然,背后却可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真相。 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的全部。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尤其是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 否则,很可能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可能会放过一个坏人。 就像此刻的我,明明是个受害者,却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那口枯井,白天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废弃井,可到了晚上,在月光下,它就像一张择人而噬的巨口,吞噬了生命,也吞噬了真相。
昨天,管子拔了。人当场就没了。48岁,在ICU里躺了整整40天,花了差不多30万
【36评论】【1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