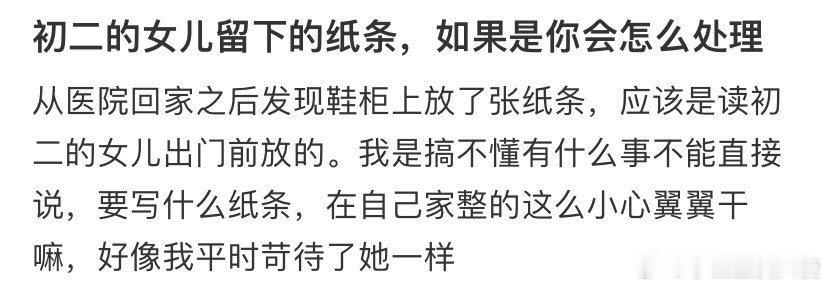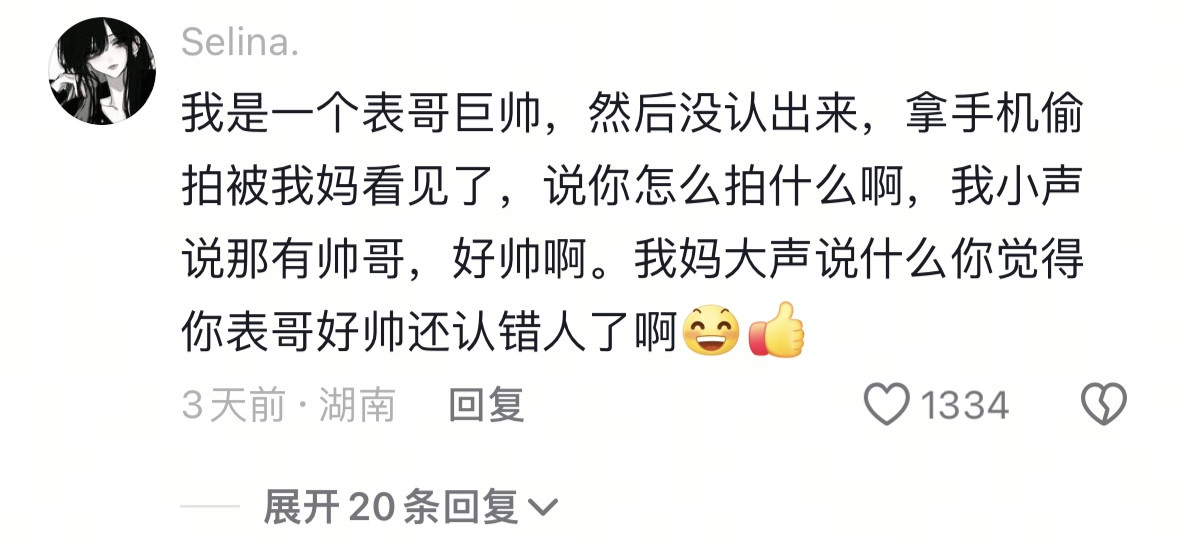我家大塘下的水稻田里有块巨石,多年来碰断父亲好几把犁头,他又气又无奈。直到今天,新犁头再被碰坏,父亲终于下决心处理它。父亲把断成两截的犁头扔在田埂上,蹲下来摸了摸那块石头露出的尖角,土黄色的石头被水泡得发滑,指尖能感 我家大塘下的水稻田中央,卧着块磨盘大的石头,青黄相间,像头不肯挪窝的老黄牛。 从我记事起,它就横在那儿,每年春耕秋收,父亲的犁头总得跟它硬碰硬——断口处新锈叠旧痕,木柄裂开的纹路里嵌着干泥。 今早我去田埂送饭,还看见去年断的那把犁头靠在墙角,铁尖豁了个口子,像咧着嘴笑。 其实父亲年轻时试过挖它,三十年前,刚分田到户那会儿,他拿铁锨刨了半宿,石头纹丝不动,倒震得虎口发麻。 后来他就认了,耕地时绕着走,嘴上骂骂咧咧,“这狗娘养的石头,专跟我过不去”,却从没真动过搬走的念头。 直到今天上午,新犁头是开春刚买的,亮闪闪的,父亲说“这把能顶三年”,结果第三趟就撞上了——“咔嚓”一声,铁犁断成两截,木柄弹起来差点打他脸上。 他没像往常那样摔东西,只是把断犁头往田埂上一扔,咚地一声,惊飞了埂边的麻雀。 然后蹲下去,手指顺着石头尖角慢慢摸。 土黄色的石面被水泡得发滑,指尖能触到细小的凹坑,那是雨水和岁月凿出来的印子,凉丝丝的,像摸着块老骨头。 我蹲在田埂上看他,突然想起奶奶说过,这石头是以前发大水冲下来的,那年要不是它挡着,田埂早被冲垮了,咱家那亩最肥的田,说不定就成了塘底。 父亲大概也想起了什么,摸石头的手停了停,指腹在凹坑里轻轻碾了碾。 新犁头断了是事实,可这石头,也替咱家扛过事啊——他突然叹了口气,声音轻得像风吹过稻叶。 中午他没回家,从邻家借了镐头,一下下凿石头边的泥。 泥是湿的,带着水腥气,镐头下去,“噗”地冒个泡,混着碎草和小虫子。 也许过几天石头真能挪走,田里再不用绕着走,犁头能直直地从这头耕到那头。 但我忽然觉得,父亲蹲在那儿的样子,不像在跟石头较劲,倒像在跟多年的自己告别。 有些东西横在心里久了,以为是麻烦,其实早成了习惯——你说,人是不是都这样? 傍晚我再去时,石头周围已经挖了个半人深的坑,父亲脱了鞋站在泥里,裤脚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泥点,夕阳照在他背上,汗珠子亮晶晶的。 他举起镐头,又停住,回头冲我笑:“这老东西,底下比上头还大呢。” 风从塘面吹过来,带着稻花香,石头的尖角在暮色里泛着光,像在回应他的话。 也许明天它还在那儿,也许下个月就不在了。 但我知道,父亲摸过那块石头的指尖,会一直记着那份滑溜溜的凉,和凉底下藏着的,三十年的光阴。
一个母亲到死都没有获得孩子的原谅前几天徐阿姨走了,她女儿没有回来送她最后一程,
【31评论】【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