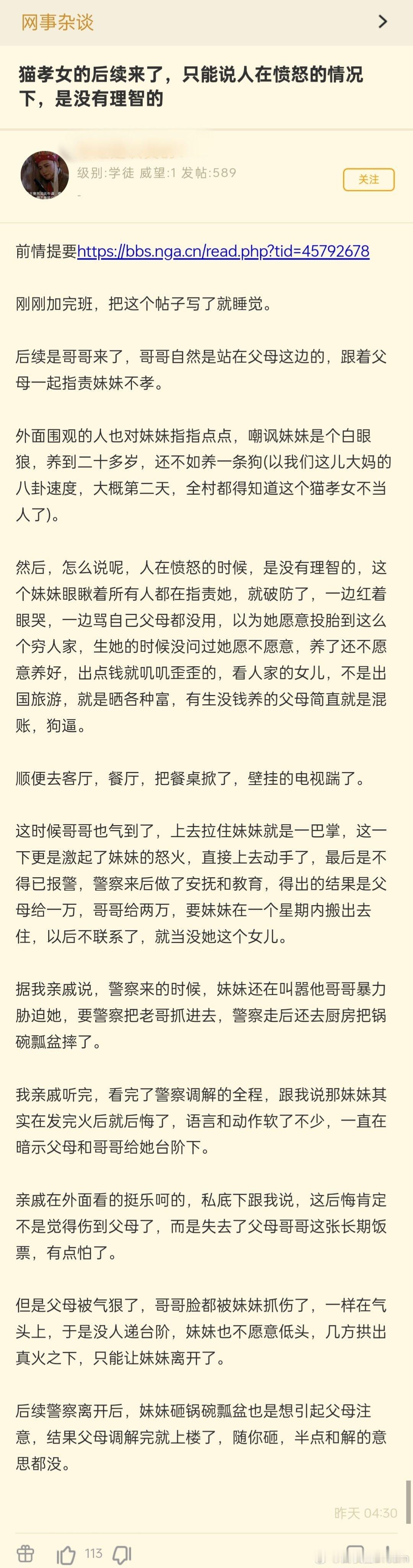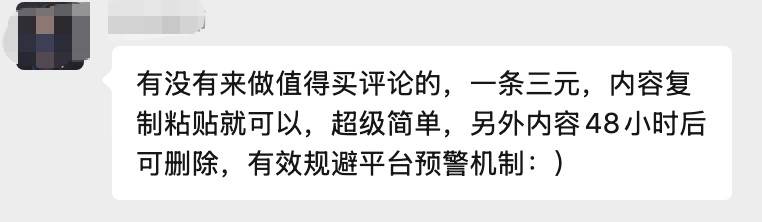单位同事递交辞职。小李把辞职报告放在总监桌上时,我正在打印机旁拆新墨盒。A4纸划过桌面的轻响里,她的马尾辫晃了晃,发尾沾着点咖啡渍——是上周帮我搬资料时洒的,当时她说"没事,洗得掉",结果洗了三次还是留着浅褐色的印子。 单位同事小李要走了。 我蹲在打印机旁拆新墨盒时,正听见她跟总监说“那我先走了”。 A4纸划过桌面的轻响飘过来,我抬头,看见她转身,马尾辫甩了甩,发尾沾着点浅褐色的印子——上周她帮我搬资料,文件堆得太高,路过茶水间时手一抖,半杯美式全洒在她发尾和我那件刚洗的白衬衫上。 当时她先用纸巾擦我的衬衫,说“这料子娇贵,得赶紧处理”,自己发梢滴着咖啡也没顾,我慌里慌张说“对不起对不起”,她笑出两颗小虎牙,“没事,洗得掉”。 结果现在看来,是没洗掉。 我手里的墨盒包装纸被指甲掐出几道印子,塑料膜窸窸窣窣响。她已经走到打印机旁了,看见我,脚步顿了顿,“哟,换墨盒呢?” “嗯,”我嗓子有点干,“刚没墨了。” “我那抽屉里还有半盒,你要是急用先拿去——”她话说一半停住,挠了挠头,“忘了,我都要走了,抽屉明天就清空了。” 空气里飘着新墨盒的油墨味,混着她身上淡淡的柑橘护手霜味,是上个月部门团建,她分给每个人一小支的那种。 你说,人是不是总这样,非要等东西要失去了,才把那些平时忽略的细节一个个捡起来,像捡散落在地上的玻璃珠子? 我想起她每天早上给我带的热豆浆,想起她帮我改PPT时圈出的错别字,想起上次我感冒,她默默把自己的暖手宝塞我桌底——这些事小得像办公桌上的便利贴,随手就能撕掉,可现在一张张叠起来,压得我鼻子发酸。 “辞职报告……总监批了?”我终于找到话说。 “批了,”她点点头,发尾的咖啡渍跟着晃,“下家在苏州,离爸妈近点。” “挺好的,”我说,心里却在想,以后谁帮我抢会议室的投影仪遥控器,谁在我加班时递过来半块巧克力,谁在茶水间碰见时跟我吐槽新来的实习生总把咖啡洒在水池里。 她突然笑了,伸手拨了拨我额前的碎发,“你这表情,好像我要去远方打仗似的。” “不是,”我赶紧摇头,“就是……突然觉得,上次你帮我搬资料,我还没好好谢你。” “谢啥呀,”她转身要走,又回头,“对了,那咖啡渍我其实没使劲洗。” 我愣住。 “那天回家想,留着呗,”她指了指发尾,“万一以后忘了今天帮你搬资料的傻样,看见这印子就能想起来——你当时脸都白了,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 原来不是洗不掉,是她根本没打算洗掉。 就像她每次帮别人做事,总说“没事,小意思”,其实那些“小意思”,她都悄悄收进了心里的小抽屉,等着某天对方想起时,能笑着说“哦,原来你还记得”。 午休时我去她工位,她正在收拾东西。桌上摆着我们去年拼单买的多肉,叶片胖乎乎的,叶尖上还有我上次浇水时滴的泥点——当时她还笑我“给多肉洗澡呢”。 “这个送你吧,”她把多肉推过来,“你比我会养。” 我接过花盆,陶土盆的边有点硌手,就像此刻心里的感觉,有点疼,又有点暖。 下午她走的时候,我在开周会,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门,看见她背着双肩包,马尾辫在走廊里一甩一甩,发尾的咖啡渍在阳光下亮了一下,像个没说出口的句号。 后来我每次换墨盒,都会想起那天的油墨味和柑橘香;每次看见那盆多肉,都会想起叶尖的泥点和她发尾的咖啡渍。 原来同事一场,所谓的缘分,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由这些豆浆、暖手宝、半块巧克力、没洗掉的咖啡渍和带泥点的多肉组成的。 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东西,拼在一起,就是我们在格子间里,偷偷藏起来的、闪闪发光的温柔啊。 下次再有人帮你递张纸,记得说声“谢谢”;再有人给你带早餐,记得说句“好吃”;再有人陪你加班到深夜,记得说句“有你在真好”。 别等发尾的咖啡渍干了,才想起它本来该是甜的。 现在那盆多肉长得很好,我每天给它浇水,都会对着叶尖的泥点笑一笑。 就像对着那个没说出口的“再见”,和藏在咖啡渍里的,一整个夏天的温柔。
猫孝女的后续来了。只能说,不如叉烧。
【1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