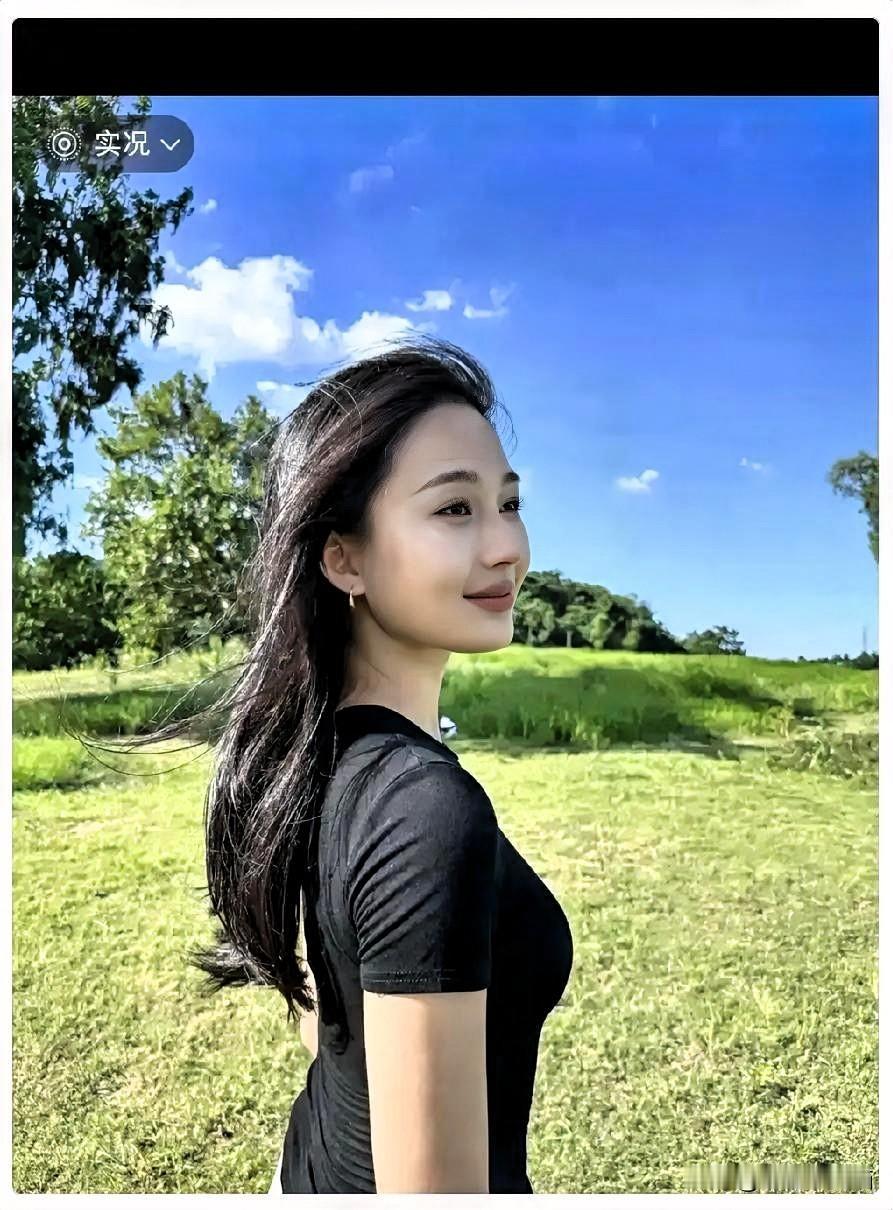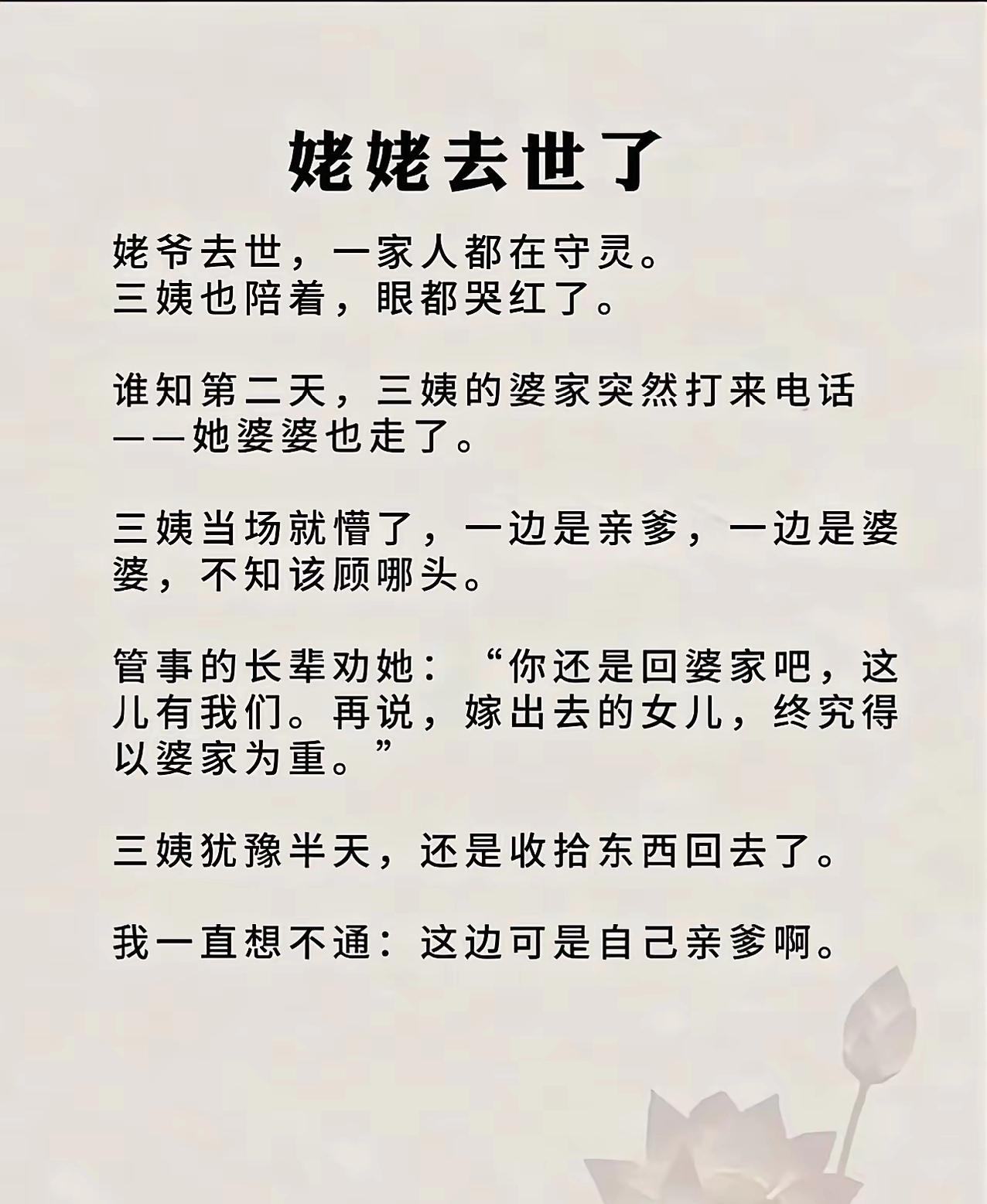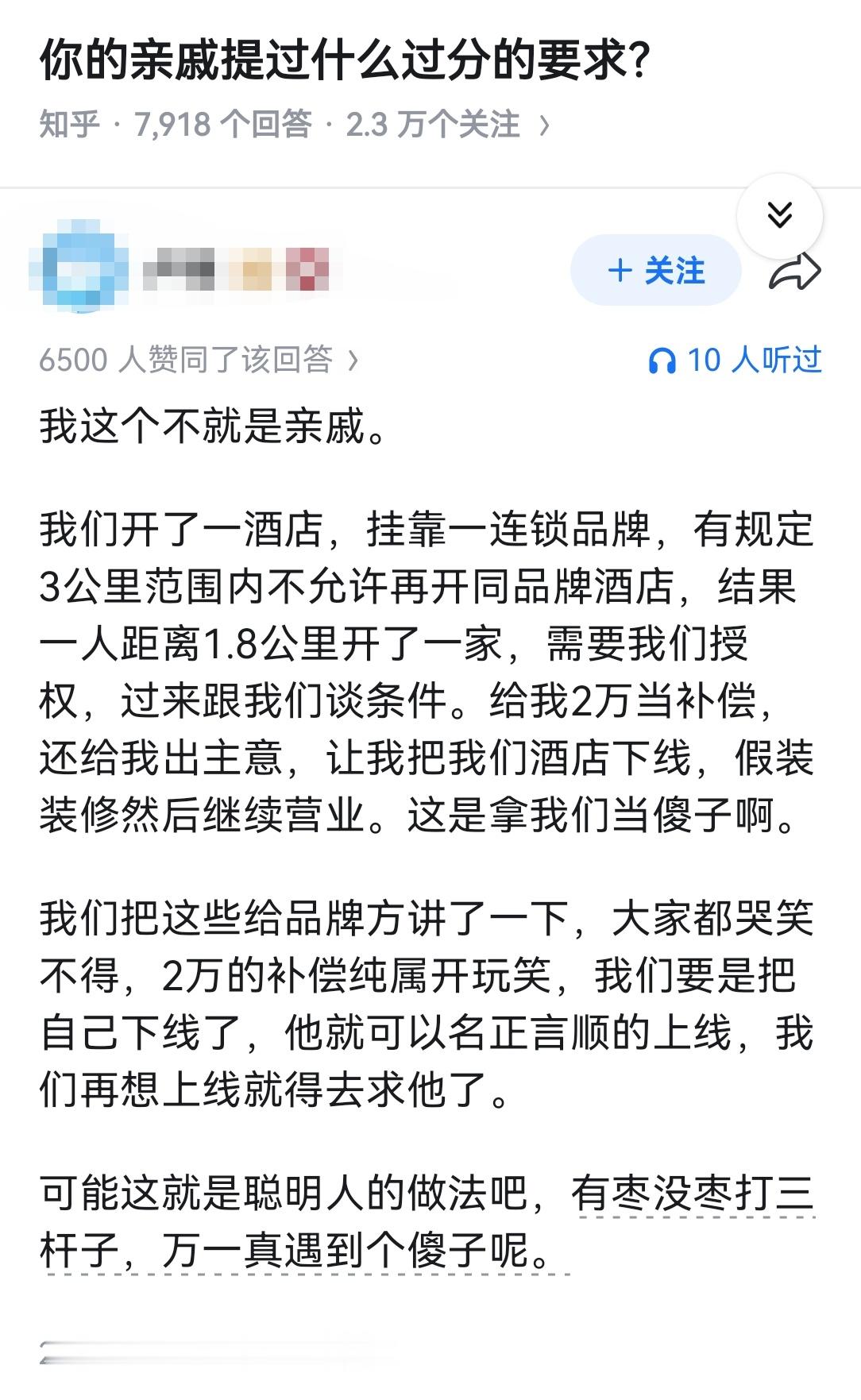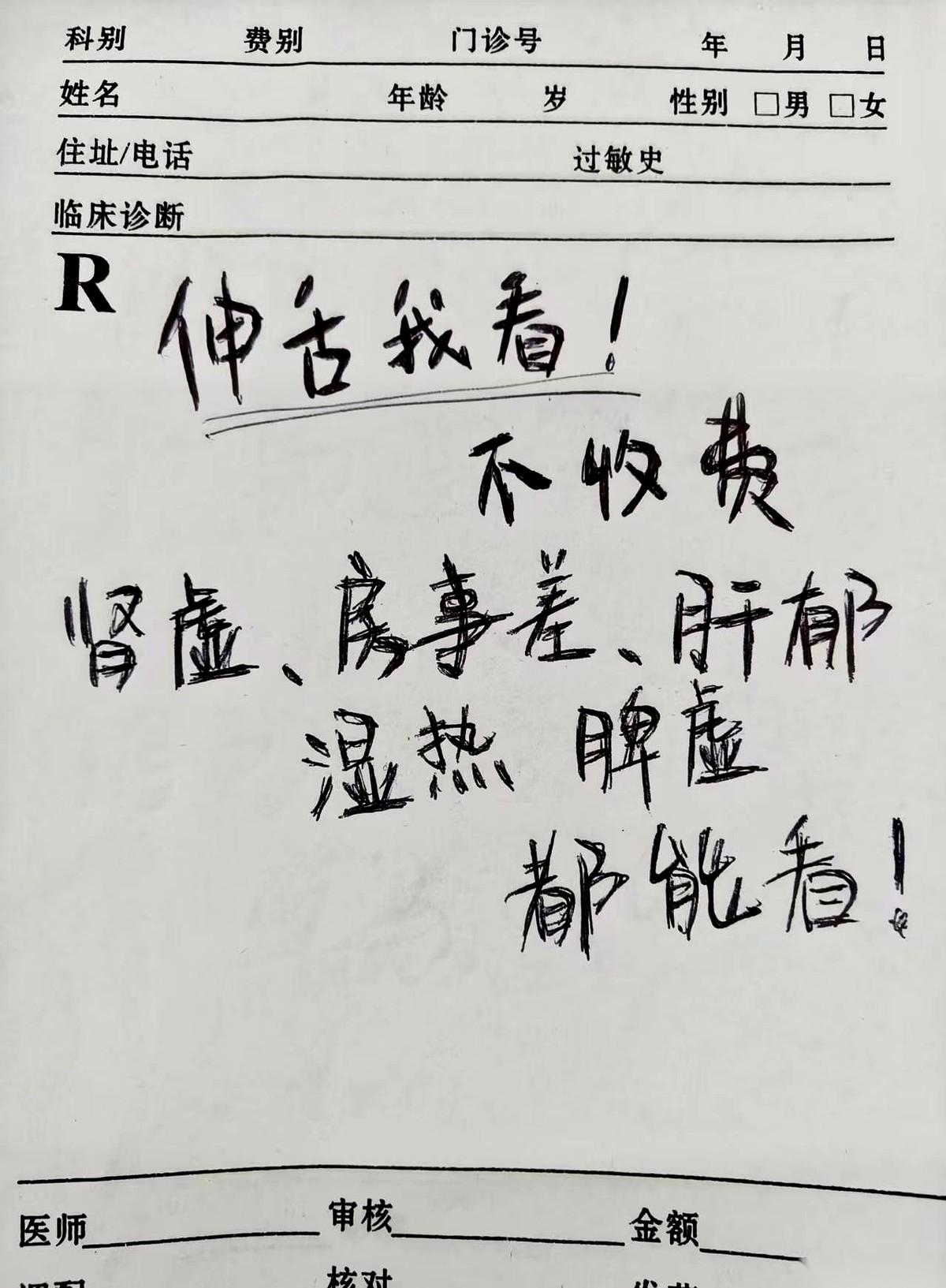我老公是一个乡镇初中教师,自从我嫁给他那天起,就发现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只要到了领工资那周的周末,他一定要去一趟他的姐姐家。起初我没太在意,想着兄弟姐妹间走动也是常事,可日子久了,我发现这事透着蹊跷。 我和老周结婚三年,他在镇中学教数学,工资卡放在抽屉第二层,和我的并排,红色塑料皮磨出了毛边。 每个月15号发工资,他总要在周六早上七点半,揣着刚取的现金出门,说去看姐姐。 起初我蹲在厨房刷碗,听他关门时钥匙串叮当作响,只当是兄妹情深——乡镇上的亲戚,周末走动本就寻常。 可这习惯雷打不动,连去年我急性阑尾炎住院,他周六早上照样去了,回来时提着姐姐炖的鸡汤,保温桶外面还沾着他骑车时溅的泥点。 我心里那点疑惑,像春天的草芽,悄悄拱了土。 有次他蹲在玄关换鞋,我靠在门框上问,“姐家不缺这点钱吧?她女婿在县城开超市,比咱们宽裕。” 他系鞋带的手顿了顿,鞋尖蹭了蹭地板上的灰,“她爱吃镇上老李的红富士,顺路买的。” 话是这么说,可上个月老李的苹果摊改成了卖橘子,他照样取了一千五出门。 我偷偷翻过他的工资条,每月三千二,房贷一千八,剩下的刚够糊口,他取的现金,几乎是我们半个月的菜钱。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躲在窗帘后面看他。七点二十,他从抽屉取了钱,又从衣柜最下面翻出个旧铁盒,打开时咔嗒一声轻响——我从没见过那个盒子。 他从里面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看了足足半分钟,才小心放回去,揣着钱出门。 我鬼使神差地拉开衣柜,铁盒上了锁,锁是老式铜制的,钥匙孔锈迹斑斑。 晚上他回来,我正在叠衣服,铁盒被我放回了原处,只是锁扣没对齐。他一眼就看见了,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手指摩挲着盒盖,“其实该早点告诉你的。” 原来他上高中那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家里借遍了亲戚,姐姐刚结婚,把婆家给的彩礼钱全拿了出来,还辞了在县城的工作,回来种大棚供他读书。 “她说,等我工作了,每个月给她买斤苹果就行。”他声音低下去,“后来我考上师范,她又说,苹果不用买了,人来就行——可我知道,她那时为了给我凑学费,把陪嫁的金镯子都当了。” 我想起姐姐每次见我们,总往我手里塞鸡蛋,说自家鸡下的;想起她袖口磨破的毛衣,洗得发白却干净;想起老周每次从姐姐家回来,包里总会多几双她纳的布鞋,针脚密密麻麻。 原来那些被我当作“寻常走动”的周末,藏着他二十年没说出口的亏欠。 那一千五,不是接济,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姐姐还一份永远还不清的情。 我突然想起上个月,他取了钱却没买苹果,回来时提了个新书包——姐姐的小孙子要上小学了。 我们结婚时,他说“以后我的工资都给你管”,可这个秘密,他守了三年。 是我太迟钝了吗?还是婚姻里的我们,总容易把对方的习惯当作理所当然,忘了每个“寻常”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段没说出口的往事? 第二天早上,我比他起得早,煮了粥,煎了两个荷包蛋。他揣钱出门时,我把自己的工资卡塞给他,“多取点,给姐买套护肤品——她眼角的细纹,比去年深了。” 他愣住了,钥匙串掉在地上,叮铃哐啷响了好一阵。 现在每个月领工资的周末,我们会一起去姐姐家。老周骑着摩托车,我坐在后面,风里带着麦田的清香,他哼着跑调的歌,手偶尔会往后伸,紧紧攥住我的。 抽屉里的工资卡依旧并排躺着,红色塑料皮的毛边更明显了,可我每次拉开抽屉,心里都暖暖的——原来最好的婚姻,不是没有秘密,而是愿意把藏在铁盒里的往事,慢慢讲给你听。
我和老公分房1年多了。晚上爸妈来看孩子,我俩只能又重新睡在一屋。我先上的床,
【6评论】【10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