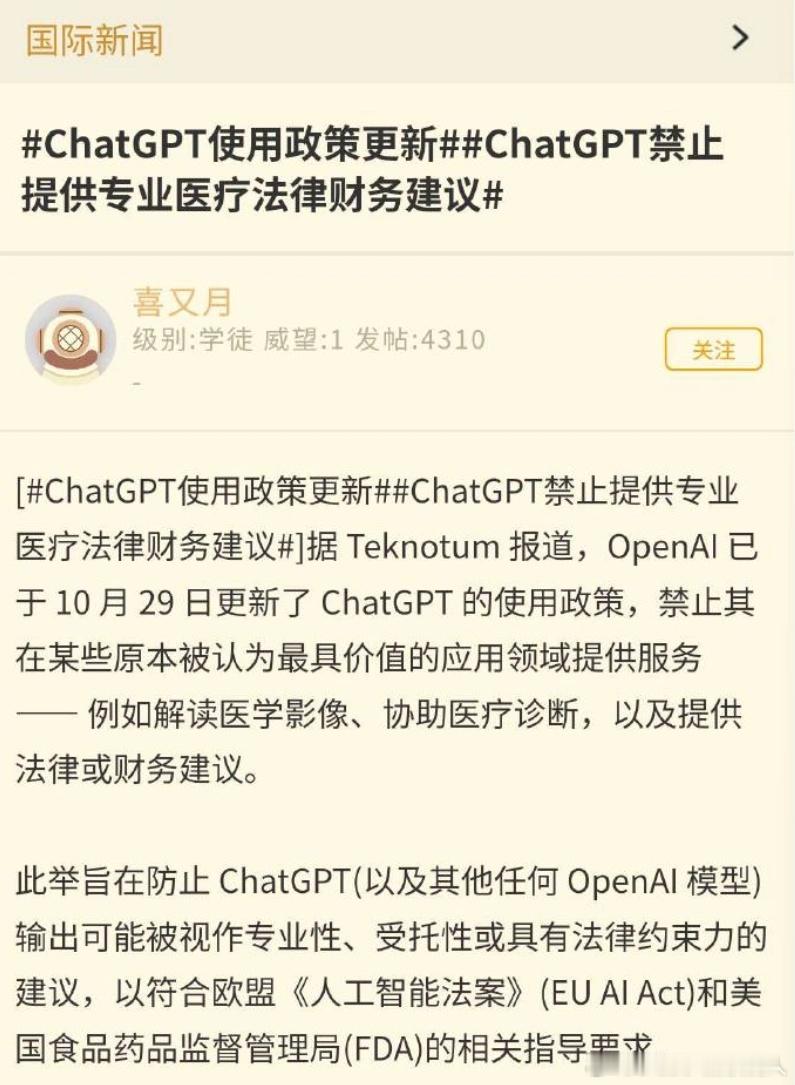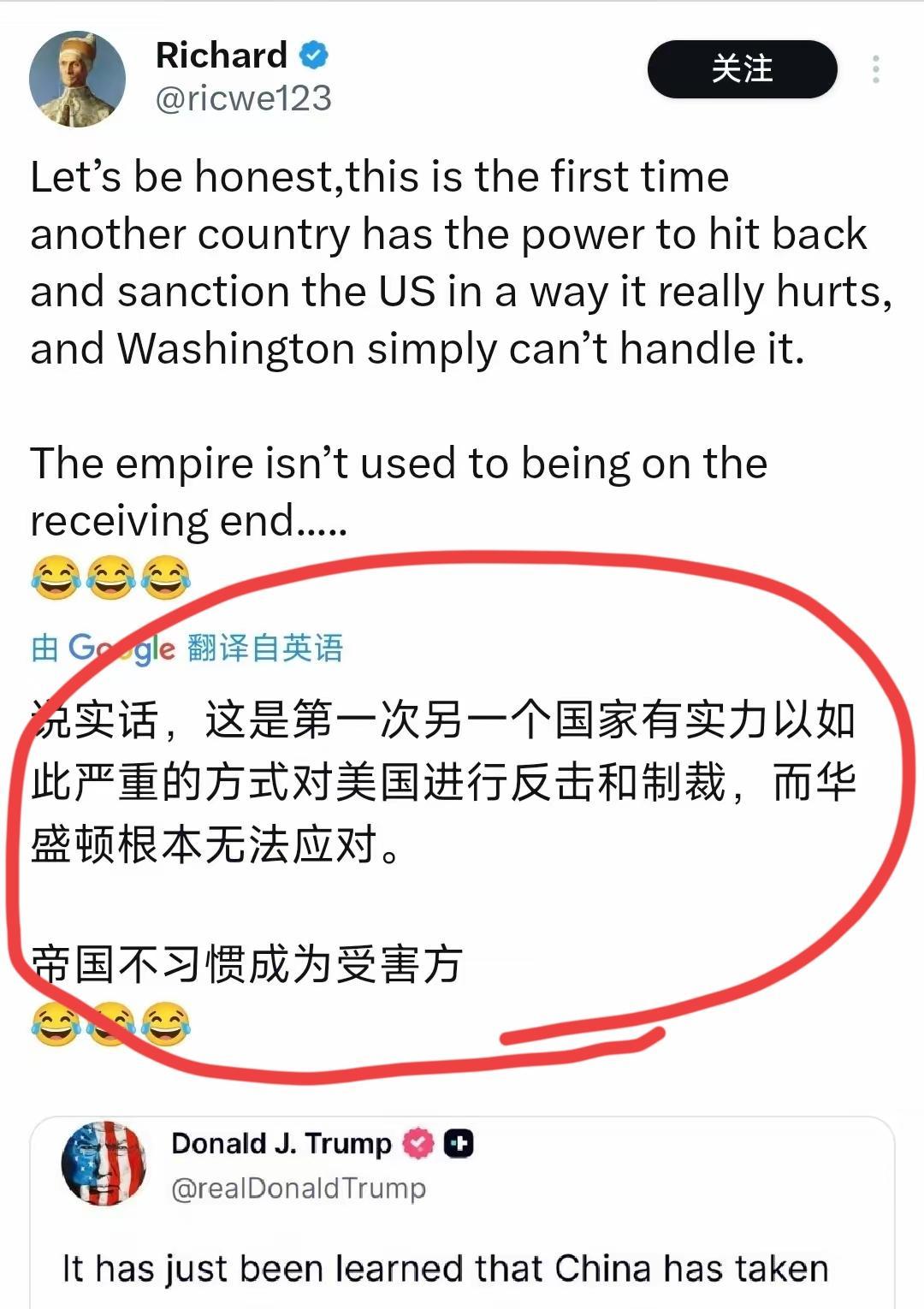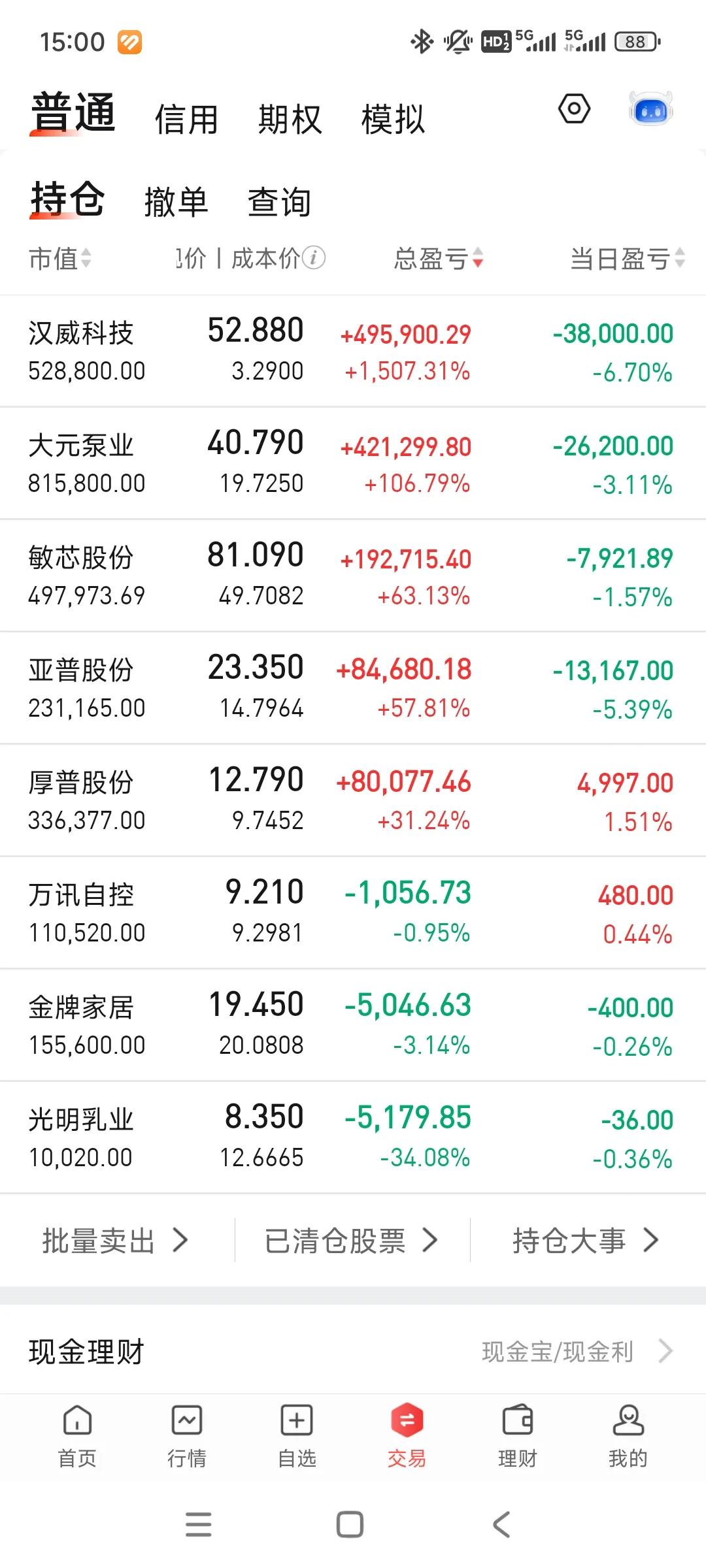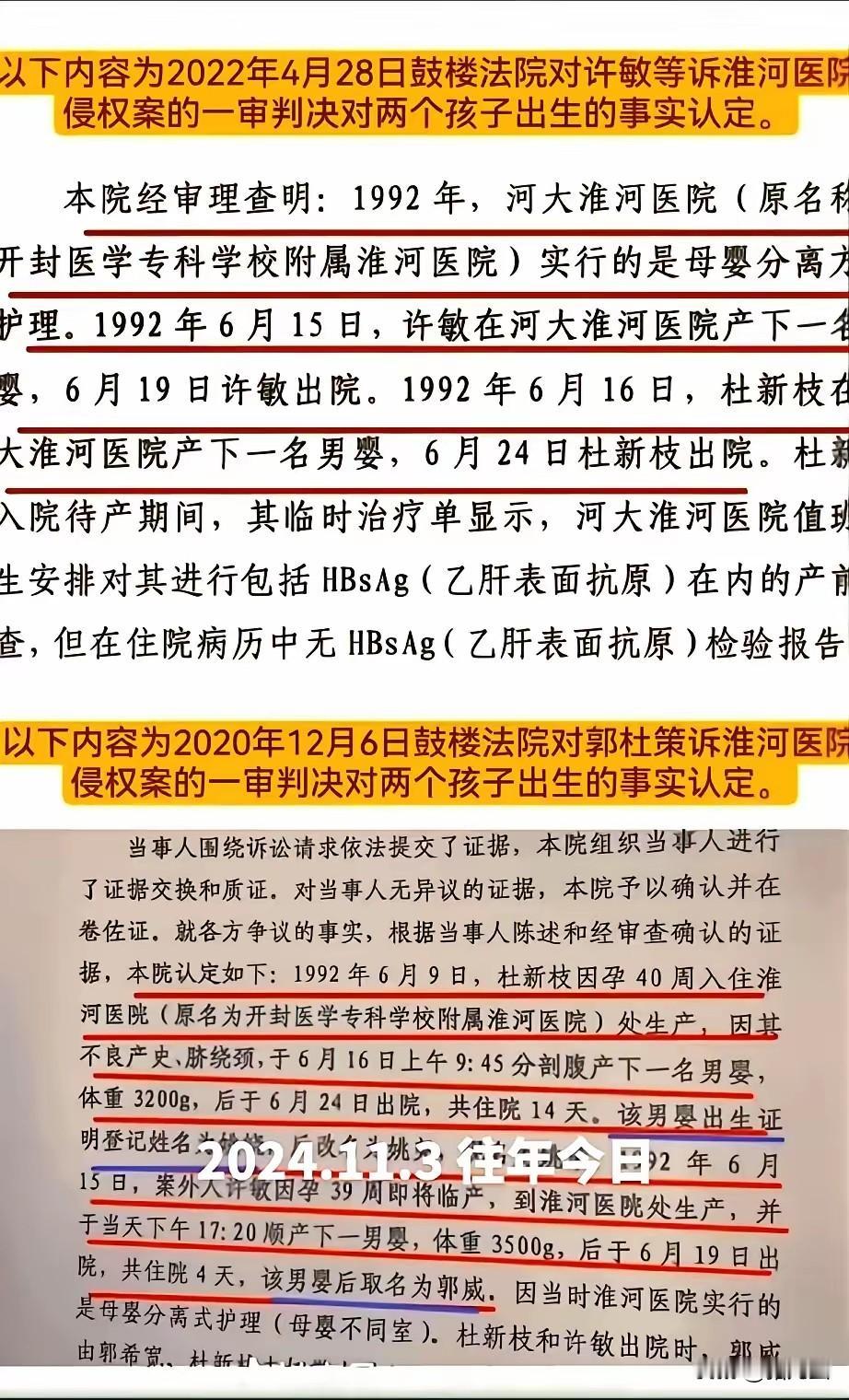吴石临刑前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陈诚的,第二个直接被拒接。 天还黑着,台北闷得很,六月的潮气贴在墙上不掉,吴石摸到电话,拨一串熟到不能再熟的号码,屋里就他一口气在走,命数这事心里早有数,不是案卷多厚,是风向把人往哪边推,明白得很,还是得打。 先找陈诚,老战友,命里有一段枪林弹雨扯着往外拖的情分,电话通了,听筒那头停了一下,吐出两个字,“放心”,话不多,线头有人听着,谁都知道,这一通不是求生,是告别,吴石又压低了声,“别让他们饿着冻着”,像是随口一提,落在那头却砸得很重,挂断后屋里只剩风声,陈诚心里跟着走了一段,转身去安排,话不说在明处,事得落在暗处。 过了七个月,王碧奎放人提早,铁门一开人出来,家里从此每月两百台币,按时,寄件人写“陈明德”,名字陌生,意思不陌生,十几年不落,账单一张一张夹进抽屉,陈诚这边有人不救得了,有人要照顾得住,能做多远做多远,承诺不放在嘴上,落在明细里更稳。 第二通,拨给周至柔,老同学,空军那边的一把手,电话一阵一阵响,桌上的灰跳了几下,手指在案上点了又点,人却没动,号码认得清,门前敲过的那伙人也认得清,毛人凤那套话摆在那儿,别插手,接与不接不是礼数,是站哪边的影子,铃声停了,屋里静得能听见呼吸,事情不可能到这儿就算。 后来每月有钱到了吴石长子手里,没留名,落款写“保定同窗”,字扁扁的,像怕人认,一笔一画很稳,这不叫赎什么,这是一种不愿说破的回应,过去那通没接的电话卡在嗓子里出不来,手里还能做点事,这就够了,沉着,不抬头,不声张。 人间有些话开不了口,有些门推不开,能开多宽就多宽,能做就先做,不往外讲,心里记着就行。 两通电话,一边接了,一边没接,落下的分量都不轻,史事像铁板,冷硬放在那儿不动,人心像水,沿着缝走,绕着石头过,还是能到达。 吴石上路时很稳,在马场町,背挺直,六枪落身,脚下没乱,留下一句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从头到尾,不是只顾自己这一口气,理想摆在前头,信念立在心上,一代人的清明要有人去扛。 王碧奎在里头缝麻袋,手磨出厚茧,拿豆腐换一点油盐,出来那天收到第一笔,单子上那个“陈明德”,她看了半晌,把纸折好放进箱子,说,“这是你父亲生前的朋友”,一屋子人都明白什么意思,眼圈不红,日子还得过。 陈诚后来病重,把“陈明德”这三个字交代清清楚楚,寄,接着寄,最小的一个长到成年再停,话说完,事情有人接手,线不断,心里才稳。 周至柔活得久一点,年岁上来,有人问他这一辈子什么放不下,他停长久,吐出一句,“该接的电话没接”,话很短,重量在字缝里,过去那晚的铃声像在屋角回荡,人的影子跟着一伸一缩。 一个在明处拉起遗孀的日子,一个在暗处托着孩子往前,名字有光的在纸上,名字藏着的在账上,两条路走到一处,风紧的年月,心里留了余地,做了能做的那一截。 史事不只黑白两格,陈诚拉不回人,却把承诺放稳,周至柔没接那通,却没让家口断炊,标签贴不上,事在那儿摆着,能看见的,都在细处。 而吴石,这个被列在清单上的名字,临终前拨的两通,声音穿过那么多年,还能在人心里响起来,每一次铃起,是对着良知的一问,每一次沉默,是另一个回声。 史书未必记下每一声铃响,我们把它记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