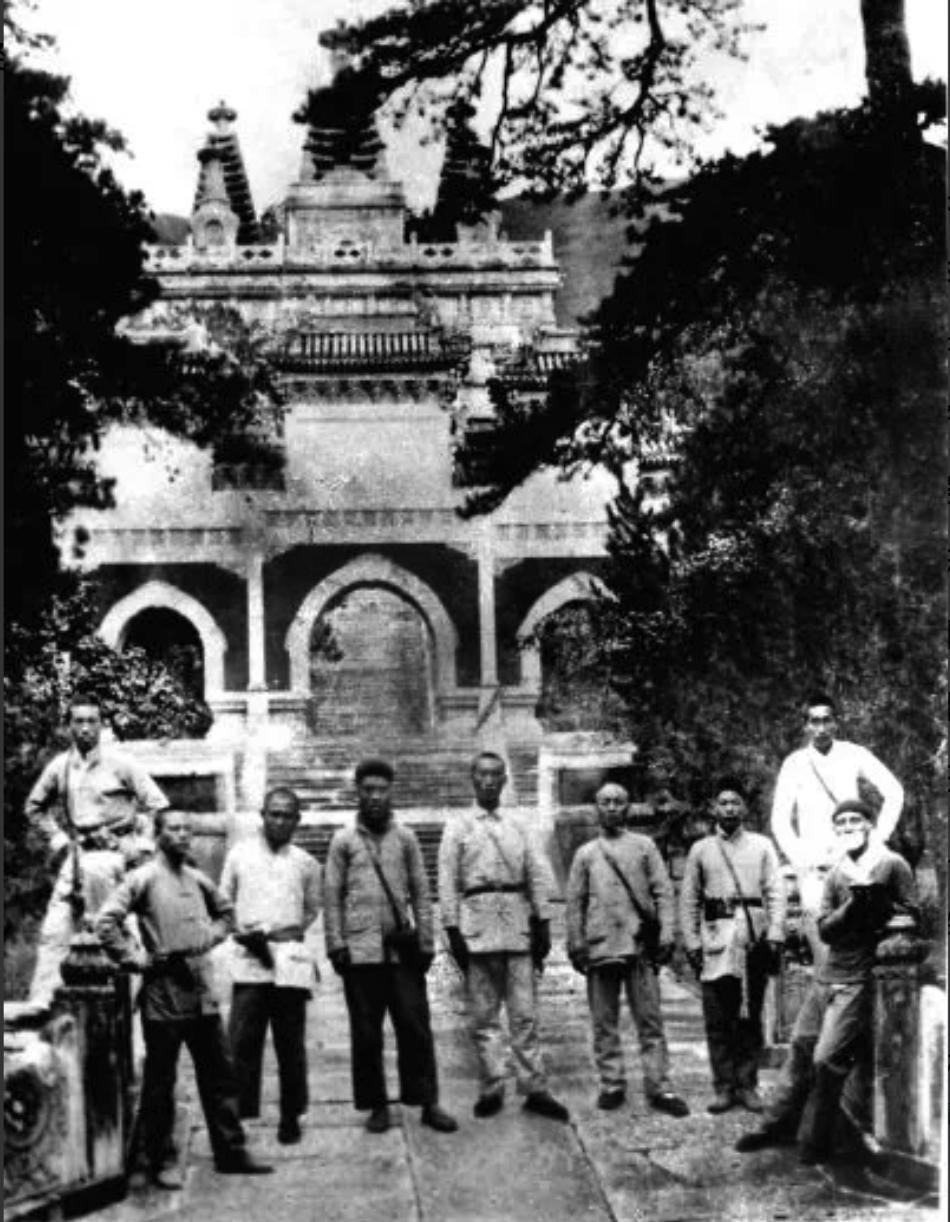1978年,女知青李亚茹返城前夜,她颤抖着解开衣扣,对丈夫表示:今晚,我们做最后一次夫妻!次日她便抛下3岁女儿,头也不回的离开,42年后,女儿的一句话让她泪流满面...... 2020年北京的冬夜,72岁的李亚茹坐在沙发上,指尖摩挲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针脚密密麻麻,鞋底还留着轻微的磨损痕迹。 这是45年前,王建国熬了三个通宵给她做的。此刻,鞋的主人王小丫正蹲在茶几旁,给她泡东北带来的大麦茶,雾气氤氲中,母女俩的眉眼渐渐重叠。 这场迟到42年的重逢,要从那个装着布鞋的蓝色布包说起。 1985年,北京纺织厂的宿舍里,37岁的李亚茹刚下夜班,就看到枕头边放着一封来自东北的信。 信封上的字迹陌生又熟悉,是公社邻居张婶写的:“建国这两年身体不好,小丫总在村口望,问妈妈是不是忘了她。” 李亚茹捏着信纸,想起1978年那个清晨,她背着行李离开东北土坯房时,王建国把这双布鞋塞进她的行李,说“城里路硬,穿这个软和”; 而3岁的小丫还在炕上熟睡,小脸红扑扑的,手里攥着她织了一半的小袜子。 时间往回拨到1969年的春天,李亚茹在公社的菜窖里找土豆,不小心摔了一跤,崴了脚。王建国听说后,背着药箱跑了三里地,蹲在地上给她揉脚踝,动作轻得像怕碰碎瓷娃娃。 “以后找东西喊我,你城里来的,没干过这些粗活。”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个烤土豆,还带着温度。那天之后,王建国成了她的“专属帮工”:她不会编草绳,他就手把手教。 1975年结婚时,李亚茹用布票换了块碎花布,给王建国做了件衬衫。王建国舍不得穿,只有过年才拿出来,平时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木箱里。 女儿小丫出生后,李亚茹常抱着孩子坐在炕头,看王建国在院子里劈柴,阳光洒在他黝黑的脸上,她突然觉得“这辈子这样过,也挺好”。 可1978年返城的消息传来,同队知青收拾行李时的笑声,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的文字,像两根绳子,拽着她往北京的方向走。 返城前夜,王建国把攒下的20块钱和小丫的百天照塞进她的行李,又把这双布鞋拿出来,反复叮嘱:“冷了就穿,别冻着脚。” 李亚茹看着他红着眼眶却强装镇定的样子,突然哭了,抱着他说:“建国,今晚我们做最后一次夫妻。”天没亮,她趁着小丫还没醒,悄悄走了。 回到北京后,李亚茹一边在纺织厂打工,一边照顾病重的父亲,日子过得紧巴巴。她想接小丫来,可宿舍六平米挤三个人,连孩子的落脚地都没有。 她给王建国写过两封信,收到的回信只有“小丫好,勿念”四个字。后来张婶又来信说,王建国农忙时把小丫托付给她,自己顶着40度的高温下地,累得吐了血,也舍不得歇一天。 李亚茹拿着信,愧疚得不敢再写,她怕自己忍不住回去,更怕回去后,再也圆不了大学梦。 1990年,李亚茹考上了夜大,毕业后在街道办找了份工作,后来又再婚,生了一儿一女。可她始终把这双布鞋藏在衣柜最深处,偶尔拿出来擦一擦,鞋底的磨损痕迹,像刻在她心上的疤。 有次小儿子问她“这鞋是谁做的”,她只说“一个老朋友”就红了眼眶。 2020年,社区组织知青联谊会,李亚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刚进门,就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棉袄的女人,手里拿着个蓝色布包,正在打听她的名字。 “您是李亚茹阿姨吗?我是王小丫。”女人说着,打开布包,里面除了她当年给小丫织了一半的小袜子,还有一沓泛黄的信; 都是王建国写了没寄出去的,上面写着“小丫今天学会走路了”“我给你腌了酸菜,等你回来吃”“今天看到个像你的人,追了两条街,不是你”。 小丫说,王建国去世前,把这个布包交给她,说“这是你妈留下的,以后找到她,给她看看”。 这些年,她拿着妈妈的照片,跑遍了东北的公社、县里的知青办,后来又跟着知青联谊会的线索找到北京。“我不怪你,妈,”小丫握着她的手,“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和我爸,从来没怪过你。” 如今,李亚茹的家里多了很多东北元素:墙上挂着小丫带来的玉米挂饰,厨房里放着腌酸菜的坛子,衣柜里除了她的衣服,还有小丫给她织的毛衣。 每天早上,小丫会陪她去公园打太极,给她讲王建国当年怎么给她编小辫子;晚上,两人坐在沙发上,李亚茹会给小丫讲她在北京的日子,讲她当年的大学梦。 有次,小丫拿出王建国没寄出去的信,念到“今天小丫问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我没敢说,只说妈妈在城里忙”时,母女俩抱着哭了很久。 现在,李亚茹常常把那双布鞋拿出来,给小丫讲当年王建国做鞋时的故事。小丫听着,就会笑着说:“我爸这辈子,最疼的就是你。”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布鞋上,也落在母女俩的笑脸上——42年的遗憾,终于在这样的日常里,慢慢变成了温暖的回忆。 信源: 黑龙江省档案馆知青返城政策专项记录 《哈尔滨日报》2020年“知青往事”专题报道 哈尔滨市教育局优秀教师表彰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