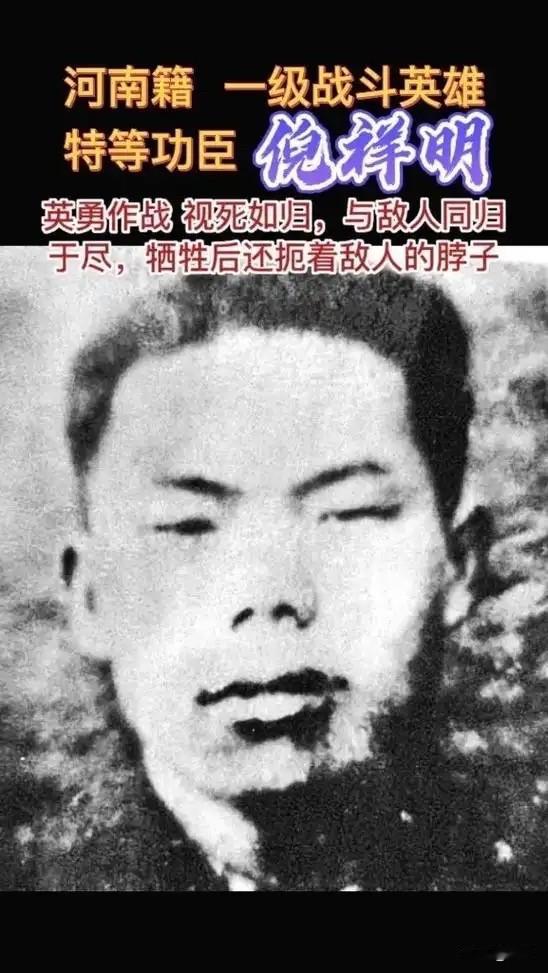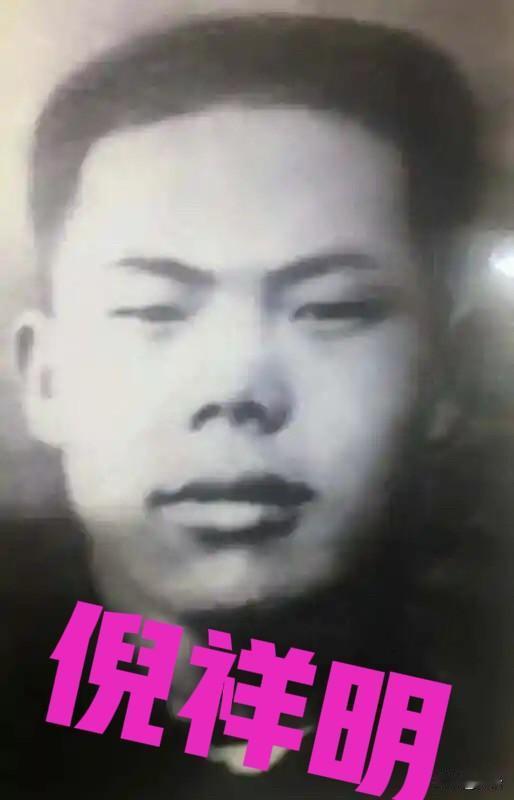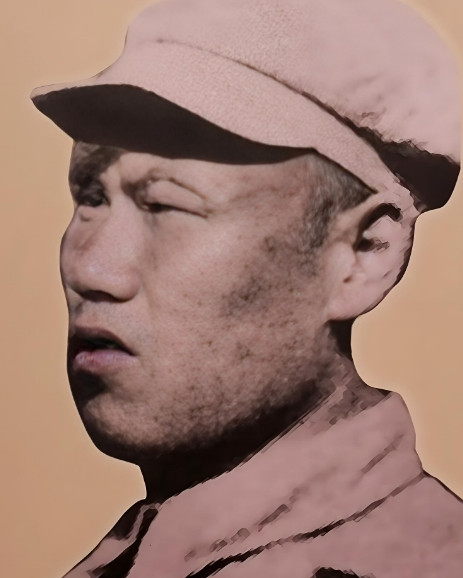1952年深夜,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都在熟睡,唯有一名战士因入党太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此时,大批美军趁着夜色,无声无息摸上了志愿军阵地。 这个睡不着的战士,就是倪祥明。兴奋与责任感像一团火在他胸中燃烧,他索性主动接替了战友的哨位,守在了坑道的最前沿。他想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倪祥明生在河南杞县的一个穷村子,打记事起,家里就没见过白馒头。爹娘带着他给地主扛活,春天摘棉花,秋天割麦子,他的小手比同龄孩子粗糙得多,指甲缝里总嵌着黑泥。 12岁那年冬天,弟弟得了风寒,家里没钱抓药,眼睁睁看着孩子没了。娘抱着弟弟冰冷的身子哭了三天,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杆敲得地面邦邦响,一句话没说。 1948年秋,村里来了穿军装的人,说要分田地。倪祥明跟着大人去村头晒谷场,看着工作队在墙上用石灰画杠杠,把地主的地分到各家各户。他家分了四亩水浇地,爹攥着写着自己名字的地契,手都在抖。 那天晚上,娘蒸了一锅玉米面窝头,还掺了把红糖,倪祥明一口气吃了三个,撑得睡不着,跑到地里摸着新翻的土,心里琢磨:这好日子,得有人护着才行。 1951年征兵,倪祥明第一个报了名。报名处的干部问他为啥参军,他脸憋得通红,说不出大道理,就重复一句:“我想让家里的地,一直长庄稼。”临走时,娘往他背包里塞了双布鞋,纳鞋底的线在鞋头打了七个补丁,那是她熬夜做的。爹把他拉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半块舍不得吃的冰糖。“到了部队,听指挥,别怂。”爹的声音有点哑。 到了朝鲜,他才知道战争有多狠。第一次上阵地,美军的炮弹像雨点似的砸下来,震得他耳朵嗡嗡响,蹲在防空洞里直想吐。可看到老兵们冒着炮火往前沿送弹药,他咬着牙跟上去。 有次运输队遇袭,班长为了掩护他,被弹片削掉了半只耳朵。班长捂着伤口笑:“小倪,你得活着,活着才能看到胜利。”那天起,他练刺杀练到胳膊抬不起来,投手榴弹投到虎口开裂,晚上在坑道里借着月光学认字,就想把入党申请书好好写出来。 第一次写申请书,他把“党员”写成了“党元”,被战友笑了好几天。他没脸红,拿着申请书去找指导员,说:“字写错了,但心是真的。”第二次写,他用了整整三个晚上,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结尾处写道:“我愿为老百姓能安稳种地,死在战场上。” 此刻蹲在坑道前沿,倪祥明摸了摸胸口,那里揣着刚发的党员证。白天支部大会上,当支书宣布他成为预备党员时,他站起来敬礼,手都没举稳。现在冷风刮过坑道口,带着硝烟味,他把步枪攥得更紧了。 草丛里的响动越来越近,能听到美军钢盔碰撞的声音。倪祥明深吸一口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们过去,绝不能。这个刚入党的年轻人,没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理论,可他清楚,自己身后是战友,是祖国,是家里那片正在长庄稼的地。 他会怎么应对这场突袭?这份深夜里的激动,能撑住这场生死考验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