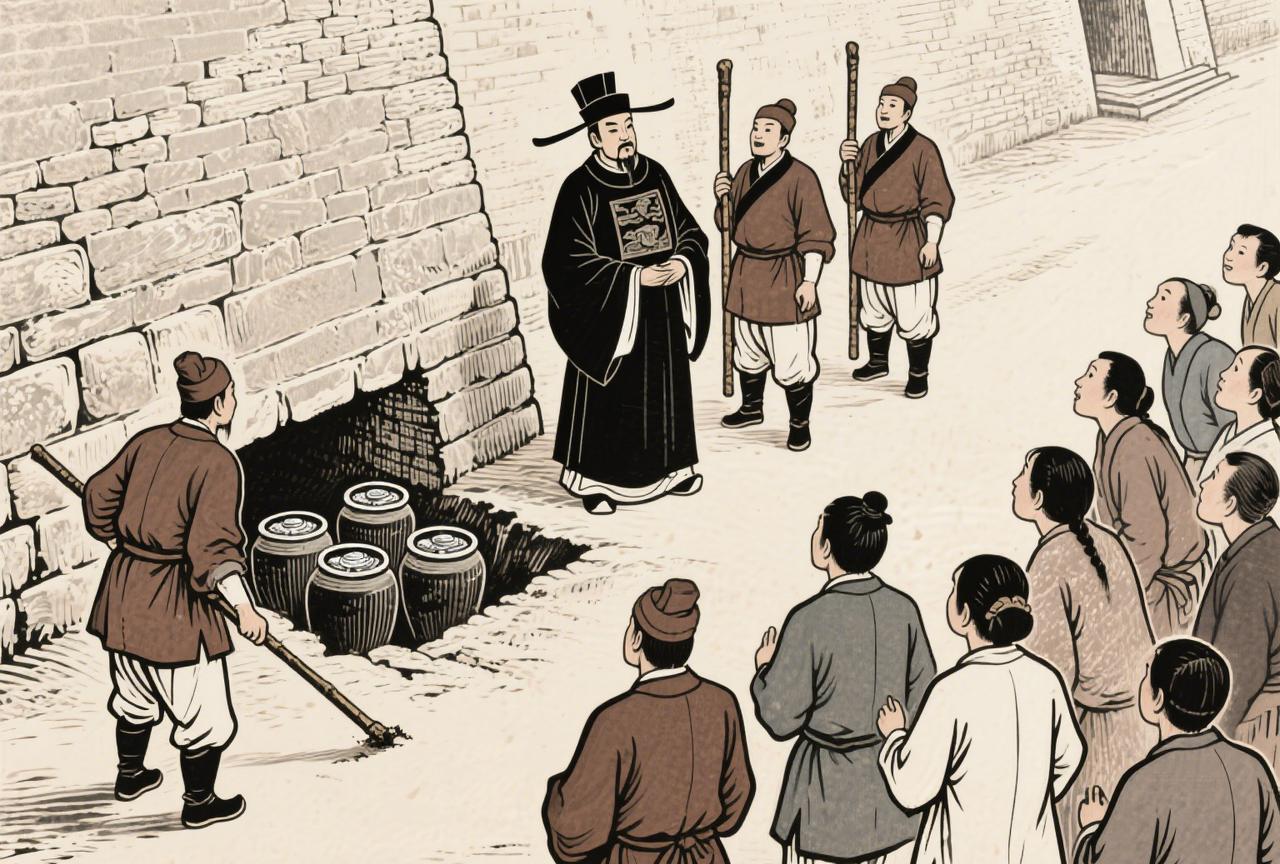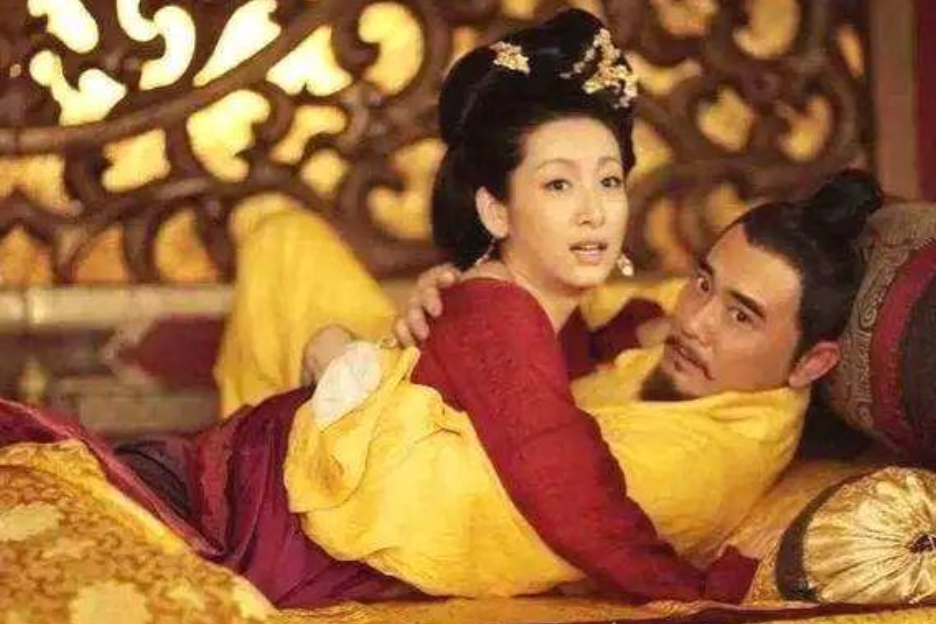公元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说:我已经70岁了,落叶归根,想回辽东老家海城养老,并带属下4300余家,共男女2万余口返回,希望皇上把以前赐给我的房屋、土地仍然给我,以便安插属下这些人员。 尚可喜出生在明万历三十二年,原籍山西洪洞,后移居辽东海州卫,那地方如今是辽宁海城一带。他家世代农耕,祖上迁徙到边疆,生活不算富裕。从小他就接触军旅,天启二年后金入侵辽沈时,他十八岁随父投军。父亲尚学礼是明东江游击,在楼子山战死沙场。尚可喜接棒,继续在明军东江部队干,驻守广鹿岛,从士兵一步步爬到副将。 这封奏折递到北京时,康熙刚满十九岁。 御案上的朱笔悬了半天,少年天子盯着“70岁”“回辽东”这几个字,指节轻轻敲着桌面。 朝堂上的老臣都知道,尚可喜这不是真的念旧。 他在广东待了二十多年,平南王府比广州城的藩署还要气派,属下的兵丁带着家眷,早把岭南的水土当成了自家的。 要带两万人回辽东?那片苦寒地,哪容得下这么多张嘴吃饭。 说白了,这是试探。 尚可喜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是降将。 当年在广鹿岛,他被同僚陷害,带着部众投奔后金,皇太极亲自出城十里接他,赐了“智顺王”的封号。 后来跟着清军入关,打李自成,平南明,一路打到广州,才坐稳了平南王的位置。 可降将的帽子,一辈子都摘不掉。 尤其是这几年,朝廷里总有人念叨“藩王权重”,吴三桂在云南当土皇帝,耿精忠在福建说一不二,他尚可喜在广东,虽说还算安分,可手里握着兵权,终究是根扎在皇帝眼里的刺。 他怕了。 70岁的人,见够了刀光剑影。 当年跟他一起降清的几个将领,有的被鸟尽弓藏,有的被罗织罪名,他不想自己的子孙也落得那样的下场。 不如主动退一步,把兵权交出去,带着人回辽东,守着祖上的土地,至少能保全家老小。 可他算错了一点——康熙要的不是退让,是彻底解决。 奏折批下来,朱批写得明明白白:准奏。但不必带那么多人,属下家眷愿意留广东的,朝廷给田给屋;愿意走的,朝廷派兵护送。至于平南王的爵位,让你儿子尚之信袭了,留在广东。 尚可喜接到批复,在家闷了三天。 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爵位留下,兵权却要分崩离析。 更要命的是,让尚之信留广东。 这儿子是个混不吝的,脾气暴躁,在军中说打就打,说杀就杀,连他这老子的话都敢顶。 把他留在广东,没了自己压着,迟早要出事。 果然,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坐不住了。 他跟尚可喜、耿精忠并称“三藩”,本就互相盯着,如今尚可喜要退,朝廷又表现得这么强硬,他要是不表态,下一步就该轮到自己了。 没过多久,吴三桂也递了奏折,说自己年纪大了,请辞云贵总管。 康熙几乎没犹豫,大手一挥:准了。 这下耿精忠也慌了,赶紧跟着上书请辞。 三个藩王,原本只想试探,没想到少年天子接了招,还接得这么干脆。 尚可喜这时候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 尚之信在广东听说老爹要带人大头兵回辽东,自己却要留下当这个空壳王爷,当场就炸了。 他带人闯进王府,把尚可喜的奏折撕了,指着鼻子骂:“你走了,我在这儿就是砧板上的肉!” 尚可喜气得浑身发抖,却拦不住这个儿子。 没过几个月,吴三桂在云南竖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耿精忠在福建响应,尚之信也逼着老爹扯了反旗。 尚可喜被儿子软禁在王府里,看着窗外的木棉花落了又开,一口老血吐在地上。 他这辈子,从明军到清军,从广鹿岛到广州城,算计了一辈子,想保全家族,最后却被自己的儿子拖进了叛乱的泥沼。 1676年,尚可喜在忧愤中病死。 临死前,他让身边的人取来当年皇太极赐的蟒袍,摸了又摸,眼泪混着血沫子往下掉。 “我死之后,把我葬回海城,别立碑,别写生平,就当我从没当过这个平南王。” 可历史哪能说抹就抹。 他那封想“落叶归根”的奏折,成了三藩之乱的导火索。 康熙花了八年时间,才平定这场战乱,彻底削除了藩王。 后来的人说,尚可喜是个悲剧人物。 想退,却退得不是时候;想保,却保不住身后事。 可细想想,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藩王和皇帝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信任。 你退一步,他进一步,直到把你逼到悬崖边。 尚可喜的悲剧,不是他不够聪明,是他身处的位置,本就没有两全的路。 信息来源:《清史稿·尚可喜传》《清圣祖实录》等史料对尚可喜请辞及三藩之乱相关背景有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