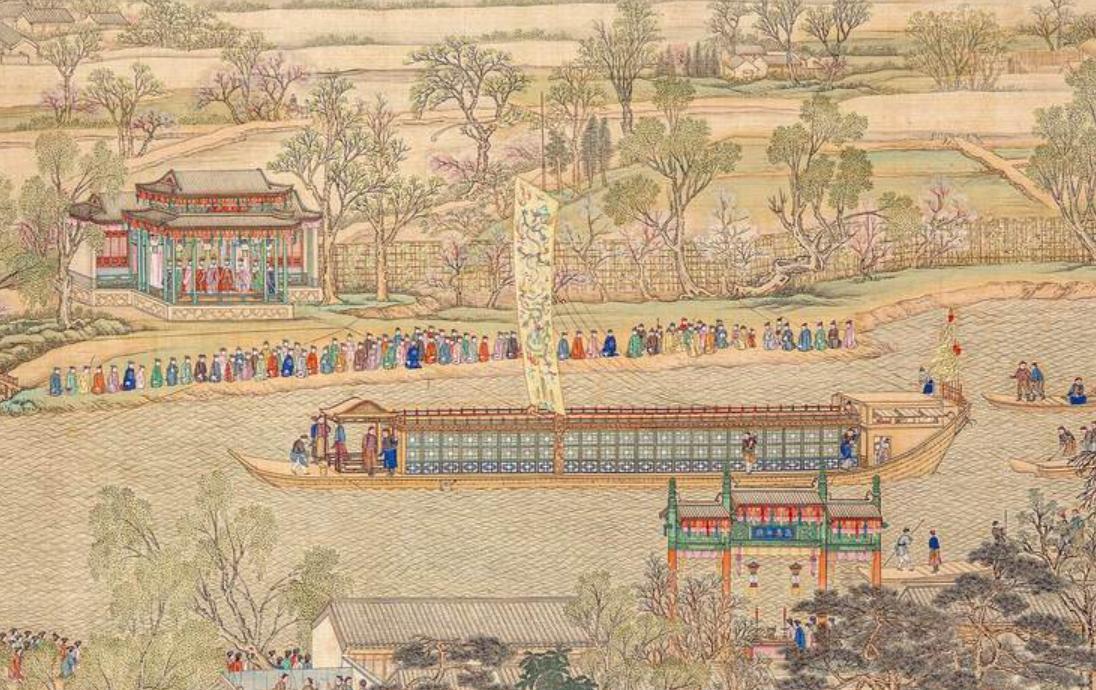据说,隋炀帝精通相术,曾夜观天象,知隋将亡,就对着镜子说:“好头颅,谁来斩他呢?”皇后闻之大吃一惊,炀帝却笑着说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提到隋炀帝,他在历史上绝对算是一位褒贬不一的皇帝。 609年,隋炀帝杨广40岁,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句话:“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从地域版图和人口来看,隋朝到了极盛之期。 但此后的他却开始了荒淫无度、生性残暴、穷兵黩武的另一面生活。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嫡次子,本无缘皇位。 然而,他却是个十分有心机,善于矫情饰行,以“仁孝俭朴”之假象蒙蔽双亲,构陷兄长太子杨勇“奢靡厌胜”,终得储位。 登基后,伪饰尽褪,野心也开始显露。 他迁都洛阳,以“控扼天下”之名,役使百万民夫,白骨铺就通衢。 开凿大运河,虽遗泽后世,却以“沟通南北”为由,征发丁壮无数,运河两岸,“尸骸相枕藉”。 三征高句丽,穷兵黩武,辽东之地,士卒填沟壑,民夫毙于途,天下户口为之减半! 他营造东都、修筑长城、广建离宫,每一项“大业”都以倾国之力推进,将文帝留下的丰厚家底与民力榨取殆尽。 他将整个帝国拖入了无底深渊。 民不聊生,大业七年,王薄于长白山首举义旗,拉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义军蜂起,贵族杨玄感亦趁机叛乱,帝国腹背受敌,根基动摇。 然而,深居宫禁的杨广,竟下诏宣称“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 直至大业十一年,雁门,被突厥始毕可汗十万铁骑团团围困,这位曾意气风发的帝王,竟吓得抱着幼子杨杲涕泗横流。 虽解围,但经此一吓,杨广的雄心壮志与最后一丝锐气,彻底泄尽。 他仓皇南逃,一头扎进江都这座用民脂民膏堆砌的温柔乡、避难所。 所以,当江都行宫深处,杨广对镜自问“好头颅,谁当斩之”时,陪伴在侧的萧皇后闻言,花容失色。 惊问,“陛下何出此不祥之言?” 杨广却缓缓放下铜镜,目光并未从镜中自己那截脆弱的脖颈上移开,嘴角反而扯出一丝近乎残忍的平静笑意。 他没有直接回答皇后的惊惶,而是抬眼望向窗外沉沉的夜幕,那里,或许有他命司天台官员日日观测、却越来越不敢细看的星象。 他想起不久前某个同样沉寂的夜晚,也是这般对萧后言道:“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 长城公,是南陈亡国之君陈叔宝降隋后的封爵。 沈后,即陈叔宝的皇后沈婺华。 杨广此言,无异于坦然承认自己已预见隋朝将亡,而他与萧后的结局,将如同二十多年前被他亲手灭国的陈叔宝夫妇一样,沦为阶下囚! 他甚至带着“豁达”,劝慰皇后及时行乐。 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积怨已深,天下汹汹,皆欲食其肉寝其皮。 他不再试图力挽狂澜,不再关心前线战报,甚至不愿听到任何关于叛乱的消息。 曾有宫女察觉护卫骁果军暗流涌动、意图北归叛变,冒险向萧后禀报。 萧后深知杨广心境,无奈叹道:“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 宫女忠心,面陈杨广,结果,杨广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宫女处死! 自此,行宫内外,所有不祥的消息,都被那挡在了迷楼之外。 迷楼之中,百间精舍,每间囚禁着一位千挑万选的美人。 他每日流连其间,宴饮无度。 萧皇后与宠妃伴其左右,强颜欢笑。 他不再临朝,甚至换上庶民般的幅巾、短衣,拄着一根短杖,在迷宫般的楼台馆榭间漫无目的地游荡。 或许,他潜意识里已明白,他项上人头,早已朝不保夕。 他深知,宫禁之内,杀机四伏。 占星术士的谶语、天象显示的“帝星晦暗”,如同诅咒在他脑中盘旋。 正是在某个这样的不眠之夜,他揽镜自照,发出了那声流传千古的慨叹。 当萧后惊问,他最终以一种近乎虚无的“通透”回应。 “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在他看来,王朝兴替,个人贵贱,不过是天道循环。 命运的绞索,终究由他最意想不到的人亲手收紧。 随驾江都的骁果军,多是关中人。 他们久戍江南,思乡情切,归心似箭。 然而杨广已决意偏安江都,无意北归。 骁果军的不满日益滋长,在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等人的煽动下,骁果军终于哗变! 此刻,镜中那颗曾令他自怜的“好头颅”,瞬间变得无比真实而脆弱。 杨广惊惶失措,却被叛军从锦幔之后拖出。 他看到了领头者熟悉的面孔,宇文化及,权臣宇文述之子,他一手提拔的臣子! 杨广自知不免,索要鸩酒,欲自尽以全帝王最后的体面。 然而,遍寻殿中,鸩酒竟不得! 原来,他平日防范严密,毒药早已被左右藏匿或销毁。 最终,叛军将领令狐行达解下自己的练巾,亲手勒死了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帝王。 隋炀帝杨广,最终以一种极其狼狈、屈辱的方式,结束了他充满争议、也充满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