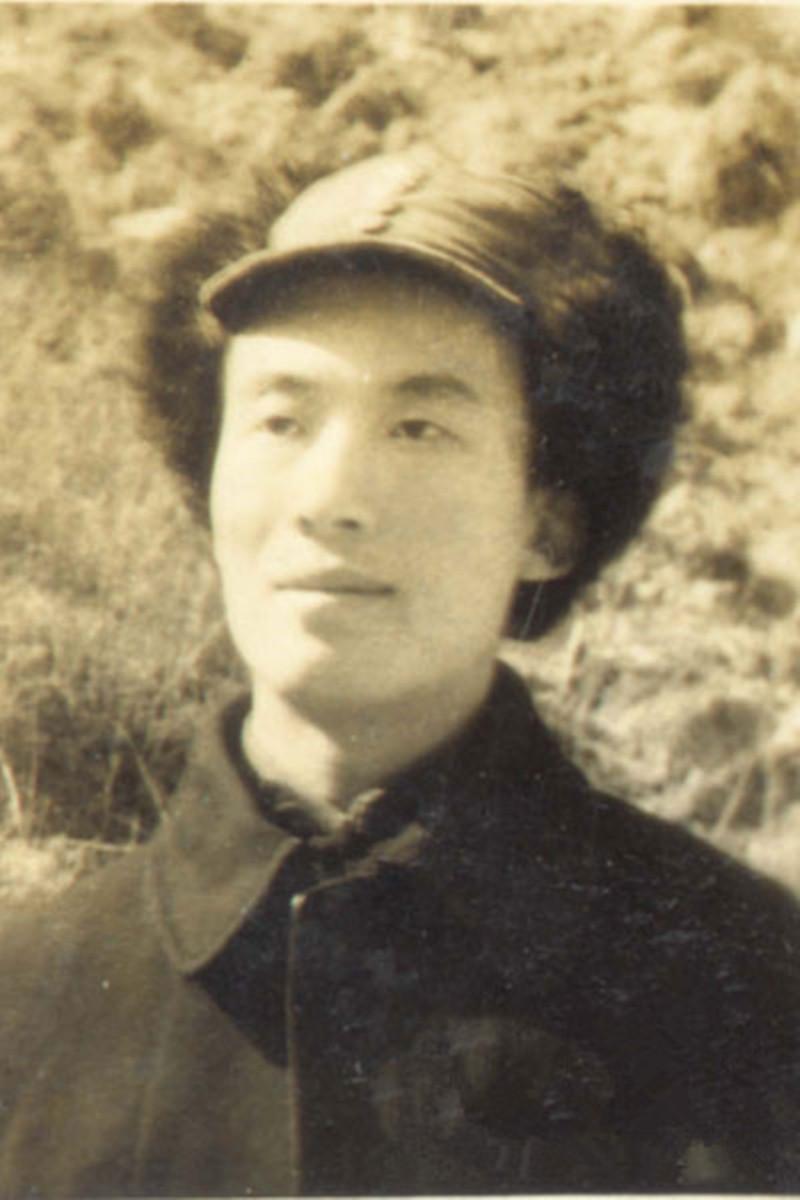1939年2月的一天早上,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没事,就背着手往窑洞外边散步,正想找点灵感。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冼星海慢慢地顺着鲁艺门口的小路走出窑洞,一只手揣在棉衣里,一只手时不时地摸摸下巴。 他来延安已经三个月,习惯了粗粝的小米饭、羊皮袄和风沙扑面的日子,但“心里那点火”始终烧得不旺。 “你问我在巴黎写曲子容易,还是在延安写曲子容易?”他常和学生开玩笑,“巴黎有钢琴有交响乐团,夜里想旋律就去塞纳河边溜达。 可延安呢?脚下全是黄土,家里只有一把破小提琴和半支铅笔。” 其实,刚到延安时他满心热情。那年,冼星海三十四岁,已经写出《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这些激励人心的曲子。 可到了延安,鲁艺的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下地劳动,饭后都去修梯田种豆子。 学生开玩笑:“星海先生,您要不要也来锄地?据说灵感都是在地头种出来的。”冼星海嘴上不说,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散步路上遇到老乡挑水,冼星海停下来搭把手。老乡笑眯眯地问:“先生,你也是来寻思曲子的吧? 前几天鲁艺那合唱,俺娃儿听了回家还唱呢!”这话让他一愣,心想,这荒地能唱出歌来?可不就得从地头找答案吗? 每天的日子都很实在。种地、劈柴、上课、改谱、还要和妻子钱韵玲一起照看小孩。 窑洞里冷得要命,常常是天没亮就得烧火熬粥,晚上还得靠灯芯油灯照着写乐谱。 那天早晨他出来转圈,心里琢磨的是,难道音乐家也只能靠回忆过去写歌? 可延安的学生、战士和老百姓,每天盼的都是“能鼓劲儿”的新曲子。他不能停。 这天走出村口,他看到鲁艺门口已经聚了不少学生,有人在用铁锹挖土,有人围着烧饼炉等着烤馍馍, 甚至还有两个弹三弦的小伙子一边拍手一边唱着自编的顺口溜。冼星海停下脚步,侧耳听了半天。 一位学生见他过来,憋红脸问:“老师,咱们天天劳动,是不是离音乐越来越远?”冼星海一边听他们的顺口溜一边想, 其实劳动和音乐哪有界限?他突然觉得,学生的合唱和老乡的号子、孩子们的吆喝,其实比教室里的乐理课还要真切有力。 就在这一刹那,他脑子里有了新旋律。他回头望着黄土坡,突然问身边的学生:“你们觉得现在的歌,能不能把地头的声音写进去? 比如锄地时喊的调子,比如井边吆喝的节奏?”几个学生都愣住了。冼星海笑道:“音乐要活,得跟脚下这片土地连起来。” 他回到窑洞就抓起铅笔,边写边哼,把上午听到的劳动节奏揉进旋律里。一首新的合唱曲子雏形慢慢浮现。 饭点时钱韵玲端着小米粥进来,见他忘了吃饭,笑着摇头:“你啊,一有想法就管不住自己。”冼星海头也不抬,“灵感就是这么来的。” 这天晚上,他在油灯下一口气写完了两段新的和声。 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可屋里却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他反而觉得,这才是属于自己的“创作时刻”。 不久,《生产大合唱》初稿完成,冼星海把曲子带去让全校师生试唱。第一遍大家还拘谨,唱到第三遍,干完农活回来的学生也跟着唱起来, 有人拍着桌子,有人站起来打拍子,声音在窑洞里越唱越亮。唱到高潮处,门外的几个老乡也凑过来:“这歌像咱们地头的号子,劲头大!” 没过多久,《生产大合唱》在延安公演。冼星海指挥着自己刚写好的曲子,看见台下全是布衣百姓和刚洗完手的农民。 他忽然觉得,音乐从来不只是给专家听的,而是跟这片土地、跟身边这些平凡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后来鲁艺有学生问他:“老师,您觉得在延安搞音乐难不难?” 冼星海笑着说:“难,可只要你听得见人声、看得见烟火气,灵感总会来的。音乐就得为这些人服务。” 再后来,《黄河大合唱》应运而生,成为鼓舞民族的强音。 可冼星海记得,正是那个没事的早上、在窑洞门外听到的劳动节奏,给了他写出作品的“钥匙”。 春天过去,窑洞边的地头又长出嫩绿的苗。冼星海还是会时不时出门散步,寻找新的灵感。 生活的柴米油盐、劳动的呐喊、百姓的期盼,都成了他心里“最真切的歌”。 如今再回望那段时光,你会发现,真正让人难忘的,不只是大合唱的旋律,还有延安清晨黄土坡上的那一点点烟火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