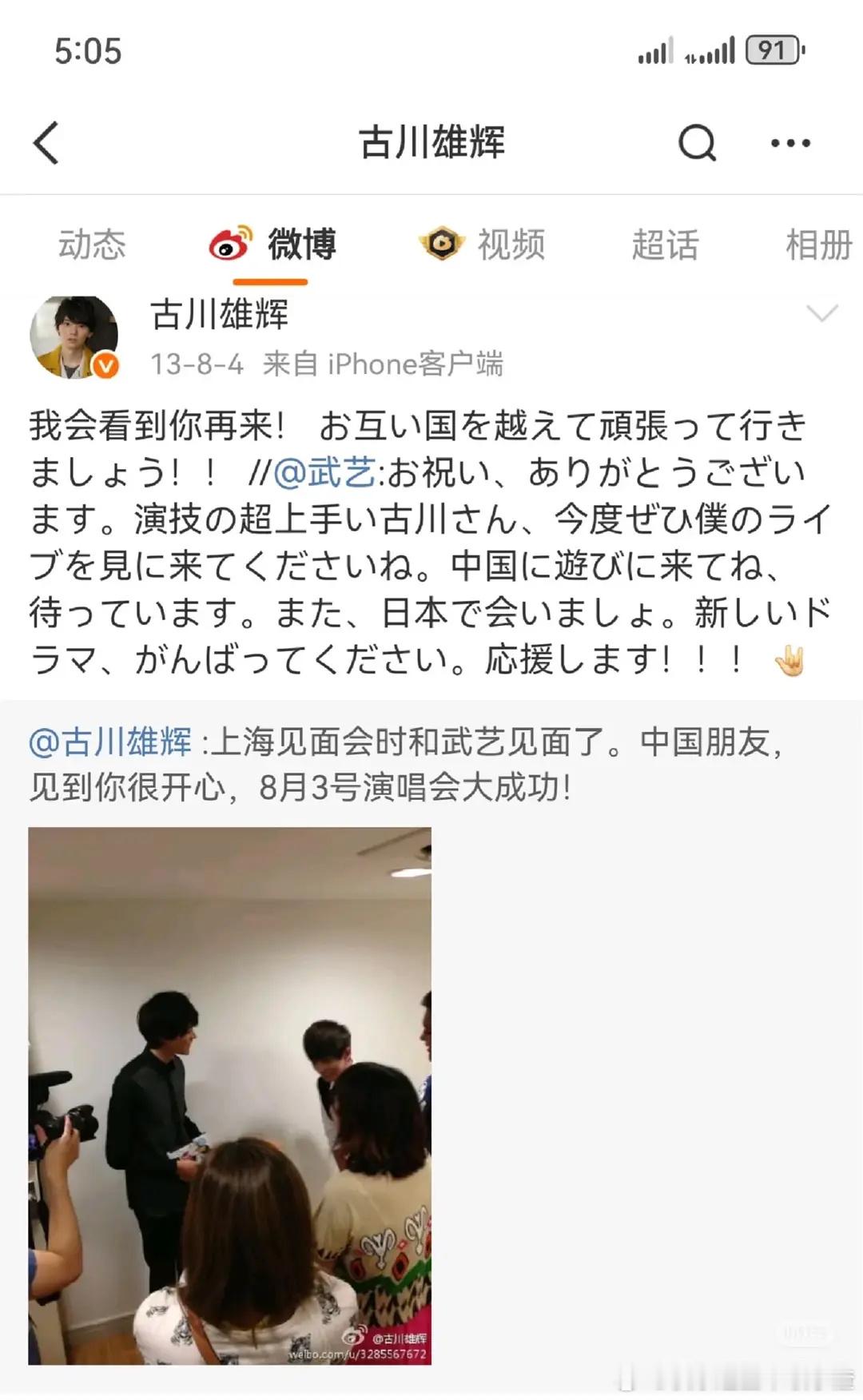小学那会儿,我跟几个小伙伴胆子肥,老爱往附近大学的人工湖跑,偷偷钓鱼。这事儿咱没少干,都成“惯犯”了。
有天运气背,正钓得带劲呢,被校卫队逮个正着。人家见我们是熟面孔,气得不行,不光罚了钱,还打电话把我们学校给捅出去了。
学校领导一听,好家伙,这帮小兔崽子屡教不改啊,火蹭地就上来了。第二天全校做早操,副校长黑着脸,把我们几个“罪魁祸首”拎上主席台。
他挨个点名,开始数落我们的“罪行”:“xxx同学,偷钓三次,头一回罚50,第二回70,第三回60。”接着又点下一个:“xx同学,偷钓两回,第一回70,第二回60。”
轮到我,副校长声音都变了调:“xxx同学,偷钓四次,嘿,头回0元,二回0元,三回0元,四回还是0元。”话刚落音,他自个儿先绷不住,扑哧乐了。这一乐,台下全校师生全跟着哄笑起来。
我当时脸臊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回到家,我眼泪吧嗒吧嗒跟我爸倒苦水,寻思能得到点安慰。结果我爸听完,愣了几秒,突然“噗嗤”一声也笑了,笑得比副校长还大声。我气得直跺脚,心里委屈得要命,却也拿这俩人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