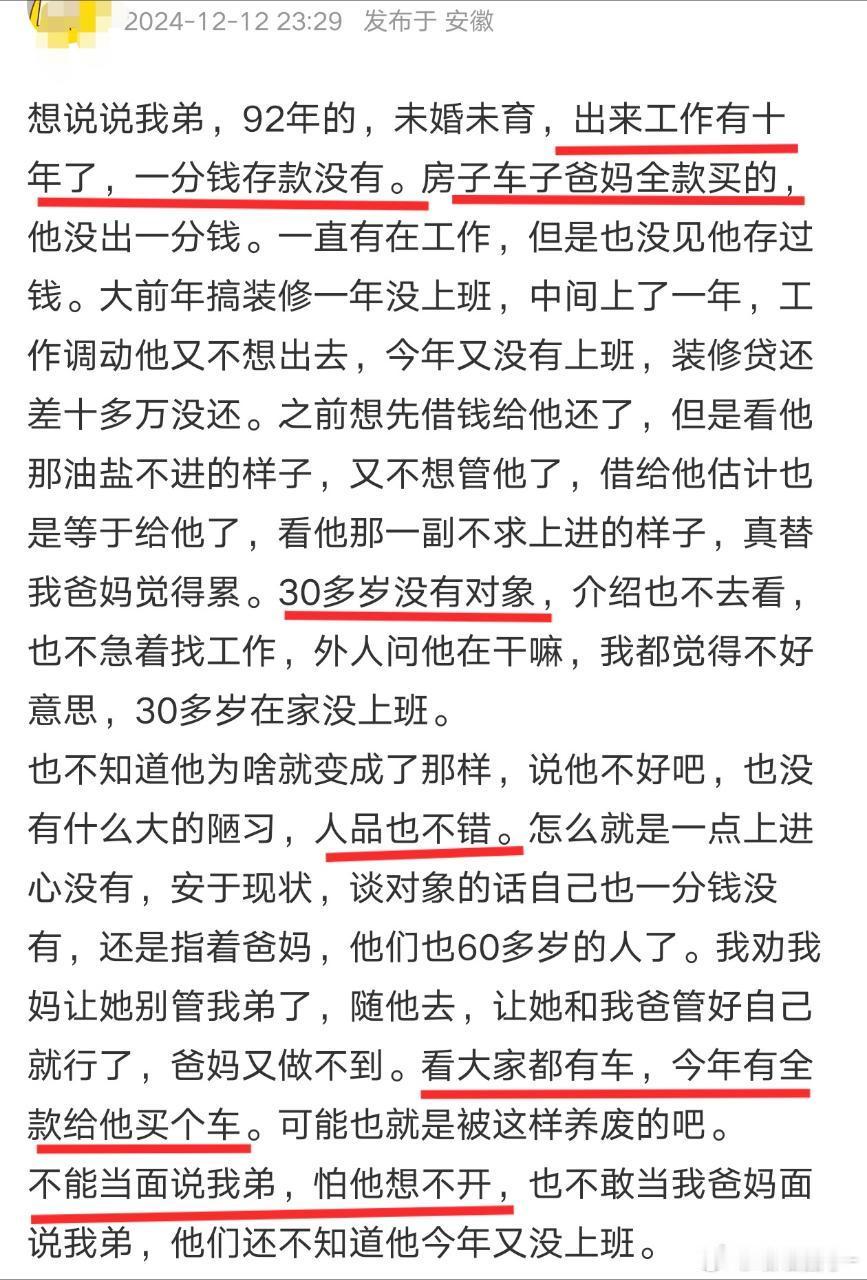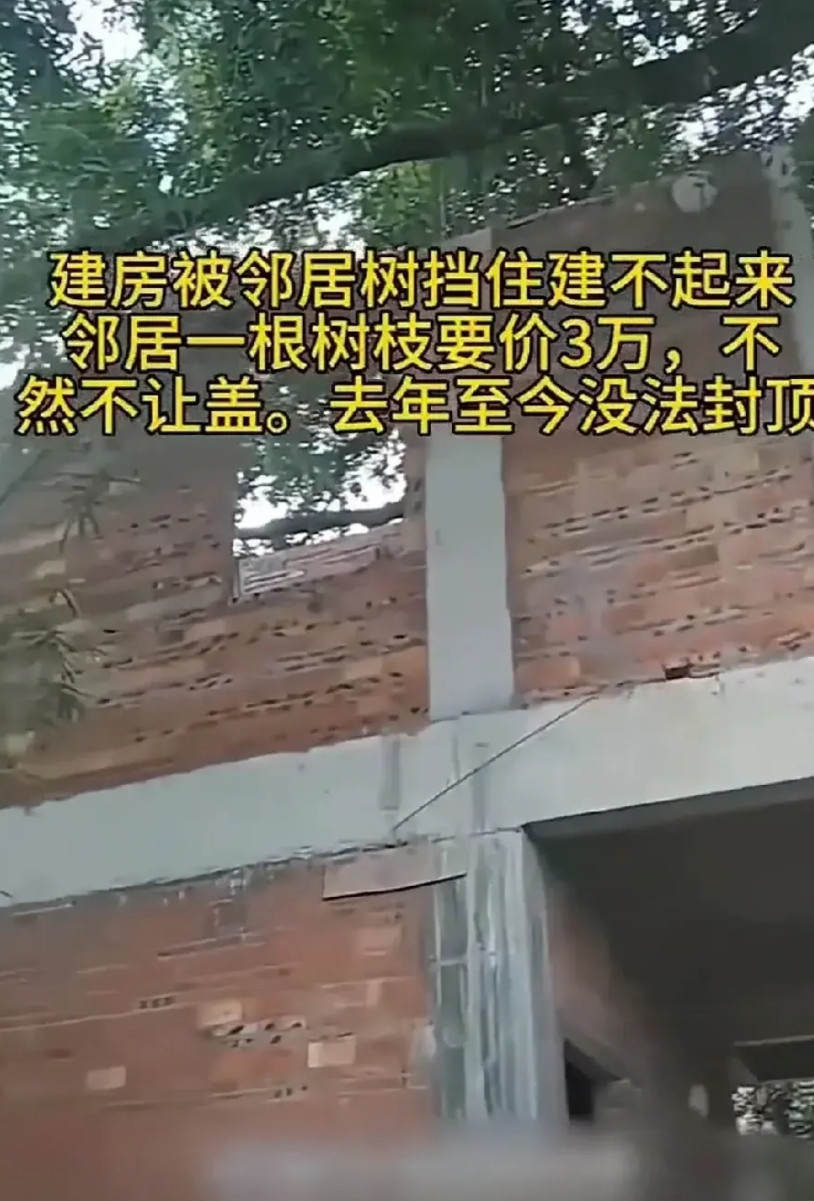姥爷走后第二年春天,姥姥说要租掉老房子。我俩蹲在堆满药盒的厨房里翻东西,我掀开冰箱冷冻层,扯出个冻成冰坨子的塑料袋,肉色发灰,边角还粘着层白霜。
“这肉都长绿毛了吧?”我拎着袋子要扔,姥姥突然伸手拦:“这是你姥爷确诊前买的。”她指尖摩挲着冰碴子,“说等你周末来,给你做宫保鸡丁。”
我喉咙突然发紧。小时候我像跟屁虫似的追着姥爷炒菜,看他把鸡胸肉切成小方块,裹着红亮的酱汁在铁锅里“滋啦”乱蹦。后来我嫌他油放得多,嫌他花生米炸得焦,嫌他总爱多留半碗给我当夜宵。现在想想,那油汪汪的酱汁里,全是他佝偻着背在菜市场挑活鸡的汗味。
“冰箱里老冻着肉,说万一你想吃了呢。”姥姥把冻肉重新塞回冰箱最里层,动作轻得像在藏宝贝。我盯着她发颤的指尖,突然发现她总把降压药和维生素混着吃——姥爷在的时候,这些药片都是他按顿分好的。
昨天我妈翻保险柜时抖出张泛黄的保单,受益人是我,缴费期从我初中就开始了。“你姥爷瞒了所有人,连你姥姥都不知道。”我妈说这话时,我正往嘴里塞外卖,宫保鸡丁的塑料盒泛着可疑的油光。
一万三千块,姥爷每月从退休金里抠出来的钱。他走后三年,这笔钱才姗姗来迟。我突然想起他临终前那几天,总把我的手往被窝外拽,说“热”,可他手背上的针眼都紫成了葡萄。
你身边有没有人,把爱藏得比存折密码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