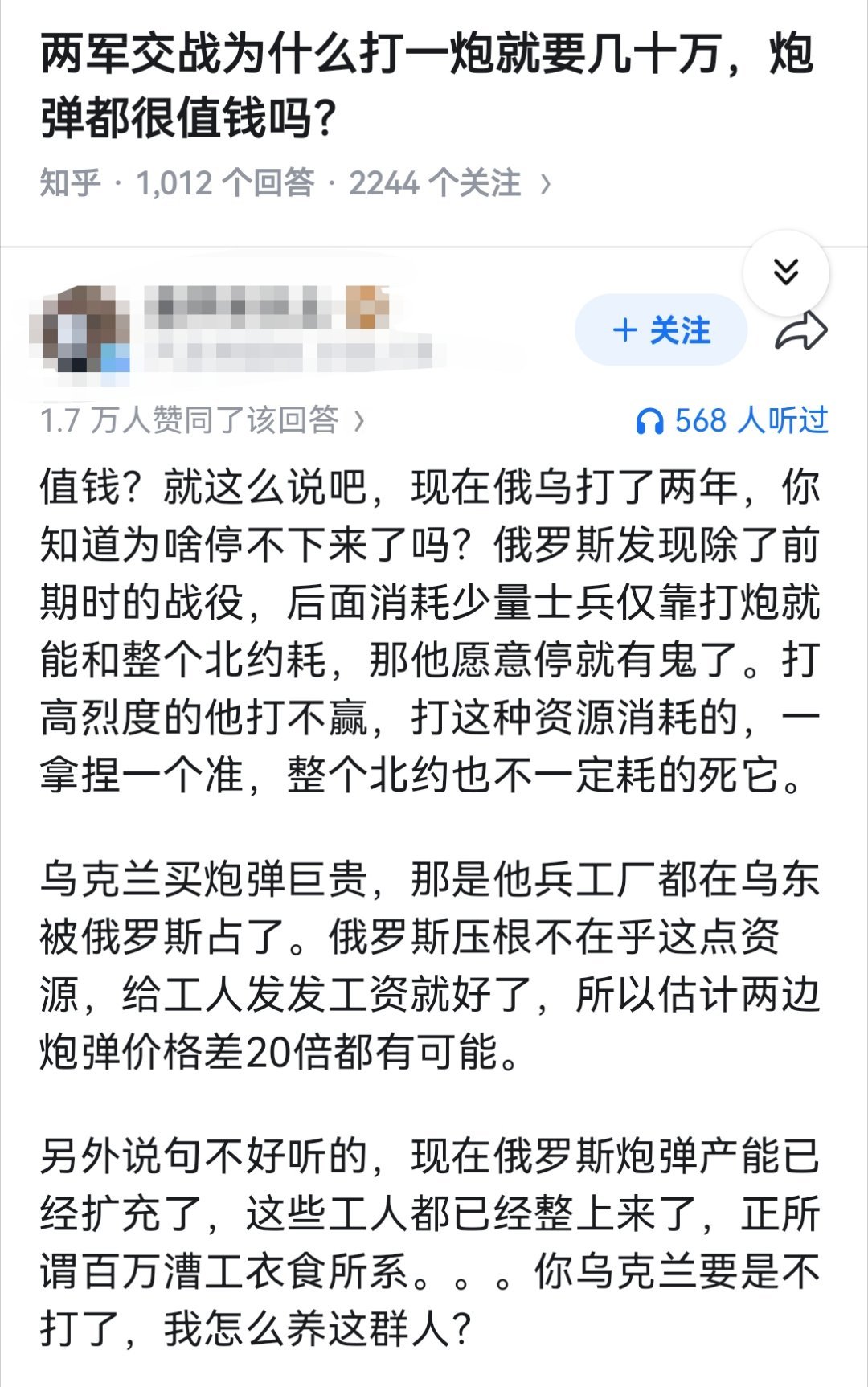1976年,一名20岁战士刚入伍,就想当驾驶兵,却当了三年炊事兵,在战场上,一摸方向盘,就立一等功。 他的名字叫杨建章,四川人。 16岁那年,他就已经在乡下摸熟了解放牌卡车的脾气,一点油门、一脚离合,他都熟得很。 他志愿表上只写了三个字,驾驶兵。 但部队任务不是靠爱好分配的,新兵连之后,他被派到工兵排,成天是挖掩体,抬圆木,力气活没完没了。 第二年被调到通信连,还不是通信兵,是炊事班的灶头兵。 他每天最常握的不是方向盘,而是菜刀和勺子。 连队的饭他做,战士口粮他管,第三年干脆成了猪圈里的专职饲养员,给二十多头猪喂食打扫,照看得干干净净。 他常常在夜里梦见自己坐在驾驶室,醒来后还要硬撑着割一车猪草,把菜地挑水挑肥,种得绿油油一片。 他也犯过犟,偷偷去汽车连帮士官擦车,蹲在车边琢磨仪表盘,一个人练挂挡的顺序,在脑子里一遍遍回带。 老兵笑过他,汽车连没你位置。 但这事他没放下。 整整三年,他除了两次“学雷锋标兵”和一张三等功,一次机会都没等来。 1978年,他身体垮了,连续发烧,确诊肠结核。 住院住了不止一次,父母劝他退伍,还劝他回去安排个国企工作算了。 连队也准备批准他复员,说好好养病要紧。 可这个平时最听话的小伙子突然一口回绝,还递了三封请战书,一份比一份字写得歪。 就在队伍即将开拔时,他又送上一封血书,说得明明白白,不上火线死不瞑目。 他还是跟上了部队,被编到战勤支援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给连队送粮送水。 战场不像想象中那种轰轰烈烈,现实很艰难。 刚进入登尚地区不久,部队连着行军三天,什么都带,就是不能动单兵口粮。 前线通信兵得守着机器不动,饿得身体发软,连个频道都调不准。 杨建章冒着危险进了山林,抓到什么生的野菜就往嘴里塞。 结果中了毒,当场吐得全身打摆子,幸好一位送弹药的民工救了他,还教他怎么认木薯。 那天晚上他就背回几十斤,那木薯成了全连唯一可吃的口粮。 哪怕自己没得吃,他也从不多留。 他把分给自己的干粮偷偷塞给别人,自己啃野芭蕉芯,塞嘴里慢慢嚼,咽不下他就含着。 哪怕发高烧,他也不松手,只愿亲自将口粮袋背到底。 他说炊事兵的枪是口粮袋,只要人还在,枪就不能丢。 这话不是感慨,是他一贯的心气儿。 整场战斗改变他的,不是某次殊死搏斗,而是一次炮火突袭。 1979年3月5日,团指挥所突遭越军火力覆盖,炮弹像下雨一样砸下来。 给养车司机被炸晕,救护车已起火,前后通信都用不上了。 敌人要是继续打下去,团部和四个连队上百号人全会暴露。 就在混乱中,他冲上去开口说自己能开车,没人拦得住他。 三年了,这双最多摸过锅铲的手,终于按上了方向盘。 挂挡、踩油、转弯,久违的感觉一上手就回来,他直接把车开出了掩体,没有往远离战火的地方跑,而是调头冲向反方向,越军炮火覆盖区。 这不是自杀式的瞎撞,这是军事判断。 他要用自己和车做引敌火力的诱饵,给战友夺出一点生的时间。 挡风玻璃被炸没了,弹片像暴雨倾盆打在驾驶舱上,他干脆半个身子探出车窗,使劲朝远处挥手。 很多战士看见了这一幕,他像在说:往我这打。 那些炮火拔掉方向盘的那一刻,他带不走任何东西,只有一只死死抓在怀里的口粮袋。 事后整理遗物,他身上的木薯也被找见了,只剩一点,已经被火烤糊,变成一块黑炭。 那是他没舍得吃的储粮,出发前还往衣兜塞了一把,最后也没来得及留给别人。 这一次驾驶,是他军旅最后的百米路程。 越军停止了攻击,指挥所也保了下来。 评功时他被追记一等功,部队给他定格的称号是“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的名字刻在烈士陵园碑上,每年清明,一位当年教他识木薯的老工人都会来放一束花。 老兵头白了,总念叨着,这个四川的小伙子救下的那群通信兵,现在都该当爷爷了。 连队保留下来的那根扁担,一头挂粮袋,一头挂急救包,现在是通信连最硬气的传家宝。 他不是高光英雄,也没打下什么重要据点,但他用自己一百米的行驶,把战斗最紧张的缺口挑了起来。 他是炊事兵,但没人在乎他岗位名头,只记得方向盘交到他手里那一刻,他从没松劲,直到最后一秒。 他就像几十年来千千万万个普通士兵那样,梦想某个位置,结果被命运挪到了另一个地方,然后死死地干,把梦想烧进了手上的活里。 或许有人会说他付出得太重,连命都搭上了,可在那个年代,有一些人就愿意往前冲,不需要谁叫唤,不需要别人看见。 到最后也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