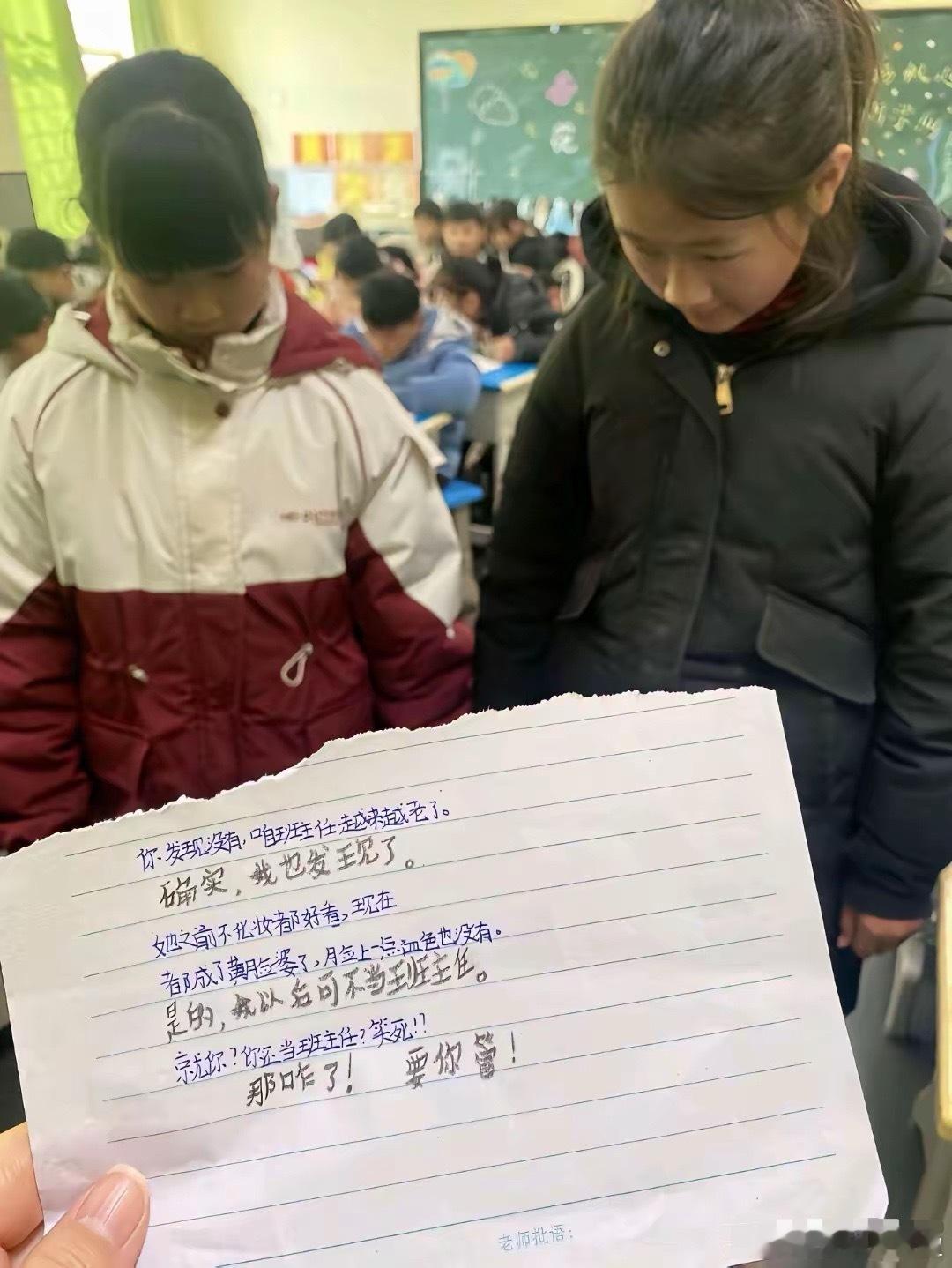我二叔当年干民兵营长时,保护一个下放的老干部,后来这个老干部落实政策回城了,当了副部级干部,我二叔就去找他,请他帮子女安排工作,这位干部根本不理我二叔。 二叔捏着那袋干豆角,走在陌生的大城市街上,脚像灌了铅。天擦黑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他寻思着找个最便宜的小旅馆凑合一宿,明早赶火车回家。路过一个街边公园,他看见长椅上坐着个老太太,脚边放着个大编织袋,正捂着胸口,脸色很不好。 二叔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大娘,您这是不舒服?”老太太点点头,说心慌,老毛病,药吃完了。二叔看她一个人,编织袋里露出些塑料瓶和纸壳。他放下自己的布袋子,说:“您等着,我瞅见那边有个药店。” 他小跑着去了药店,用自己的钱买了瓶速效救心丸,又跟店员要了杯温水。伺候老太太吃下药,守了她半个多钟头,看她脸色缓过来了。老太太拉着他的手,千恩万谢,非要他留下名字地址。二叔摆摆手,只说自己是路过,该做的。老太太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个皱巴巴的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了个电话号码塞给他:“我儿子电话,你以后要是在省城有啥难处,打这个电话,就说帮过公园里的周老太。” 二叔没当真,客气地收下纸条,和那袋干豆角一起塞进了中山装的内兜。他把老太太送到能看见的公交站,看她上了车,才转身去找住处。 回家后,日子照旧。老大工作的事,二叔后来托了远房表哥,在县里的粮站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虽然钱不多,但总算稳当。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被他随手夹在了家里的老户口本里,渐渐忘了。 大概过了大半年,村里要修一条连接省道的水泥路,指标紧,好几个村都在争。村长急得嘴上起泡,知道二叔去过省城,硬拉着他一起去跑手续。在省交通厅,他们人生地不熟,连门都摸不着,更别提找管事的人了。二叔在走廊里发愁,手无意间摸到内兜,忽然想起那张纸条。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思,他找到公用电话,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个声音沉稳的男人。二叔磕磕巴巴说了周老太和公园的事。对方沉默了几秒,说:“我知道了。你们现在在哪儿?” 两天后,村里修路的批文就下来了,顺畅得让村长不敢相信。后来才隐约听说,接电话的人是周老太的儿子,在省里某个很重要的部门工作。二叔没再去深究,也没跟人炫耀。他只是觉得,那天傍晚走进那个街边公园,大概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之一。那袋没送出去的干豆角,最后自家过年炖肉吃了,特别香。
感觉这玩意能把美国人的脑壳看烧了。
【1评论】【1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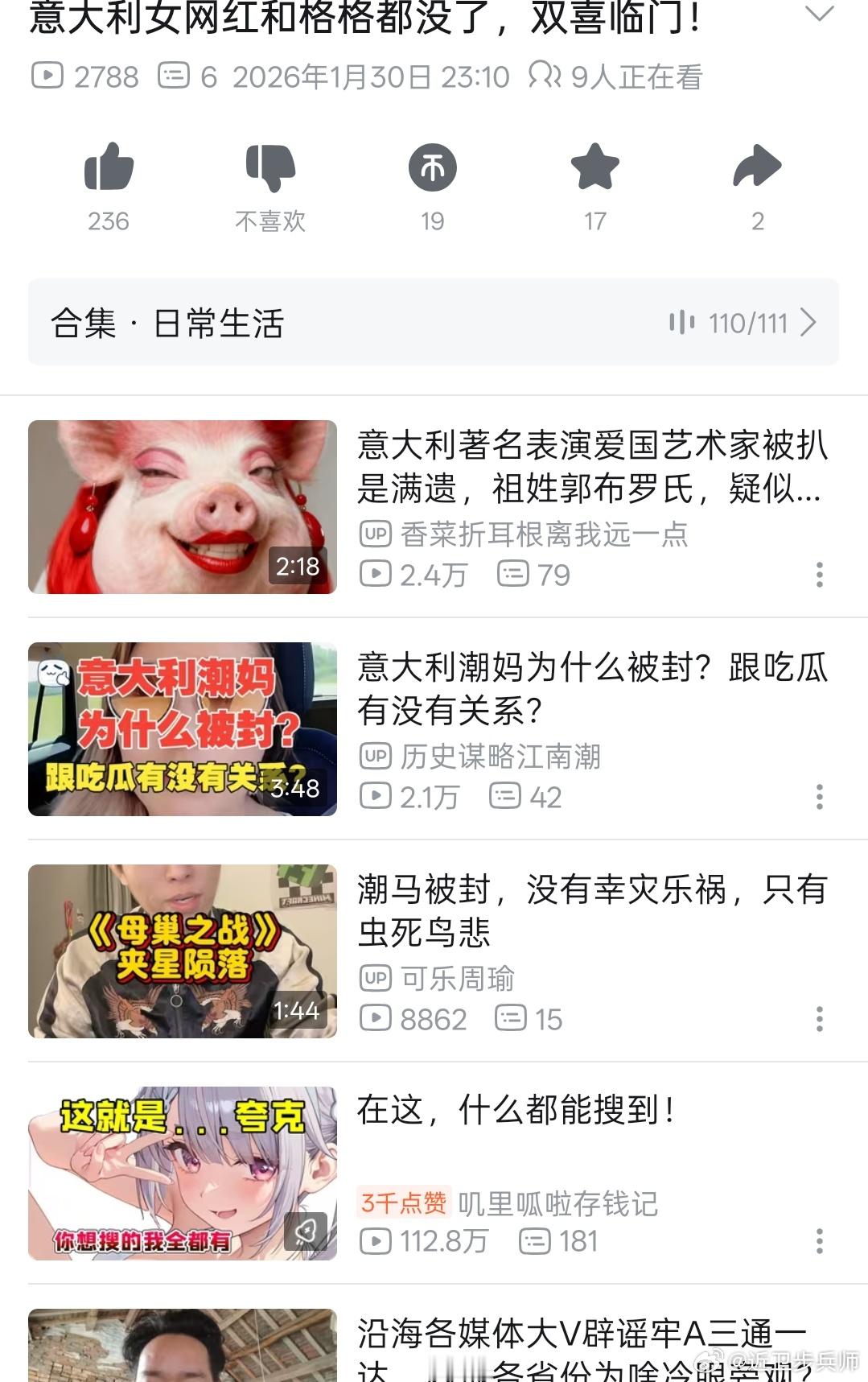
![辛辛苦苦润出去,你们不仰望我,那我不是白润了[doge]近日,一个润去美国的润人](http://image.uczzd.cn/866960318641367997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