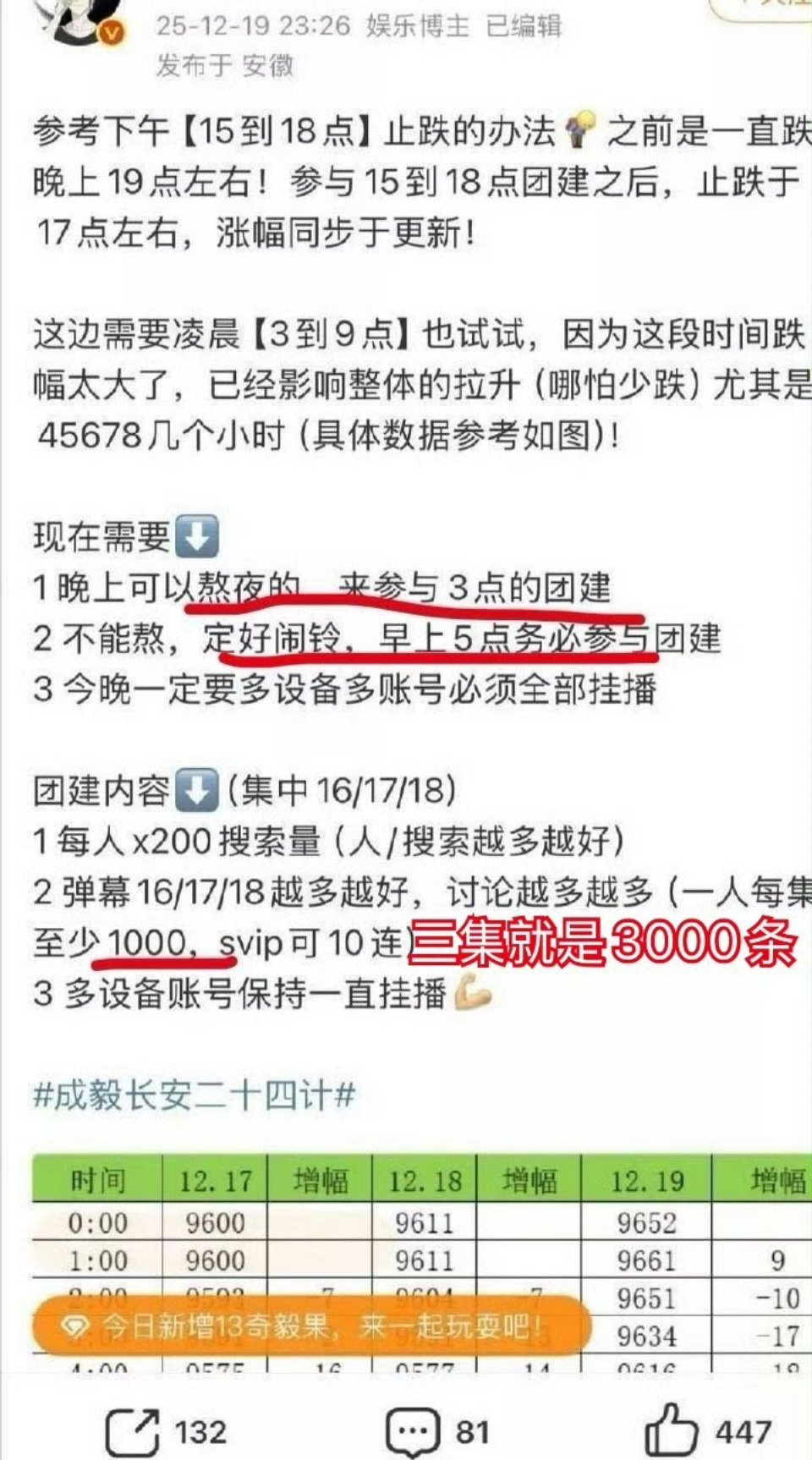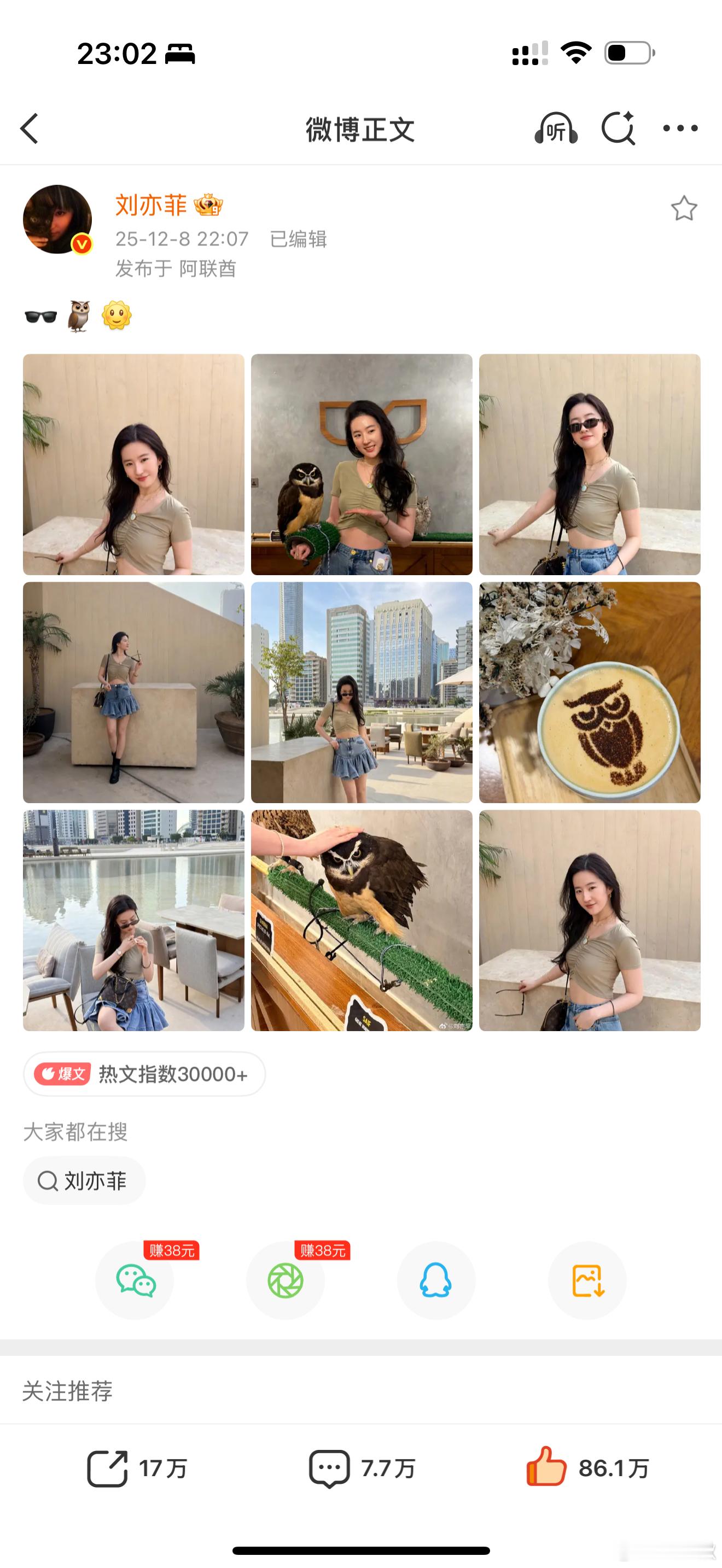我们村里曾经发生过一件怪事,始终也无法解释。村子里住着一个铁匠,是外姓,不是本村人,他媳妇长像很特殊,个矮瘦小,平胸,经常留着超短发,打眼猛一看,简直不像一个女人,而铁匠却是一米七丶八的大汉,膀大腰圆,力大如牛。 我们村老王家的铁匠铺,常年飘着铁屑味。 老王一米八的汉子,抡锤时胳膊上的青筋能蹦出二寸高。 他媳妇却像块没发起来的面团,矮矮瘦瘦,头发比村里小子还短,夏天总穿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打远处看,谁都以为是老王收的徒弟。 那年头村里婆娘聚堆纳鞋底,总有人拿眼角瞟铁匠铺:"你说怪不怪?" "哪有女人家不长头发的?" "听说夜里睡觉都不脱衣裳......" 我第一次见她说话,是在村东头的井台边。 老王挑着水桶过来,她正弯腰系鞋带,后颈晒得黢黑,露出一小截突出的椎骨。 "水满了。"她声音沙沙的,像砂纸蹭过木头,却伸手稳稳扶住老王晃荡的水桶,指节上全是老茧。 真正让议论声小下去的,是那年秋天。 老王给生产队打犁铧,淬火时火星溅到柴堆上,火舌"腾"地窜起半人高。 我们都端着水盆往那跑,就见他媳妇从铁匠铺里冲出来,手里攥着条湿棉被——她居然把自己睡觉的褥子扯下来了! 火苗燎着她额前的碎发,她眼睛都没眨,直接把棉被摁在最旺的火头上。 后来我才发现,她不是不长头发。 有回赶夜路经过铁匠铺,看见昏黄的油灯下,她正给老王缝补工装,后脑勺用根红绳扎着个小小的揪揪,像株倔强的狗尾巴草。 老王坐在旁边拉风箱,风箱呼嗒呼嗒响,他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铁钳上的火星子,竟烫红了耳根。 现在想想,那些年我们盯着她平平整整的胸脯、短得扎眼的头发、沉默寡言的样子,以为看懂了什么。 其实呢?我们只看懂了自己眼里的尺子。 她会在老王咳嗽时,默默把灶上的水壶往他那边挪半寸;会在冬夜里,把冰冷的铁砧焐热了才让老王开工;会把攒了半年的布票,换成块蓝布给老王做新褂子,自己依旧穿着那件发白的旧衣。 人这一辈子,哪有什么该有的样子? 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旁人说的。 就像老王打铁,旁人只听见叮当响,只有他媳妇知道,哪一锤用了几分力,哪道火星子代表铁水正合适。 如今铁匠铺早拆了,老王和他媳妇也搬去了镇上。 但每次路过那片空地,我总觉得还能闻到铁屑混着皂角的味道——那是她给老王洗衣服时,皂角在石板上搓出的泡沫香。 你说,那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 或许,从她攥着湿棉被冲向火堆的那一刻,答案就已经烧进了铁里,淬成了钢。
沒想到陆挺终于捅破了这层遮遮掩掩的窗户纸!闹半天,陆赫竟然是陆挺
【24评论】【20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