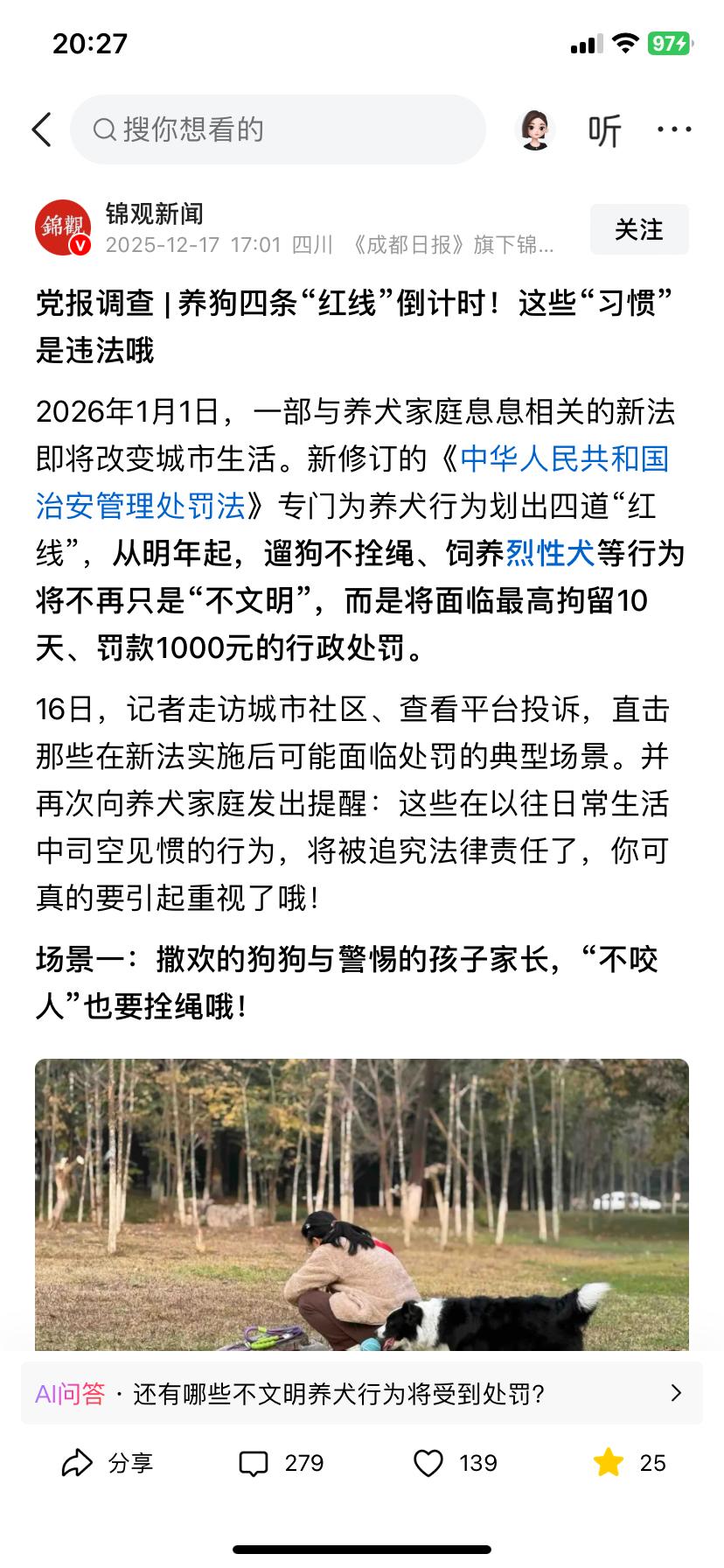有一老汉上街里,坐公交车回家,他越看对面的老太太越眼熟,他对老太太说,大妹子,你家在哪里住呀,我看你怎么这样子有缘分,莫非咱俩前生是夫妻?老太太抬眼打量老汉半天,慢悠悠开口,我家在桥东头老槐树巷第三排。 午后的公交车晃悠着穿街过巷,车窗外的树影碎在老汉的蓝布衫上。 他刚从街里买完药,兜里还揣着没拆封的创可贴,指尖蹭过塑料包装的棱,有点发涩。 对面座位的老太太一直垂着眼,花白的头发用黑网兜拢着,露出的耳背有颗小痣——这痣,怎么跟记忆里的那颗重合了? 老汉盯着那颗痣看了三站地,公交车报站的电子音都变模糊了。 老太太终于抬眼,目光扫过他手里攥皱的药盒,停在他眼角的皱纹上——那皱纹里像藏着几十年的风。 “大妹子,”老汉的声音比车轱辘还颤,“你家……住哪片啊?” 他咽了口唾沫,喉结动得明显,“我瞅你咋这么面善,莫不是……上辈子在哪见过?” 问完自己先红了脸,觉得这话比街里小贩的吆喝还莽撞。 老太太没笑,也没皱眉,只是把手里的竹编篮往腿中间挪了挪,篮底露出半块没吃完的红糖糕。 “桥东头,”她慢悠悠地说,每个字都像从旧棉絮里掏出来的,“老槐树巷,第三排。” 老汉的脑子“嗡”一声,手里的药盒“啪嗒”掉在脚边——老槐树巷第三排,那不是他住了半辈子的地方吗? 可他分明记得,巷子里的张婶前年搬走了,李家阿婆去年冬天走了,哪还有这样耳背带痣的老太太? 难道是自己老糊涂了,把梦里的人安到了现实里? 事实是他在那巷子住了五十年,闭着眼都能数清砖缝里的草;推断是这老太太若不是新来的,就该是刻在巷尾老墙上的名字;影响是他突然想起,十八岁那年隔壁窗台上总摆着一碗红糖糕,主人耳后也有这么颗痣。 公交车“吱呀”一声靠了站,热风裹着烤红薯的甜香灌进来。 老汉弯腰捡药盒时,看见老太太的布鞋沾着巷口特有的红泥——那泥只有雨后的老槐树底下才有。 有时候熟悉不是因为见过,是因为某颗痣、某个住址,甚至一句慢悠悠的话,都在替时光喊你的名字——你敢不敢停下来,问问那句“眼熟吗”? 老太太把红糖糕往他这边推了推,竹篮把手磨得发亮。 公交车报站音突然清晰:“老槐树巷到了,请下车的乘客……” 阳光从车窗溜进来,刚好照在两人中间的空位上,像一块没写完的空白。
有一老汉上街里,坐公交车回家,他越看对面的老太太越眼熟,他对老太太说,大妹子,你
好小鱼
2025-12-21 14:51:02
0
阅读: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