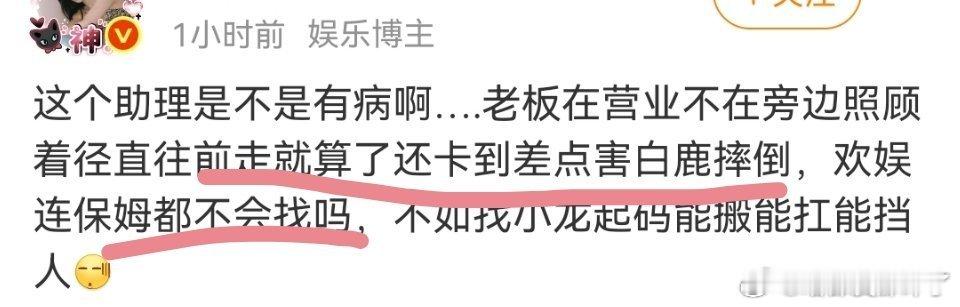我爷爷那一辈亲兄弟两个,我爷爷是老大。我爷爷有5个儿子,二爷爷没有儿子,只有3个女儿,商量后就把三叔过继给了二爷爷。那年三叔才八岁,抱着自己的小包袱从东屋搬到西院时,把爷爷给的一把花生糖全塞给了我父亲,糖纸在晨光里亮得刺眼。 我爷爷和二爷爷是亲兄弟,俩院子挨着火墙,东屋住我家,西院是二爷爷家。 爷爷五个儿子,炕上铺盖卷挤得像捆柴火;二爷爷三个女儿,灶台上总飘着女孩们叽叽喳喳的笑。 那年秋天,族里老人揣着旱烟袋来,蹲门槛上抽了三袋烟,说:“老二家没根苗,过继个小子吧。” 三叔八岁,成了那个“小子”。 他抱着小包袱站在东屋门槛上,包袱角露出半块打补丁的蓝布——那是奶奶连夜给他缝的新里子,针脚密得像撒了一把星星。 爷爷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塞他手里:“路上吃。”是裹着芝麻的花生糖,村里供销社逢年过节才有的甜。 可三叔没吃。他攥着油纸包跑到父亲面前,把糖一颗颗往父亲兜里塞,糖纸窸窣响,橘红的、翠绿的,在晨光里亮得刺眼。 你说八岁的孩子懂什么是“过继”吗?他只知道要搬去西院了,要睡二爷爷家那张空着的小床了,以后不能跟大哥挤一个被窝听故事了。 搬家那天,父亲追着他跑到西院门口,攥着他的手不放,指节都白了。二奶奶红着眼圈来拉:“让孩子进来吧,晚上我让他跟你睡。” 三叔却突然松了手,转身跑进西院,没回头。 头几天,他总在西院墙根下转悠,眼睛往东边瞟。二爷爷喊他:“小三,过来劈柴。”他“哎”一声,斧头却劈歪了,木渣子溅到鞋面上。 二奶奶看在眼里,第二天煮了六个鸡蛋,塞他兜里:“给你哥送去。” 三叔捏着热乎的鸡蛋,跑起来像阵风,到东屋门口却慢了,扒着门框往里瞅——父亲正帮奶奶喂猪,裤腿上沾着泥。 他把鸡蛋往窗台上一放,转身就跑,衣角带起的风,掀动了窗台上那本父亲没看完的小人书。 后来的日子,东屋西院的炊烟总往一块儿飘。三叔学会了帮二爷爷编筐,筐底编得比谁都密;父亲学会了帮二奶奶挑水,桶里的水晃悠着也洒不出几滴。 每次三叔从西院过来,兜里总鼓鼓囊囊的:有时是二奶奶晒的柿饼,有时是二爷爷上山摘的野枣,他都一股脑塞给父亲,像当年塞那把花生糖一样。 有人说过继是分了家,可东屋的水缸空了,西院的扁担会自己过来;西院的油灯没油了,东屋的灯盏会悄悄递过去。 去年整理老屋,在父亲的旧木箱底,翻出个铁盒子。 打开一看,里面躺着张泛黄的玻璃糖纸,边角磨得圆滚滚的,阳光透过糖纸照在墙上,映出一小片模糊的彩光——像极了那年早晨,三叔塞给父亲糖时,糖纸在晨光里亮起来的样子。 父亲摸着糖纸笑:“你三叔后来总说,那天他其实没跑远,就躲在西院那棵老榆树下,看我把鸡蛋一个个剥开,蛋黄噎得我直伸脖子。” 原来有些离别,不是走散了,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把日子过成糖。 现在我每次回老家,还会去西院看看那棵老榆树,树下的泥土里,好像还埋着两个孩子没说出口的话:不管东屋西院,咱们永远是兄弟。
我爷爷那一辈亲兄弟两个,我爷爷是老大。我爷爷有5个儿子,二爷爷没有儿子,只有3个
好小鱼
2025-12-19 11:50:42
0
阅读: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