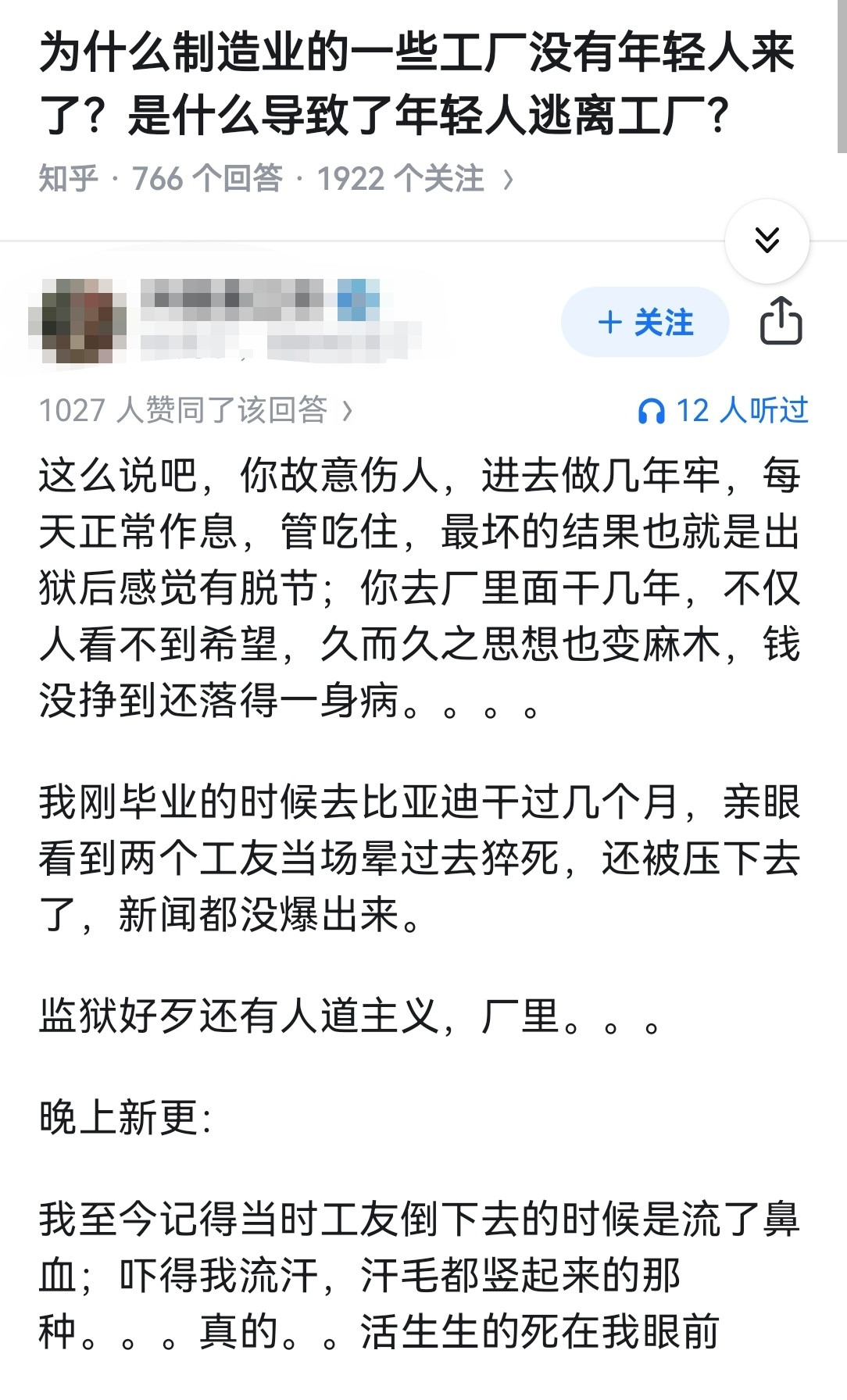当年,郭宝昌拉着养母的手:“老娘,咱把房子捐了呗,我也能有个好前程。”养母嘴巴一抽搐:“我是500大洋买来的,比你多300,你凭啥在我面前豪横!”临死前,养母只说了三个字,让郭宝昌后悔一生。 郭宝昌刚记事时就摸透了郭家的底细:他本姓章,亲生母亲生在北平城郊的穷村子,连着生了几个孩子养不活,把他卖到郭家时,只换了200块大洋。养母郭榕是郭家老爷子花500大洋买来的姨太太,比他早进郭家三年,这事她总挂在嘴边,不是要压着他一头,是夜里点灯纳鞋底时,摸着手上的茧子,能念叨出自己这辈子的来路——她从小没了爹娘,被叔伯卖到人贩子手里,转了三手才到郭家,这栋坐落在西城的四合院,是她在大宅门里唯一能抓得住的东西,比命还金贵。 郭榕没上过一天学,却把郭家的日子打理得滴水不漏。凌晨四点就起来生炉子熬小米粥,给郭宝昌梳羊角辫,盯着他背《三字经》,他要是偷偷溜出去跟胡同里的孩子掏鸟窝,她不打也不骂,就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给他做的千层底布鞋,眼泪砸在鞋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这辈子没盼过别的,就盼你能读成书,将来能自己说了算,别像我这样,一辈子由着别人摆弄。”郭宝昌那时候嫌她唠叨,捂着耳朵跑开,压根没瞧见她望着自己背影时,眼里混着期盼和心酸的模样。 1950年的夏天,郭宝昌揣着戏剧专科学校的招生简章回了家,张口就提捐房子。那时候北京刚解放,文艺界正号召工商界人士捐产支援建设,他打听到捐了家产的子弟考学能被优先考虑,满脑子都是舞台和剧本,拉着养母的手说得热火朝天,没注意到她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干净。 等他说完,养母才扯着干裂的嘴唇说出那句戳心的话,郭宝昌年轻气盛,只觉得她眼界窄,不懂“大局”,爷俩在院里吵了三天,最后是养母半夜摸着黑找出房契,往他手里塞时,指尖抖得厉害:“你要走你的阳关道,我不拦着,别将来后悔就行。” 房子捐出去的第二天,郭宝昌就揣着录取通知书去了戏校,可他和养母的关系就断了弦。放假回家,院里的石榴树还是老样子,可桌上再也没有他爱吃的炸酱面,养母也不再坐在炕沿上问他功课,俩人对着坐半个时辰,能憋不出一句话。他心里憋着气,觉得养母不理解他,直到胡同口的张奶奶偷偷拉着他说,养母把陪嫁的金镯子当了,给他寄了十块钱生活费,还跟人念叨:“我儿子去北京学能耐,这点东西值不当啥,别委屈了他。”郭宝昌捏着兜里的汇款单,鼻子酸得厉害,却愣是拉不下脸跟养母说句软话,扭头买了张回北京的火车票。 这一别就是五年,等他再接到家里的电报,只写了四个字:母病速归。他连夜挤上绿皮火车,回到家时,郭榕已经躺在炕上起不来了,颧骨高高凸起,眼窝陷进去,只剩一双眼睛还亮着,死死盯着他。他跪在炕边,攥着养母干瘦的手,想说对不起,想说自己错了,话到嘴边却堵着,半天吐不出一个字。郭榕看着他,张了张没牙的嘴,费了老大劲,才挤出三个字:“不怪你。”话音落,手就从他掌心里滑下去,再也没抬起来。 郭宝昌在炕边跪了整整一夜,眼泪把前襟泡得透湿。他这才琢磨明白,养母不是舍不得房子,是舍不得自己这辈子的根——那栋四合院是她从人贩子手里逃出来后,唯一能称得上“家”的地方,她捐出去,不过是疼这个没血缘的儿子,愿意把自己最后的依靠,换成他想要的前程。后来他写《大宅门》,白文氏身上藏着郭榕的影子:那个嘴硬心软,一辈子撑着家,把所有念想都搁在孩子身上的女人,他把半辈子的愧疚都揉进剧本里,可写得再真,也换不回养母临死前那三个字里的原谅。 他晚年总跟采访的记者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写《大宅门》磨了几十年,是当年逼着养母捐了房子,是没来得及跟她说一句“娘,谢谢你”。那栋被捐出去的四合院,成了他心里永远填不上的窟窿,而养母的三个字,像根针,扎在他心上六十多年,提醒他,人年轻的时候总盯着远方的光,却忘了身后给你撑着灯的人,一旦走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们总在追逐所谓的“前程”时,把亲人的包容当成理所当然,仗着他们爱得深,就肆意消耗那份真心。郭宝昌和养母的故事,藏着太多人的遗憾——那些嘴上的“计较”,不过是他们把爱揉碎了,藏在柴米油盐里,我们总要等失去了,才看懂那些碎碎念里的牵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