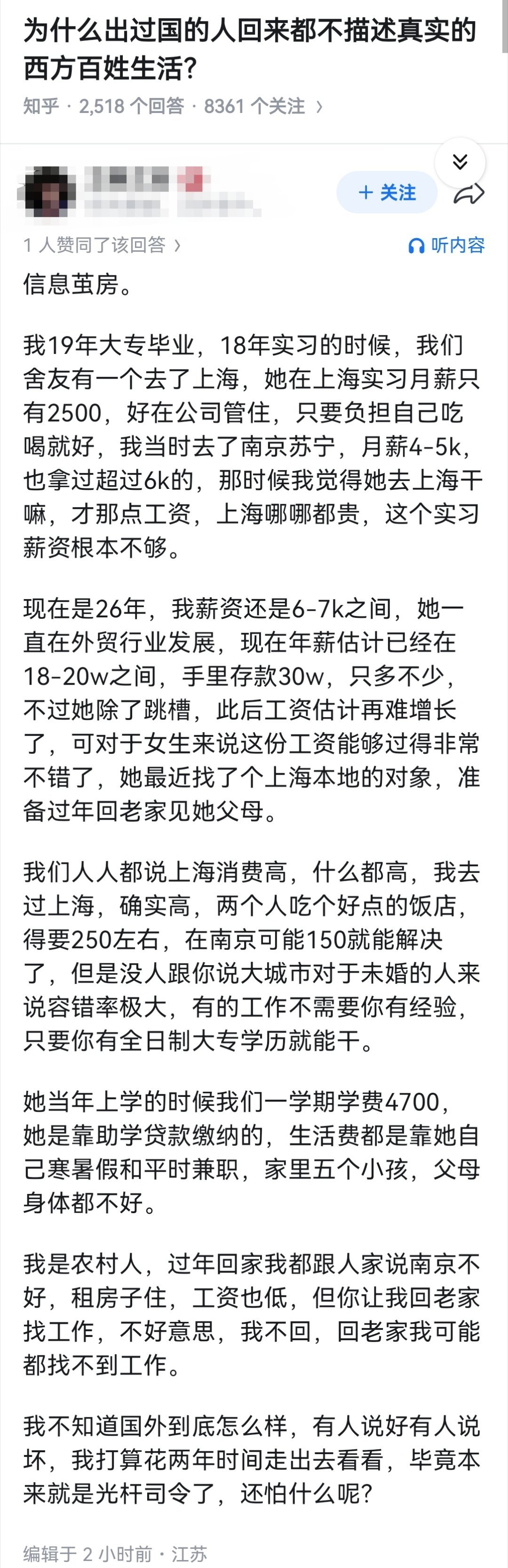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有超过300万中国军民因伤口感染丧生,每十个受伤者中,就有八个倒在了“等不到药”的绝望里。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无数家庭的破碎,而这份苦难,深深揪着每一位爱国医者的心,汤飞凡便是其中最坚定的一员。 或许很多人听过“汤飞凡造青霉素”的传闻,但今天要讲的,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他从未研制过青霉素,却用另一种方式,拯救了数百万同胞的生命。 作为湘雅医学院首批高材生,汤飞凡曾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在微生物学领域崭露头角,本可留在条件优渥的海外,拥有光明的科研前景。 可心系祖国的他,早已看穿战乱背后的医疗危机,毅然放弃一切,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扛起了防疫救国的重担。 彼时,中央防疫处因战乱从北京一路南迁,最终落脚在昆明郊外高峣村的荒滩上。 所谓的“实验室”,其实就是几间漏风的土坯房,连像样的显微镜都要小心翼翼用布包着防灰,经费短缺、耗材匮乏,每一步都难如登天。 但汤飞凡从未退缩,他深知,抗战不仅是战场的厮杀,更是防疫的较量。 前线将士受伤后,除了伤口感染,霍乱、鼠疫等传染病更易趁虚而入,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他召集魏曦、朱既明等顶尖人才,开读书会、钻研文献,即便身处绝境,也始终没有与国际科研脱节。 就在汤飞凡潜心研制防疫疫苗的同时,另一群爱国医者也在为青霉素难题拼尽全力——樊庆笙、童村等微生物学家,同样在昆明的简陋环境中,开启了中国青霉素的试制之路。 他们没有先进设备,就拆废旧汽车零件改装手摇离心机;没有恒温箱,就用木板钉箱、点煤油灯手动控温;没有进口培养基,就用玉米浆代替,凭着“蚂蚁啃骨头”的韧劲,一点点突破难关。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发现,有人在发霉的物品上发现了青霉菌,科研团队小心翼翼刮下绿霉培养,最终分离出高产青霉菌株。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1944年9月,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在昆明试制成功,5小瓶、每瓶5000单位,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数量,却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前线伤员带来了生的希望。 而汤飞凡的战场,就在隔壁的土坯房里,他带领团队不分昼夜,攻克牛痘疫苗、狂犬疫苗、霍乱疫苗的标准化生产难题,没有真空干燥设备,就用最原始的方法烘干提纯。 没有稳定水电,就白天采集样本、晚上钻研数据,他的白大褂上沾满霉菌孢子,头发被煤油灯熏得发黄,却从未喊过一句累。 有人说,汤飞凡没有造青霉素,可他造的疫苗,拯救了数百万军民的生命;有人说,他们的方法太简陋,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份“不信邪、不服输”的硬骨头,就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底气。 无论是樊庆笙团队研制青霉素,还是汤飞凡团队深耕疫苗,他们都是战火中的逆行者。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坚守的行动;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只有一颗滚烫的爱国心。 他们用最朴素的坚守,在乱世中凿出了一条生命通道,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为国担当”。[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