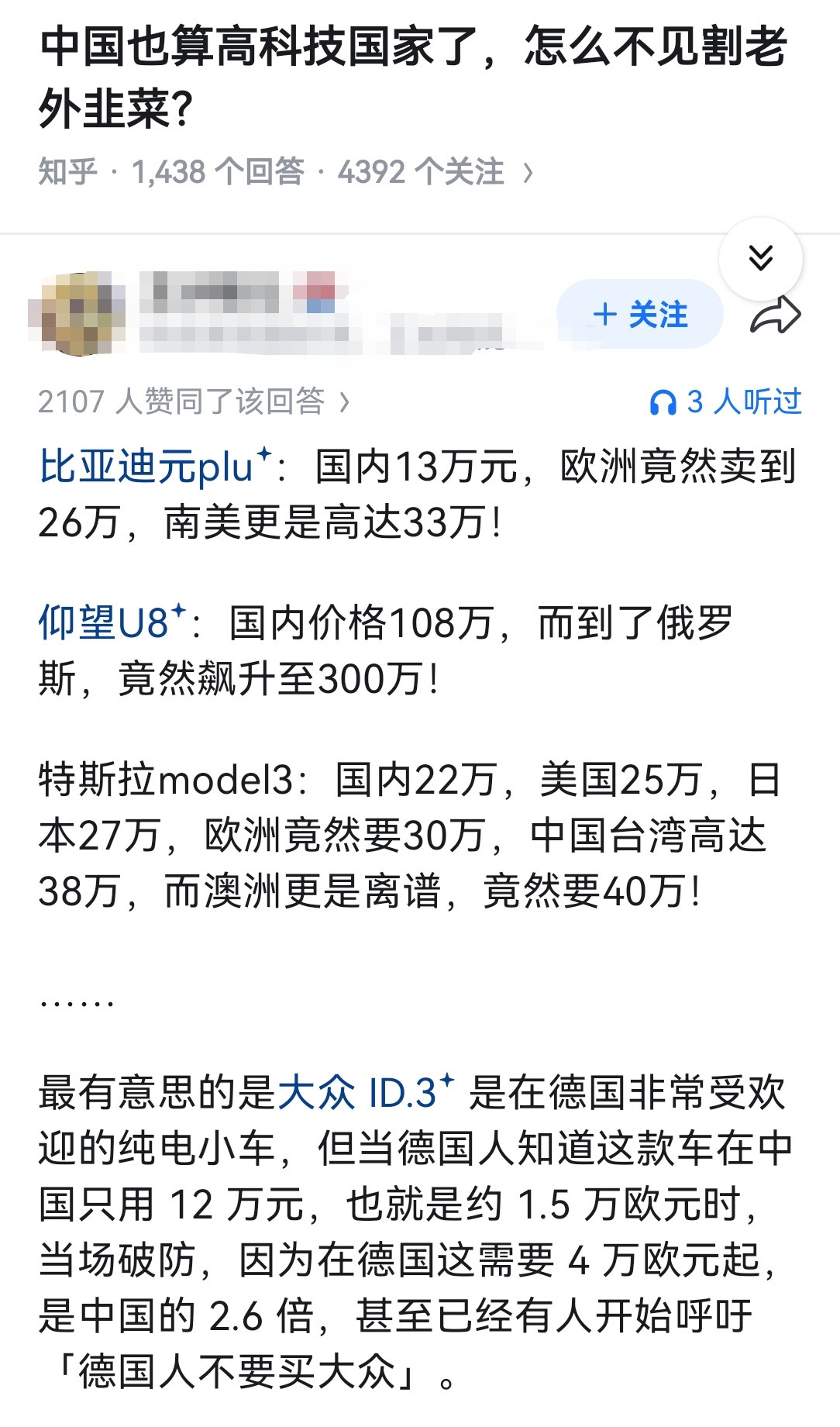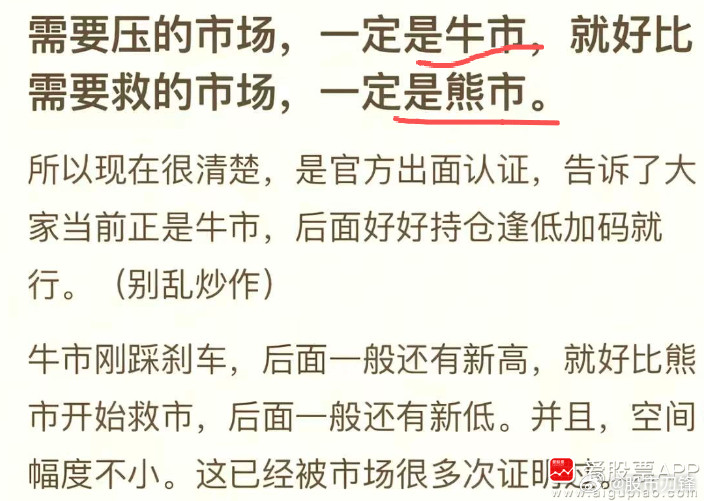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99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里,气氛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时年71岁的褚时健站在被告席上,身形已有些佝偻,但眼神依然清亮。 在做最后陈述时,他的声音平稳而清晰: “说我收了三千多万贿赂,这个我不认,我没拿过那些钱。但说我通过不规范方式拿了四百多万,这个我认。” 这番话,为一个时代的传奇故事,画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句号。 褚时健的人生是从云南玉溪的田间地头开始的。 1928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少年丧父,早早扛起了家庭重担。 他酿过酒,为了多出几斤酒,能守着酒甑琢磨好几天; 他也捕过鱼,熟悉澜沧江畔每个回水湾。 这些经历磨砺出他务实、肯干的性格。 后来他参加革命队伍,在战火中成长,锻炼出果敢的决断力。 这些早年的烙印,都为他日后执掌企业埋下了伏笔。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9年。 当时已年过半百的褚时健,被派到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当厂长。 摆在他面前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设备老旧,产品滞销,工人士气低落。 但这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汉子没有退缩。 他力排众议,咬牙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他更知道好烟叶是根本,于是卷起裤腿就往烟田里跑,和烟农同吃同住,研究怎么种出好烟叶。 几年时间,在他的铁腕治理和精心经营下,“红塔山”异军突起,从云南走向全国。 玉溪卷烟厂也脱胎换骨,成长为红塔集团,一度贡献了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褚时健本人,也从默默无闻的地方干部,变成了举国闻名的“烟草大王”。 然而,巅峰往往与悬崖相伴。 1995年秋天,一封从郑州寄出的举报信,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信中实名举报有烟贩通过贿赂褚时健家人获取紧俏香烟批文,获利惊人。 这封信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组迅速进驻云南。 更具体的案情也随之曝光: 褚时健曾与两位核心下属商议,将三百多万美元账外资金私分,并通过新加坡商人账户操作。 其中他个人名下就有一百七十余万美元。 虽然这笔钱尚未实际转入个人账户,但性质已然严重。 在调查中,褚时健还主动交代了一件事: 几位香港商人曾到他家中,见他生活简朴,便以朋友名义共同赠予他四百多万元人民币。 他认为自己未曾为这些人谋利,便作为馈赠收下。 这笔款项最终被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1998年末,案件公开审理,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 法庭上,辩护律师马军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褚时健执掌企业十七年,创造利税超千亿,其个人全部合法收入仅八十万元,这合理吗? 国企负责人的价值该如何体现? 这番话触动了时代神经,引发了关于贡献与回报、制度与人性的大讨论。 法律给出了最终答案。 法院认定褚时健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宣判后,他没有上诉。 这位古稀老人开始了铁窗生涯。 在监狱里,他被安排管理图书室。 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时常有人悄悄留下些钱物,他都随手放在书架上。 2002年,因表现良好且健康恶化,他被批准保外就医。 出狱后,褚时健没有选择安逸的晚年。 74岁高龄的他,在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山,开始种橙子。 他吃住在山上,像年轻创业者一样从头学起,将工业管理的精细用于农业生产。 十年后,“褚橙”横空出世,因品质优良和他个人的传奇经历,被称为“励志橙”,风靡全国。 他的人生,在跌入谷底后,又一次攀上了令人瞩目的高峰。 褚时健的一生,犹如一部浓缩的时代史诗。 他的成功,是改革开放初期敢闯敢干精神的写照; 他的坠落,暴露了转型时期制度建设的滞后与缺失; 他的重生,则展现了个人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他的故事早已超越个案,成为一代人反思制度、人性与时代的复杂标本,留给后世长久的思索。 主要信源:(东南卫视——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