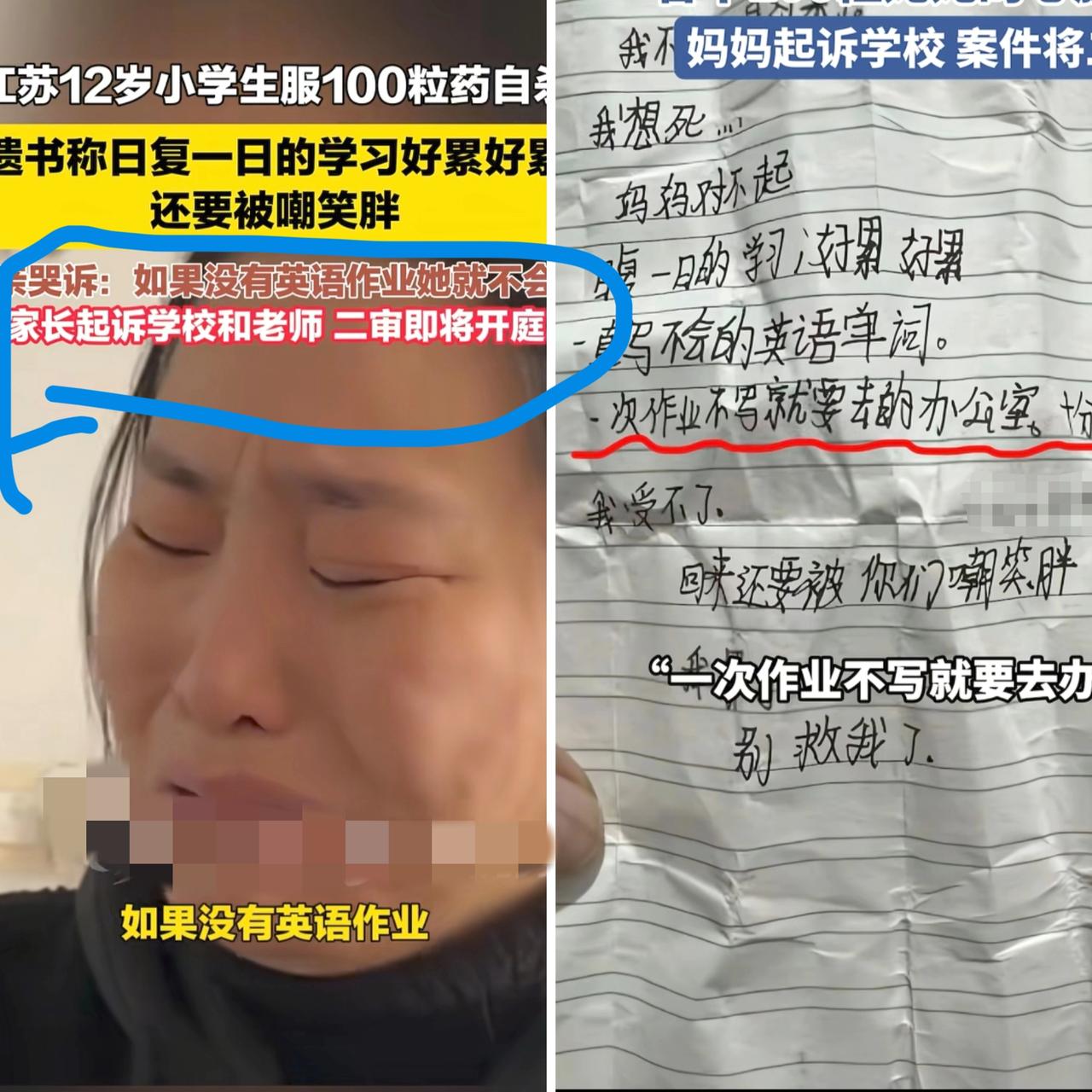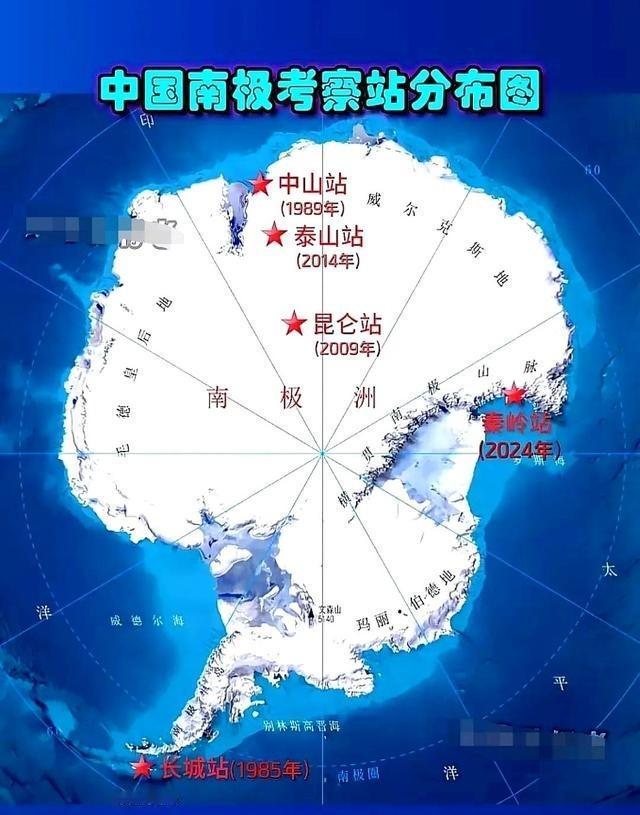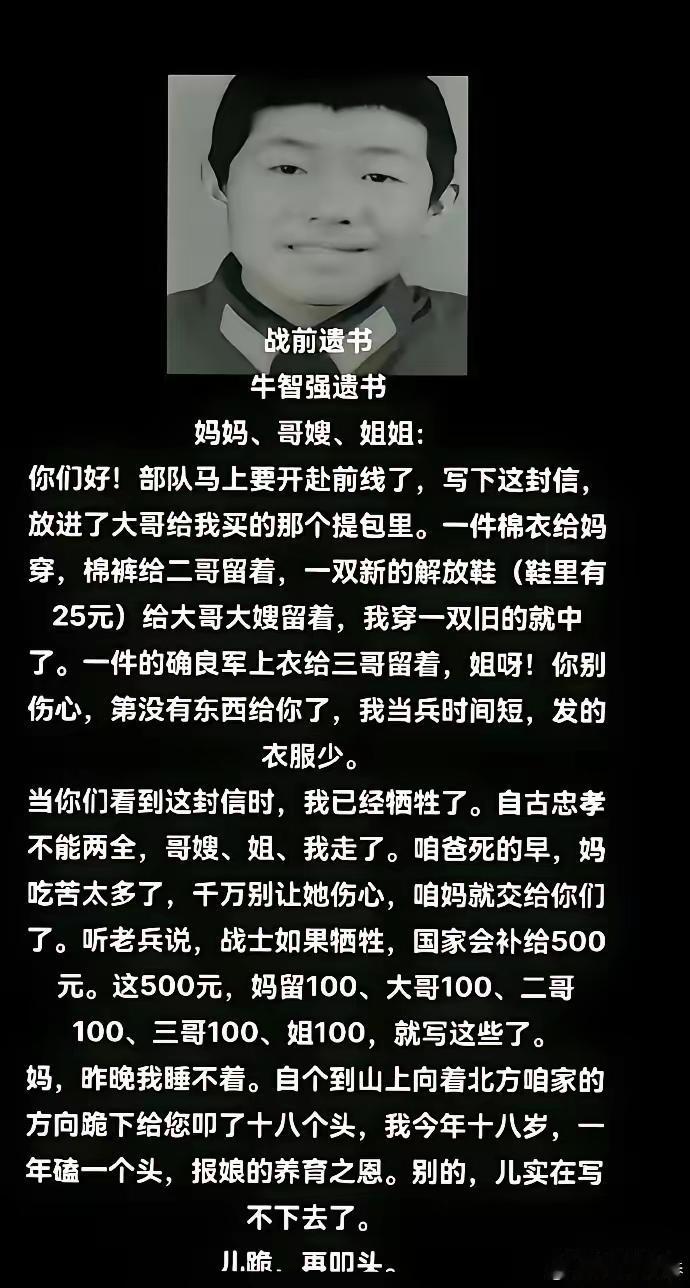八七年的夏天在外婆家窗前,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拿到了镇上中学的语文教师分配通知,彼时我二十岁,衣角还沾着院子里栀子花的香气,心里既雀跃又忐忑,想着要去陌生的镇上站讲台,要面对一群素未谋面的学生,总觉得前路像村口那条蜿蜒的土路,看不清却又满是期待,后来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再翻出这张照片时,才发现年少时的那份青涩与勇敢,早已被岁月酿成了温暖的回忆,而当初那条看似漫长的从教路,也在粉笔灰与读书声里,走到了鬓角染霜的年岁。 外婆站在我身后,手里捏着刚晒干的豆角,看见我攥着通知红了眼眶,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转身进了厨房,端出一碗凉甜的绿豆汤。她知道我打小就恋家,初中住校时还偷偷哭鼻子,现在要去十几里外的镇上,路不好走,得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报到那天,天刚蒙蒙亮,我推着家里那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外婆缝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教案本、一沓粉笔,还有两个煮鸡蛋。镇上的中学比我想象的破,院墙是夯土砌的,校门口的歪脖子槐树下,挂着一块掉漆的木牌子,写着学校的名字。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学校缺语文老师,孩子们底子薄,你得多费心。我点点头,手心全是汗,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份“费心”,一费就是半辈子。 第一节课我教的是初一(2)班,四十多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课桌是长条的,桌面坑坑洼洼,刻满了歪歪扭扭的字。上课铃响的时候,我站在门口,腿肚子都在抖,原本背得滚瓜烂熟的开场白,到了嘴边全忘了。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后排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突然站起来喊,老师你别紧张,我们都很乖。全班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紧张感一下子散了大半。那节课我讲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讲到覆盆子的酸甜,孩子们的眼睛都亮了,有几个孩子偷偷说,他们放学也去山里摘野果。那时候我才明白,课本里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符号,是能和孩子们的生活勾连起来的桥。 日子一天天过,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家校,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冬天最难熬,路面结冰,车轱辘打滑,有一次我摔在路边的沟里,教案本湿了大半,膝盖磕得青紫,咬着牙爬起来,还是一瘸一拐地去了学校。孩子们看见我的狼狈样,下课的时候,偷偷往我办公桌抽屉里塞了冻疮膏,还有个小姑娘,把自己织的手套递给我,手套针脚歪歪扭扭,却暖得我心窝发烫。那时候学校的工资不高,有时候连粉笔都得省着用,一根粉笔要掰成两段,写完黑板的正反面。我舍不得让孩子们抄笔记抄得辛苦,就把重点内容工工整整写在油印纸上,熬夜刻蜡板,油墨沾得满手都是,洗都洗不掉。有家长看我实在不容易,送了自家种的红薯和玉米,我推辞不掉,就给孩子们煮了红薯粥,全班围在一起喝,甜香飘满了整个教室。 三十多年里,我见过太多让人心疼又欣慰的孩子。有个叫王小宇的男孩,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奶奶过,性格孤僻,上课总趴着睡觉。我知道他不是懒,是晚上要帮奶奶喂猪,没睡好。我开始放学后留他补课,给他带早饭,慢慢的,他愿意跟我说话了,作文也写得越来越有灵气。后来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临走前给我鞠了一躬,说老师,我以后也要当老师。这句话,我记到现在。还有个女孩,家里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她哭着跑到学校找我,我骑着自行车去她家讲道理,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让她爹妈松了口。现在那个女孩在城里做医生,每年过年都会回来看我,给我带好多东西。 这些年,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夯土墙换成了砖墙,长条桌变成了单人课桌,多媒体设备搬进了教室,粉笔也不再需要省着用。我也从那个青涩的二十岁姑娘,变成了学生口中的“张老师奶奶”。有时候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会突然想起八七年的那个夏天,外婆窗前的栀子花,还有那条蜿蜒的土路。当初的忐忑,早就变成了沉甸甸的责任和欢喜。我总跟学生说,读书不是为了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来,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看到山外面的世界。 教书育人,从来都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粉笔灰里的岁岁年年,是看着一棵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欣慰。那些曾经的青涩与勇敢,那些藏在教案本里的汗水与温暖,都成了岁月馈赠的礼物,在鬓角的霜花里,闪闪发亮。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