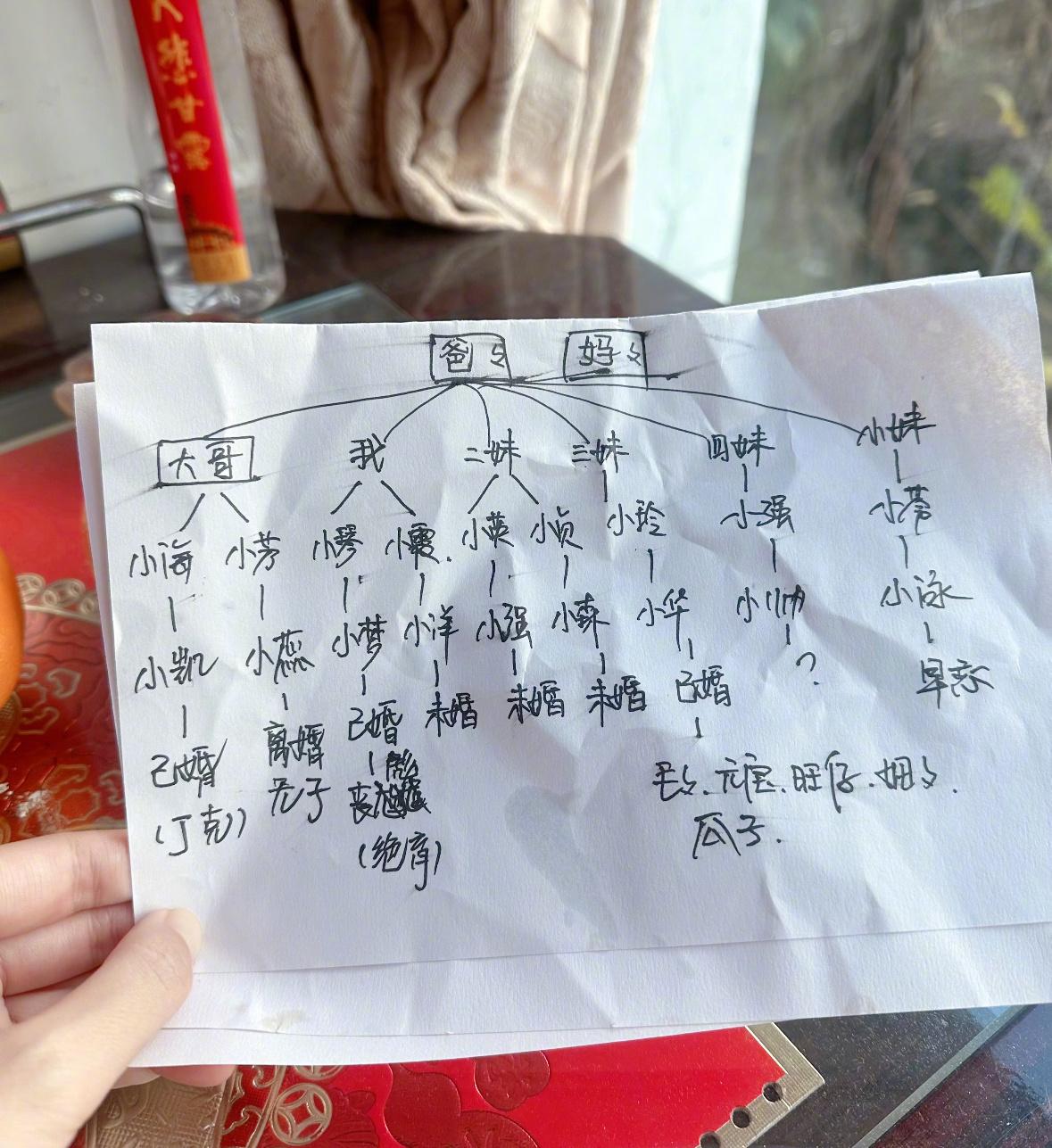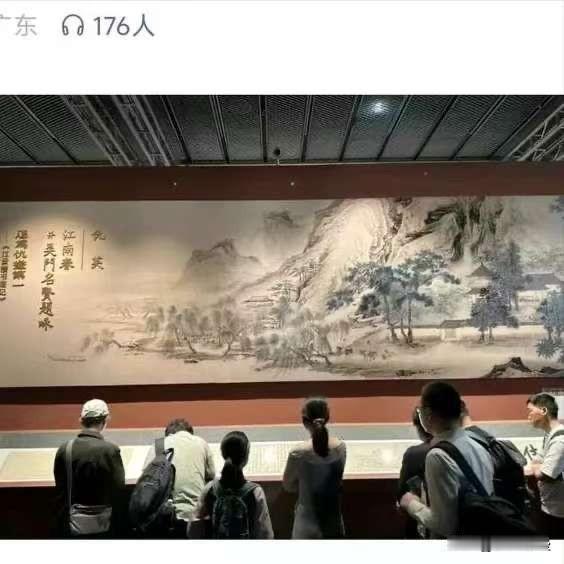1904年,通房丫李氏正站着侍奉丈夫与正妻,突然,管家进来喊了一句:“中了!”李氏手一抖,碗筷掉在了地上,大房扬手就要打她。谁知,丈夫却说:“这24年,你辛苦了!” 光绪三十年腊月,广州两广总督府饭厅。 通房丫鬟李氏手一抖,青瓷碗砸在金砖地上迸裂成八瓣。 热腾腾的白米饭混着菜汤漫开,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煞白的脸。 正房陈氏扬手欲打,门外忽炸开管家嘶吼:“三少爷谭延闿高中会元!头名!” 同治十年,十岁的李氏被卖进谭府。 因打碎主母心爱花瓶,她被“赔”给总督谭钟麟做通房丫鬟。 这身份比奴婢高半等,比妾室低一头,吃饭永远立在廊柱阴影里,看主人妻妾坐享珍馐。 光绪五年,李氏小腹微隆。 府里婆子嚼舌根:“九年没动静,铁树开花了?” 谭钟麟听闻只冷冷丢下一句“别碍眼”,继续搂着新纳的姨娘饮酒。 次年寒冬难产,稳婆剪断脐带时,谭钟麟在隔壁书房酣睡,只嘟囔了句“吵死了”。 而活下来的男婴取名谭延闿。 李氏得了妾室名分,却仍是府里最卑贱的摆设。 每日晨昏定省,她得跪着给正房捶腿。 宴客时她捧壶斟酒,酒液溅出半滴便遭呵斥。 儿子懂事早,见她站着吃饭便拉她坐下,总被她推开:“姨娘坐不得,祖宗规矩比天大。” 谭延闿在柴房识字时,李氏正跪着擦拭地砖缝。 她把米汤省给孩子补脑,自己啃着馊饭看儿子背书。 某夜谭延闿高烧呓语,她冒雪跑遍西关药铺,当掉陪嫁银镯换来犀角粉。 “娘,我将来坐八抬大轿回来,接您堂堂正正吃饭。” 少年郎的誓言混着药气飘进李氏耳朵。 她听后抹把泪,把谭钟麟赏的云片糕塞进儿子书包,而那是她攒了三个月的体己。 光绪三十年的春闱放榜,谭延闿以会试头名震动朝野。 报喜的快马冲进府门时,李氏正给陈氏染指甲。 饭厅死寂被瓷器碎裂声刺破。 李氏盯着满地狼藉,陈氏的巴掌悬在半空。 管家连滚带爬冲进来高喊“三少爷中举”,谭钟麟的象牙箸“当啷”掉在鱼脍盘里。 总督猛地起身,官袍带翻酒盏。 他死死盯住抖如筛糠的李氏,突然大步跨过满地碎瓷,一把拽起她枯瘦的手腕:“添副碗筷!李氏,坐下吃!” 满堂倒吸冷气。 陈氏的护甲掐进掌心,丫鬟们缩着脖子偷瞄。 李氏被按在黄花梨交椅上,臀下硬木硌得生疼。 她舀起半勺饭,热气熏得眼眶滚烫,这是她嫁入谭府二十四年来,第一次坐着吃饭。 十二年的光阴流转。 1916年上海法租界寓所,李氏咳出的血染红绣枕。 在弥留之际她拉着谭延闿的手:“娘这辈子……值了。” 谭延闿时任湖南督军,扶灵回乡时却吃了闭门羹。 谭氏族老堵住祠堂大门:“妾室棺椁走侧门,祖宗规矩动不得!” 人群骚动中,谭延闿突然扯开军帽。 他翻身跃上楠木棺椁,直挺挺躺倒,双眼赤红如炬:“我谭延闿今日已死!抬我出殡!” 沉重的朱漆大门缓缓开启。 阳光穿透祠堂天井,照亮棺盖上躺着的三军统帅。 族老们抖如秋风落叶,谁敢拦湖南督军的“灵柩”? 而李氏最终葬入谭家祖坟正穴。 墓碑刻着“一品夫人李氏”,那是谭延闿用北洋政府勋章换来的名分。 后世翻开《清史稿》,只见谭延闿“历任都督、国民政府主席”的履历。 可鲜有人知光绪三十年那碗热饭的温度,更不知民国五年棺木上的呐喊如何震碎千年礼教桎梏。 广州博物馆现存一方褪色帕子,是李氏跪擦地砖时用过的。 绢角绣着歪斜的“忍”字,针脚里藏着三十三载卑微。 解说员总爱指着它感慨:“瞧瞧,这才是真正的‘母凭子贵’。” 如今谭氏宗祠游人如织。导游指着正厅太师椅讲解:“从前妾室只能站着伺候,直到1904年……” 游客们想象着那个冬日场景,碎瓷纷飞中,总督老爷拽着通房丫鬟的手腕,吼出石破天惊的命令。 而祠堂角落,一块光绪年间的地砖微微凸起,那是李氏跪了上万次的印记。 历史的烟尘散尽,唯有那碗热饭的温度穿透时空。 原来所谓尊严,不过是有人肯为你弯腰拾起破碎的碗,再亲手捧上一副干净的筷子。 主要信源:(华声在线——历史上的今天丨1880年,“文甘草”谭延闿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