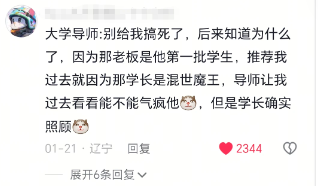我村有个人,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去了美国,成了美国人。他家有父母哥嫂,开始那几年,父母哥嫂,自豪的不得了,到外宣传,逢人就讲,我儿去了美国。我弟成了美国人。 村口老槐树的影子刚爬到石磨盘上,我婶就端着板凳往树下挪,手里蒲扇摇得比平时快三分。 我叔蹲在磨盘边,摸出烟袋却没点,眼睛望着村东头那条土路——那是三十年前,他儿子背着帆布包去县城上高中的路。 “俺家老三,哈工大的研究生!”婶子的声音裹着风,吹到路过的二奶奶耳朵里,“现在啊,在美国!成美国人了!” 哥嫂从地里回来,扁担还没放下,就有人凑过来问:“大强,你弟真成美国人啦?” 我哥把扁担往墙上一靠,嘿嘿笑,露出两排被太阳晒得发黄的牙:“可不是咋的,前儿来信说,入籍手续都办利索了,以后就是美国公民!” 那几年,我婶的蒲扇上总沾着点炒瓜子的香——谁家来串门,她就抓一把塞人手里,话匣子跟着打开:“他小时候就聪明,五岁能背乘法表,十岁那年夏天,趴在炕桌上算题,汗珠子滴在草稿纸上,洇开一小片蓝。” 我叔终于把烟点上,猛吸一口,烟圈慢悠悠飘向天上:“那会儿穷,供他读书不易,他哥辍学打工,他嫂子把陪嫁的银镯子都当了——现在好了,熬出头了!” 赶集的日子最热闹,我哥推着独轮车卖白菜,旁边总围一圈人:“大强,美国是啥样?高楼比咱村的树还密?” 我哥停下手里的秤杆,想了想说:“听老三说,街上跑的车都没声儿,晚上跟白天一样亮——他还寄了照片,穿西装打领带,站在一个大铁架子下头,说是自由女神像。” 有回村西头的老光棍打趣:“成了美国人,还认咱这穷爹妈不?” 我婶的蒲扇“啪”地拍在腿上,脸一下子红了:“咋不认?上个月还寄钱回来呢!比他哥一年挣得都多!” 可那天晚上,我起夜路过叔婶家,听见婶子小声哭:“他说美国好,可咱村的星星,他小时候最爱数了……” 叔没说话,只把婶子手里的蒲扇接过来,一下一下,扇得比白天轻。 村里人都说老两口是“崇洋”,是炫耀——可谁见过我婶把儿子的奖状一张张裱起来,贴在炕头墙上,每天睡前摸一遍?谁见过我哥把弟弟寄来的信,读给不识字的爹妈听时,声音里带着颤? 那点“自豪”,哪是啥“崇洋”?不过是庄稼人看着自己种的麦子,从青苗长到金黄,打了满仓的粮;是爹妈想起孩子啃着干馍馍在煤油灯下读书的夜,终于有了个能说出口的“结果”。 后来,信渐渐少了,电话也多是哥嫂打过去,说不上三句就挂——“时差,他那边是半夜。”叔婶总这样跟人解释。 但老槐树底下,婶子的蒲扇还是摇着,只是话少了,偶尔有人再问起“美国的儿子”,她就指指天上的云:“飘得远了,就由着他飘吧。” 秋风起时,老槐树叶落了一地,我婶捡了片最大的,夹在那本泛黄的相册里——相册第一页,是她儿子十岁那年的照片,穿着打补丁的褂子,站在老槐树下,笑得露出豁牙。 现在,那豁牙的笑,和纽约街景里的西装革履,隔着一页薄薄的槐树叶,在相册里挨得紧紧的。 你说,他们到底在自豪啥? 或许不是“美国人”这三个字,是那个从泥地里爬起来,一步步走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的孩子——他过得好,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实在的体面。
我村有个人,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去了美国,成了美国人。他家有父母哥嫂,开始那几年,
卓君直率
2026-01-04 15:42:08
0
阅读: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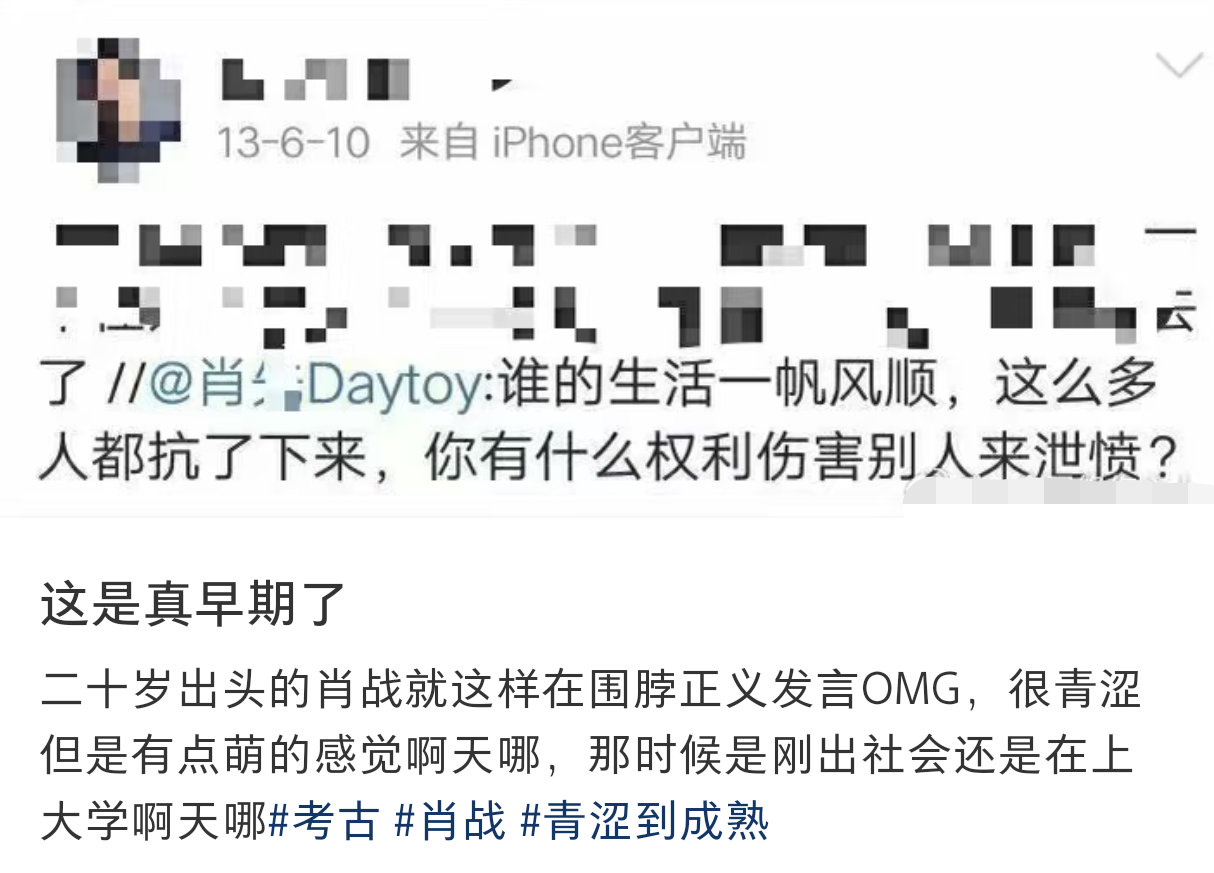
![博士超长延期是指最长6~8年毕业[doge],全日制博士基本学制3-4年,非全日制基](http://image.uczzd.cn/988985541853275658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