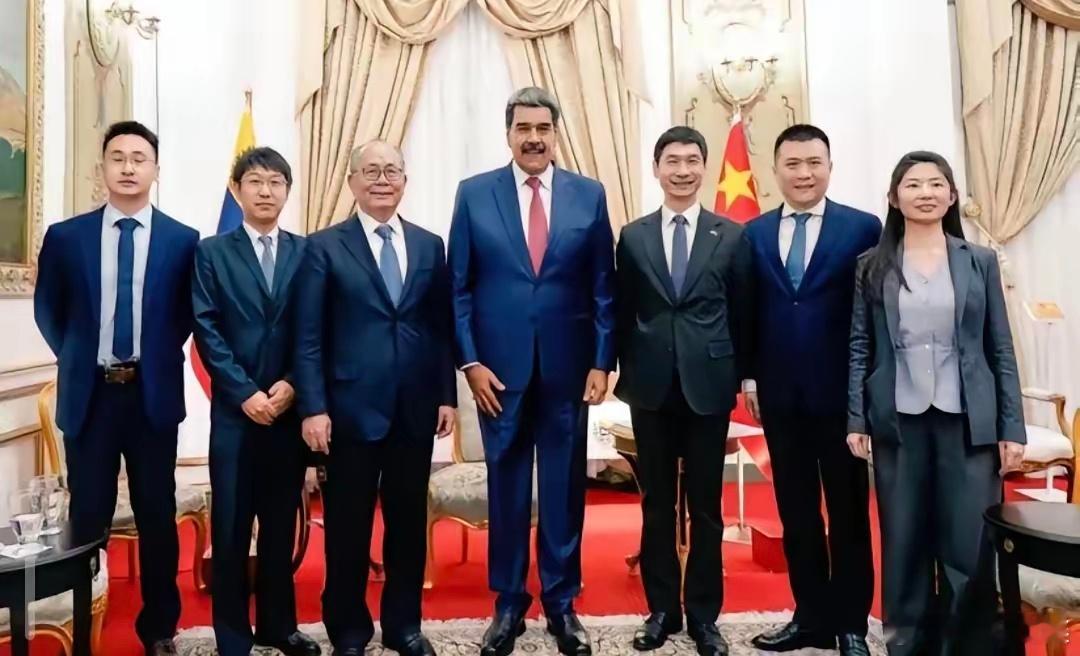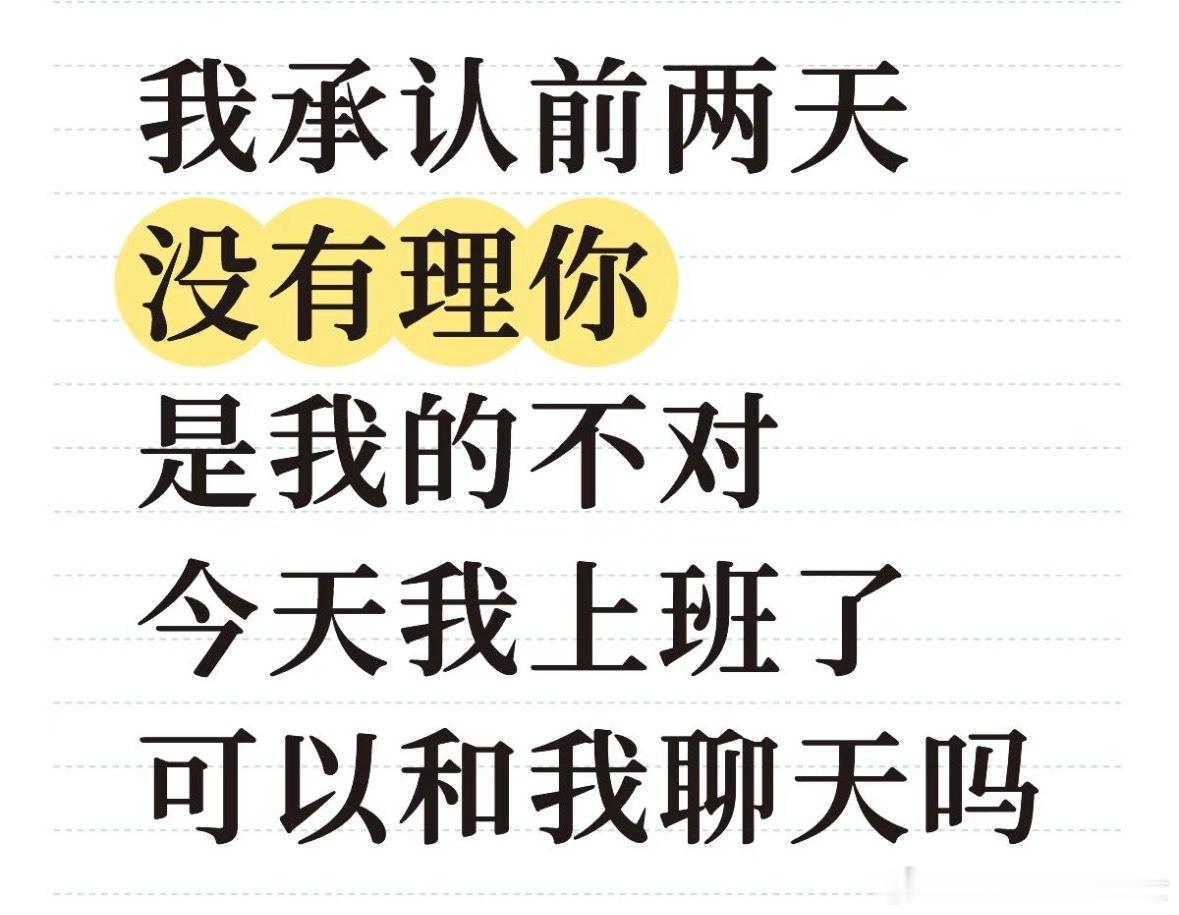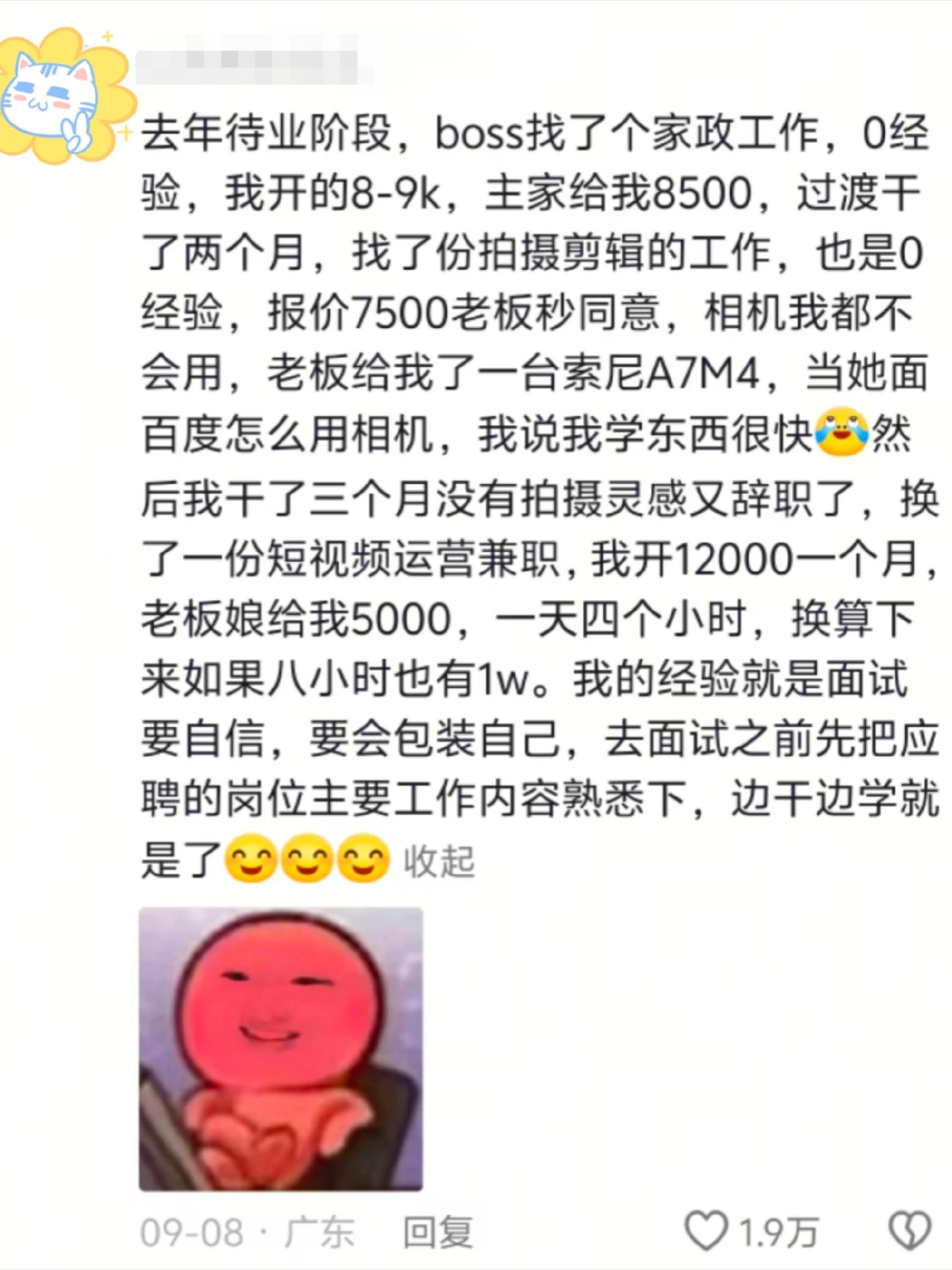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那一沓突然摆在饭桌上的钞票,差点让孙玉芹手发抖。家里一串账单压得她喘不过气,孩子的书本费,欠下的人情债,老家还盼着寄钱。可就算再紧,这个当家人的女人心里也清楚,买一只烤鸭仍算奢侈。 更让她不安的,是这个一年到头见不着几面的丈夫。于敏常常说走就走,一去几个月没有音讯。 搬家时联系不上他,她只好一个人扛着大包小包挪窝。他好不容易回到旧屋,只能对着空房间发呆,最后还是邻居告诉他新址。 到了新家门口,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一脸陌生地打量他。研制氢弹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瘦了一大圈,头发大把脱落,连自己的孩子都几乎认不出来。 胡同里有人冷嘲热讽,猜他是不是犯了事被下放,女儿被同学欺负时,只能红着眼说出一句爸爸是保密的。 走进核研究所大门那天起,他的名字就成了保密条例里的一个代号。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常常消失的背影。 面对妻子的追问,他只能解释说氢弹爆炸是大喜事,国家有底气了,咱们这些老百姓的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这钱是新发的工资。 谁都不知道,在那之前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三十五岁那年春天,他被叫进办公室,从原子核理论的学者一下子转成氢弹攻关的主力。 全国起步几乎是一张白纸,能用的只有几台老旧计算机,一屋算盘和堆成山的空白草稿纸。家里仅有的四百块存款,被他悄悄取出捐给国家买计算纸。 白天在黑板前推公式,深夜围着稿纸算数据,机器空不出时间,就靠几十个人打算盘。国外权威杂志认定必须走氚材料路线,他却死盯着自己算出的数字,坚持氘才是更合适的选择。 这个后来被称作于敏构型的方案,在巨大压力下被推上去,既省下几座化工厂的投入,也让罗布泊那团蘑菇云提前升空。 氢弹成功消息传到北京时,他正在给年轻人上课,只是粉笔在手里微微一抖。那天晚上,他特意绕路去买了一只烤鸭,想给妻子和孩子一个小小的庆祝。饭桌上,孩子们听他讲起金黄酥脆的外皮和喷香的鸭肉,眼睛都亮了。 等孩子们在对烤鸭的幻想中睡去,孙玉芹把账单摊开,说在梦里吃就行,日子不能这么花。她的梦很简单,只盼一家人平安团圆。而于敏心里的梦,比这大得多,是让这个曾经被人卡着脖子的国家有自己的底气。 后来,中子弹的阴影又压下来,他揣着心脏药往大山深处的实验室里钻,头发一茬茬掉,白细胞只剩常人的一部分。 家里搬来搬去,孙玉芹始终咬牙撑着这个家。一次他突然回家,门外孩子愣住了,她只冷冷说了句还活着呢,他接一句活着回来了,把所有委屈都咽了回去。 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在颁奖台上认出这位穿旧中山装、走路都有些踉跄的老人。而在他留下的一叠发黄稿纸旁,压着的只是一行小字和一段普通人的心思。 那只反复被提起却很少真正吃到嘴里的烤鸭,是一家人的盼头,也是他用一生去兑现的那个更大的梦想的温暖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