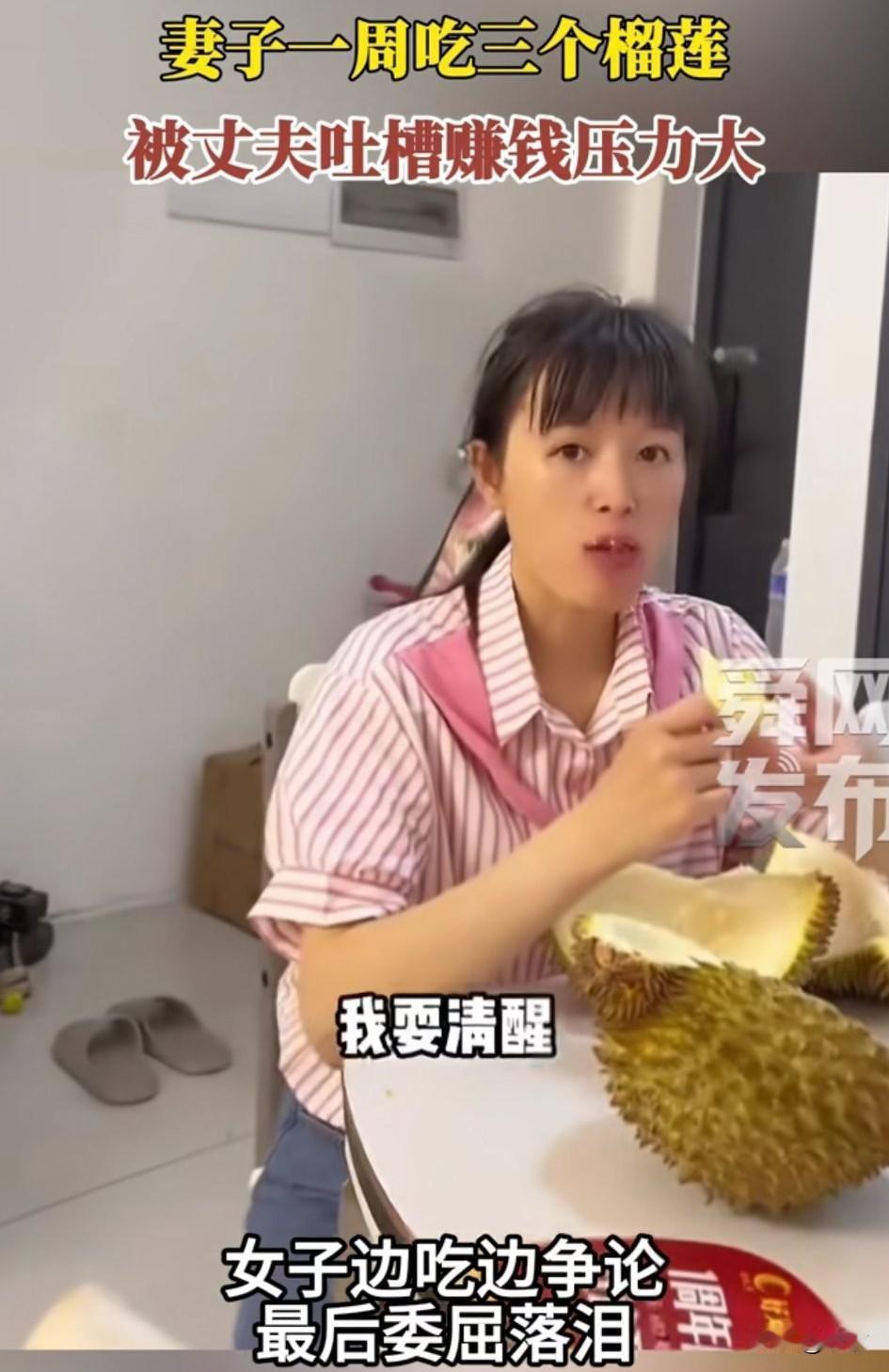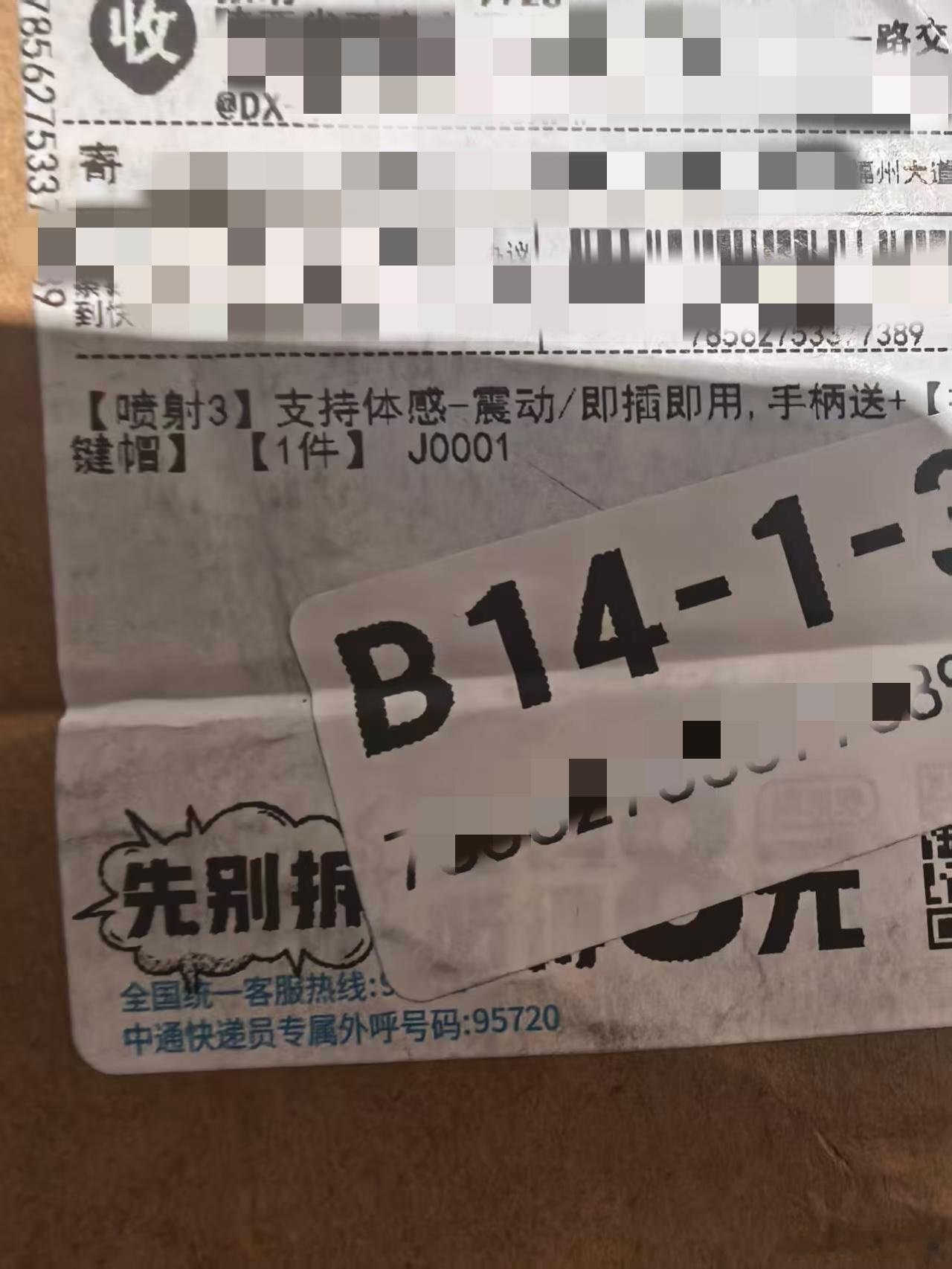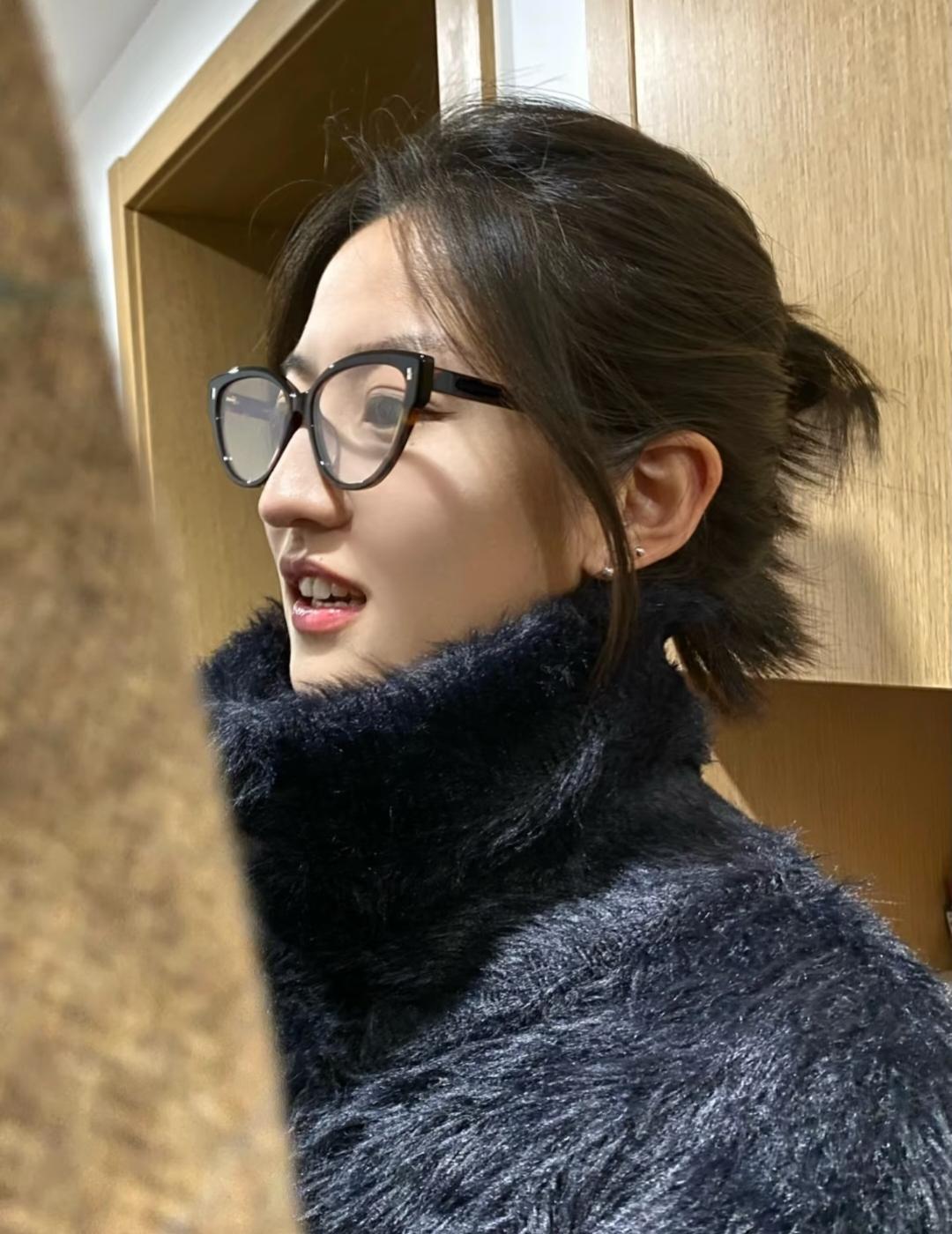邻居那年家暴把妻子打死了,送葬那天家暴男头上戴着孝去迎接妻子的娘家人,妻子的舅舅把家暴男打了几巴掌骂了一顿。那几巴掌响得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家暴男没躲,只是低着头,孝布从头上滑下来,露出半边青黄的胡茬,像块没长好的烂木头。 我至今记得那个女人,姓刘,我们都叫她刘姐。她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楼道,碰见谁都笑着打招呼,声音细细软软的。有次我家孩子发烧,她半夜敲我家门,塞给我一把艾草,说煮水擦身子能退烧,我家那口子小时候就这么弄好的,说这话时,她眼角的淤青还没消。 楼道里总飘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是刘姐的味道。 她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天不亮就拿着扫帚往下走,木柄磨得发亮,扫过台阶时沙沙响,像春蚕啃桑叶。 碰见谁都笑,声音细细软软的,“上班去啊?”“孩子放学啦?”尾音带点怯生生的颤,像被风揉过的棉线。 有次我家孩子半夜发烧,她突然敲门,门缝里递进来一把艾草,叶子上还沾着露水,“煮水擦身子,我家那口子小时候就这么好的。” 说这话时,她左边眼角青了一块,像没洗干净的墨渍,我盯着看,她慌忙别过脸,围裙带子滑下来,露出手腕上几道红印子,像勒紧的绳。 后来才知道,那些印子是她丈夫攥出来的;后来又知道,那天她递艾草时,刚被推搡到墙上,后脑勺撞出个包。 送葬那天是阴天,楼道里的皂角香变成了烧纸的焦糊味。 她丈夫戴着孝布站在单元门口,低着头,孝布滑下来,露出半边青黄的胡茬,像块在雨里泡烂的木头。 她舅舅从车上下来,一眼看见他,上去就是几巴掌——啪!啪!啪!响得楼道声控灯都亮了,惨白的光打在孝布上,晃得人眼疼。 “你也配戴这个?”舅舅的吼声带着哭腔,“她给你洗了十年衣服,扫了十年地,你就是这么还她的?” 他没躲,也没说话,就那么低着头,孝布全滑到脖子上,露出的胡茬里沾着几根白线头,不知道是孝布上的,还是她以前缝补衣服时蹭上的。 街坊都站在自家门口看,没人说话,只有风吹着纸钱,打着旋往楼上飘,像她没说完的话。 我想起她递艾草那天,手一直在抖,我问“没事吧?”她笑了笑,“没事没事,老毛病了。” 老毛病?是他摔东西的毛病,还是她忍着疼不敢喊的毛病? 我们当时要是多问一句呢?要是拉住她手腕说“去我家坐会儿”呢? 她总说“没事”,或许是怕麻烦别人,或许是怕他知道了更生气,或许是……她根本不知道“有事”可以找谁。 直到那天下午,楼道里突然没了扫地声,只有沉闷的撞墙声,接着是她短促的尖叫,然后什么声音都没了——像被掐断的琴弦,余震都藏在墙缝里。 舅舅的巴掌没停,打得他嘴角出血,他还是低着头,血滴在水泥地上,红得刺眼,像她生前最喜欢的那盆凤仙花,被踩烂了根。 后来街坊说,他那天戴的孝布,还是她生前给他缝的,针脚密得像鱼鳞,她总说“孝布得结实点,不然不吉利”。 多讽刺啊,她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连最后给他戴的孝布,都缝得那么仔细。 现在楼道里没人扫了,台阶上积着灰,有时候半夜起夜,我总觉得听见沙沙声,开门看,只有风卷着落叶滚过去,像谁没说完的话。 刘姐的蓝布围裙,后来被她娘家人拿走了,说要烧给她,我却总看见那抹蓝在眼前飘,洗得发白,却比楼道里任何灯都亮。 要是再遇见谁眼角带伤,笑着说“没事”,别只点点头走开;要是听见邻居家有东西摔碎的声音,别劝自己“清官难断家务事”。 有些“没事”,是在等一句“有事跟我说”;有些沉默,会变成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皂角香早就散了,艾草的味道却总在记忆里飘,苦丝丝的,像她没来得及流的泪,也像我们没说出口的愧疚。
上夜班回来的丈夫,看见妻子没有做饭,反而在大口大口的吃榴莲,丈夫气不打一处
【33评论】【1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