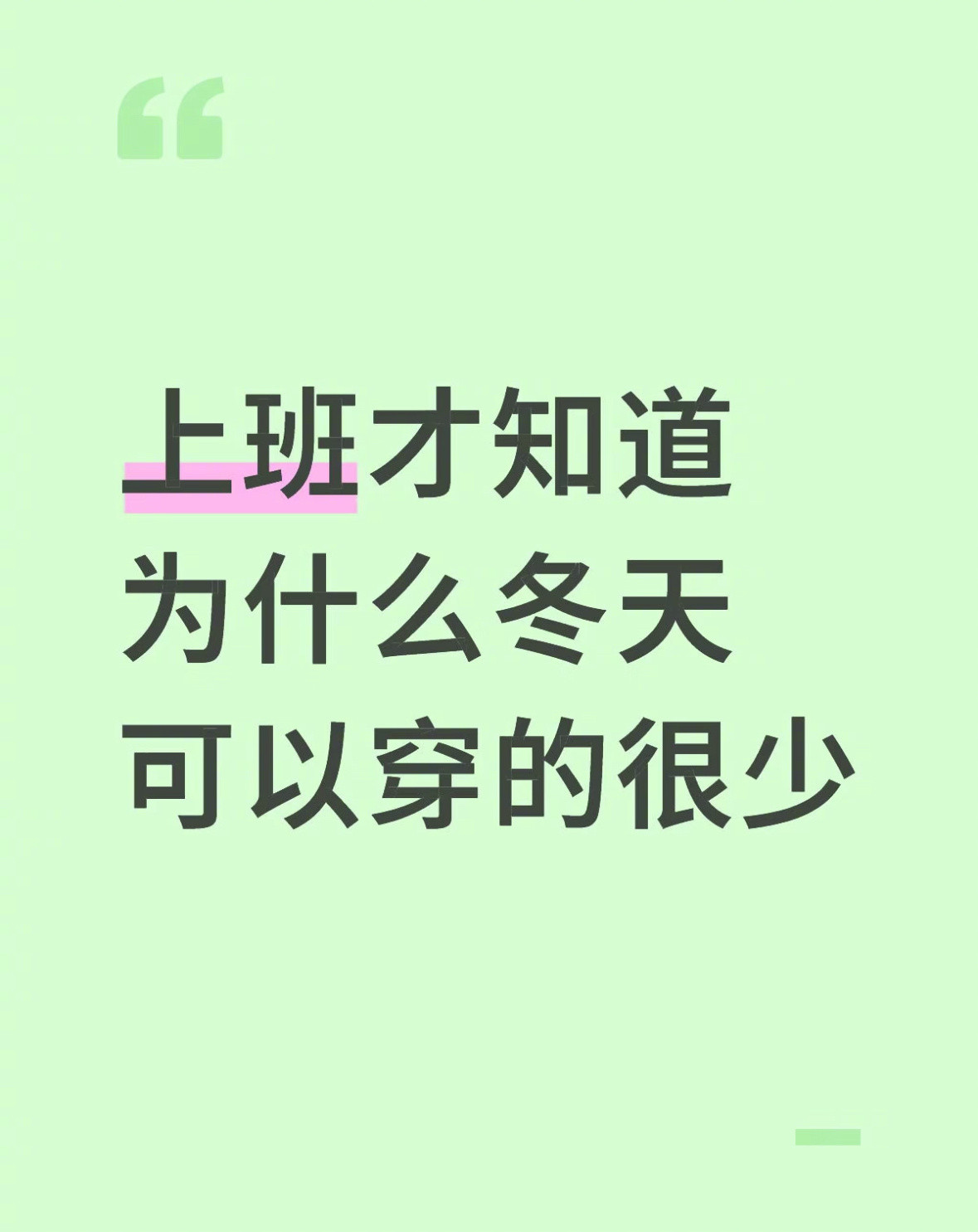浴室里的水声哗啦作响时,我正坐在沙发上叠刚收回来的衣服。棉质T恤蹭过指尖的触感很暖,可后背总像敷着块冰——我知道再过十分钟,那扇磨砂玻璃门会冒出白汽,老公周明裹着浴巾出来,发梢滴着水往我这边走。他会先从背后圈住我的腰,下巴搁在我肩窝,热气混着沐浴露的柠檬香漫过来:“今天累不累?” 浴室里的水声哗啦作响时,我正坐在沙发上叠刚收回来的衣服。棉质T恤蹭过指尖的触感很暖,可后背总像敷着块冰——不是真的冷,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慌,像冬天没关严的窗缝,冷风丝丝往里钻。 墙上的石英钟分针刚跳过数字7,水声突然停了。我数着秒,1,2,3,磨砂玻璃门果然开始冒白汽,像刚掀开的蒸笼。周明裹着浴巾出来时,发梢的水珠正滴在地板上,砸出小小的湿痕,一步一步往我这边挪。 他还是老样子,先从背后圈住我的腰,掌心带着水汽贴在我小腹上,烫得我指尖一颤。下巴搁在我肩窝时,热气混着沐浴露的柠檬香漫过来,比空调风还暖:“今天累不累?” 我没回头,手里的袜子差点叠歪。“还好,”声音闷在棉质衣堆里,“就是晒衣服时够不着晾衣杆,踮了好几次脚。” 他圈着我的手臂紧了紧,手指无意识摩挲我腰侧的旧疤痕——那是去年切菜划的,当时他也是这样从背后抱着我,非要替我贴创可贴,说“你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可现在,他的手指在疤痕上顿了顿,就移开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连他的疲惫都要猜了?上周三他加班到十一点,我打了三个电话都没人接,后来他回微信说“在开会”,可我凌晨起夜,看见他手机屏幕亮着,是和同事的聊天记录,最后一句是“方案还得改,你先睡”。我当时没吭声,只是第二天早上他喝咖啡时,多往他杯里加了半勺糖——他最近总说咖啡太苦。 “下周项目答辩完,我们去吃巷尾那家火锅吧?”他突然开口,下巴蹭得我颈窝发痒,“你上次说想吃毛肚,我记着呢。” 我手里的T恤“啪嗒”掉在沙发上。棉质布料摊开,像一片被晒软的云。他弯腰去捡,我看见他左手虎口有块淡红的印子,是握笔太久磨的。原来他说的“开会”,是在办公室改了一晚上方案。 “周明,”我终于转过身,他还维持着捡衣服的姿势,浴巾松松垮垮挂在腰上,发梢的水珠滴在我手背上,凉丝丝的,“你上周三,是不是没吃晚饭?” 他愣住了,眼睛里的睡意像被戳破的泡泡,慢慢散了。过了会儿,他低低地“嗯”了一声,伸手把我头发别到耳后:“怕你担心,没敢说。” 我突然想起刚结婚那年,他发烧到39度,还硬撑着给我做番茄鸡蛋面,说“你胃不好,外面的饭油大”。那时他眼里的红血丝,和现在虎口的印子,好像没什么不一样。 “那你刚才怎么不问我?”我捏着他的手腕,指腹摩挲他手腕内侧的青筋,“问我累不累的时候,怎么不说说你自己?” 他笑了,有点不好意思,往我怀里钻了钻,像只讨暖的猫:“怕你嫌我烦。” 浴室的白汽还没散完,飘到客厅里,裹着柠檬香,把沙发上的衣服都熏软了。我捡起刚才掉的T恤,重新叠好,这次指尖的暖意顺着胳膊爬上去,一直暖到后背——原来那片冰不是他放的,是我自己忘了给心里的窗关严实。 “火锅要特辣锅底,”我拍了拍他的背,浴巾上的绒毛蹭得我手心发痒,“还要点两份毛肚,你一份我一份,谁也别抢。” 他在我怀里闷闷地笑,下巴搁在我肩上,热气呼在我颈窝里:“好。” 水声早就停了,可我好像还能听见哗啦哗啦的响,不是水管里的水,是心里那点慌,终于顺着刚才的对话,流进了地漏里。
浴室里的水声哗啦作响时,我正坐在沙发上叠刚收回来的衣服。棉质T恤蹭过指尖的触感很
勇敢的风铃说史
2025-12-17 12:21:39
0
阅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