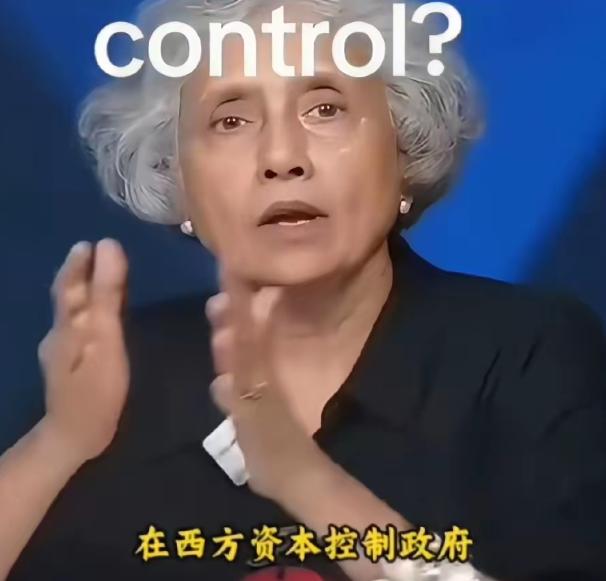外国学者说:“中国和西方本质的不同就是,中国是国家控制资本,西方是资本控制国家!”她接着说,这和市场无关,问题是如何监管市场,如何治理市场?企业是否受到监管?他们在为谁的利益工作? 这不是“计划”与“市场”的对立,而是资本的“时间属性”和“服务对象”出了分歧,中国让资本成为穿越周期的“耐心玩家”,西方则任由资本变成追逐短期暴利的“投机者”,而国家在其中的角色,正是这种差异的根源。 有人可能会以为以为这单纯的是行政指令在推动资本流动,实则是国家通过制度设计,让资本看到长期价值。 浙江的杭台高铁就是最生动的例子,这条连接杭州与台州的线路,民营企业持股超过一半,是国内首条民资控股的高铁。 高铁建设周期长、投资大,民营资本原本避之不及,但政府通过设计“运营收入+缺口补贴”的回报机制,给出34年的合作周期,让资本愿意沉下心来参与基建民生项目。 开通三年来,这条高铁带火了沿线旅游,光是新昌县的过夜游客就涨了近两成,资本赚到合理收益的同时,地方经济也被激活了。 这种模式在战略产业上更明显。芯片产业被“卡脖子”后,中国没有急着逼资本砸钱,而是通过产业基金持续输血,不追求短期回报。 相比之下,美国的芯片法案看似投入几百亿美元,却因为资本的短期算计难以落地。 特朗普政府甚至想把补贴变成股权,要求从英特尔、台积电这些企业手里分一杯羹,企业担心核心利益受损,对技术转移处处设防,法案推行两年多,实际到位的资金还不到计划的一半。 中国的资本愿意陪国家“啃硬骨头”,正是因为国家守住了“长期回报”的底线,而不是让资本在短期博弈中迷失方向。 这种引导绝非“控制”,而是给资本套上“价值锚点”。中国联通的混改早就让人看到了端倪,2017年引入腾讯、阿里等民资股东后,央企的战略资源和民企的市场活力形成了互补,共同做优云计算、网络安全这些新业务。 现在大部分央企都引入了民资股东,市场化运作和战略责任并行不悖,既没丢了国家战略的“根”,又激活了市场竞争的“魂”。 就连中石油、中石化这些能源巨头,也在保障民生供应的同时推进新能源转型,2023年两家企业的新能源投资都同比增长了三成以上,资本在政策引导下找到了公益与盈利的平衡点。 西方资本的逻辑则完全是另一套,从历史深处就带着“短期暴利”的基因。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质上就是资本与国家权力捆绑的产物,政府给它垄断贸易权,它用武力开拓殖民地,股息率一度冲到40%,却把血腥掠夺留给了殖民地人民。 这种“资本借国家之力谋利”的模式延续至今,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中,前副总统切尼曾执掌的哈里伯顿公司,三年内从战争合同中赚了160亿美元,而美国民众只收获了伤亡和债务。 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从来不是现代才有的新鲜事,而是刻在西方资本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这种法则到了当下,变成了资本对国家权力的反向绑架。美国的医药行业最是典型,辉瑞2024年营收超过600亿美元,却靠着游说国会推迟药价谈判,普通民众看一次病的花费能抵得上几个月工资。 金融领域更夸张,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巨头拿着政府救助款继续发奖金,还通过游说放松监管,短短几年就恢复了往日风光。 即便是被寄予厚望的科技产业,也成了资本操控舆论的工具,Meta、谷歌能通过算法左右选举认知,却因为巨额游说资金,让国会的监管法案迟迟无法落地。 国家本应是监管者,却成了资本的“提款机”和“保护伞”。 欧盟曾想硬气一把,累计对谷歌开出超过100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试图遏制科技巨头的扩张,但收效甚微。 企业可以通过转移业务、调整架构规避处罚,而欧盟各国因为资本利益不同,很难形成统一监管合力。 美国更是深陷泥潭,2020年大选花费创下144亿美元的纪录,政客对资本的依赖越来越深,即便知道去工业化会让蓝领失业,也不敢触动资本向金融、科技转移的趋势。 资本把国家机器变成了“逐利工具”,自然没人再为长远发展操心。 两种模式的差异,最终落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国际油价暴涨时,中国的加油站不会随意涨价,“两桶油”哪怕短期亏损也要保障供应;而美国的油价跟着资本炒作波动,炼油企业趁机抬高价格,利润同比翻番。 中国的高铁票价十年不涨,还在不断加密线路;西方很多国家的高铁项目因为资本不愿投入长周期项目,规划了十几年仍未开工。 中国的资本是“跟着国家修路架桥”,西方的资本是“围着政客算钱逐利”,这背后就是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