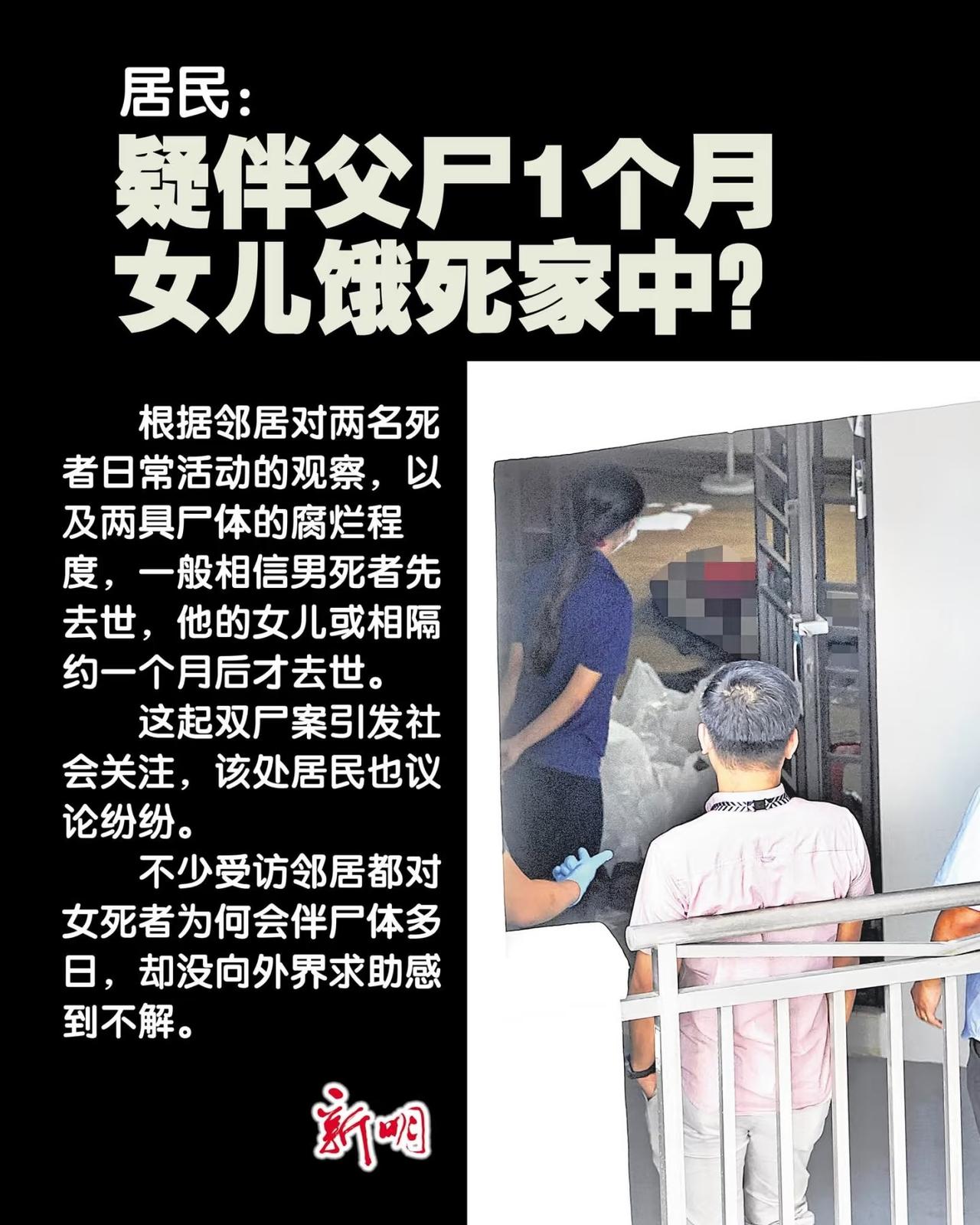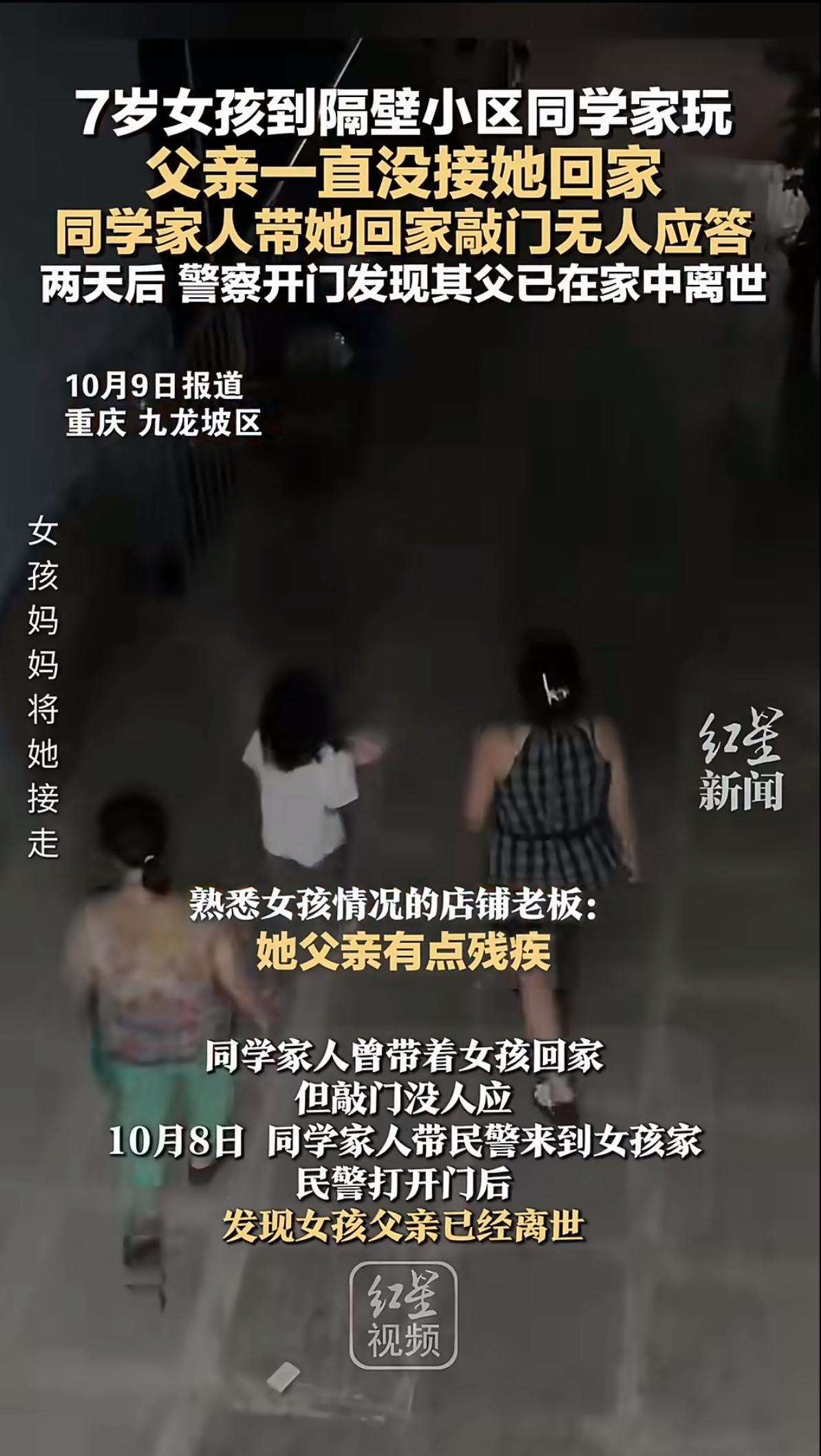大庆油田发现者谢家荣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在睡梦中离世,第二天,妻子吴镜侬在他身边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短短十个字令人泪目。 2024年地质研究所档案室,89岁的谢学锦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展开一张泛黄信纸。 信纸是父亲谢家荣1966年写的,收信人是“大庆油田勘探队”,却没寄出去,末尾“愿祖国多找油”几个字,被泪水洇得模糊。 这封未寄出的信,和谢家荣手绘的松辽盆地构造图、《中国矿床学》手稿放在一起,藏着这位“中国找油先驱”最后的遗憾与坚守。 1978年冬,谢学锦从木箱里翻出这封“找油信”时,手指止不住发抖。 木箱是母亲吴镜侬当年藏在衣柜深处的,里面除了信,还有父亲被批斗时扯破的地质服、用了几十年的罗盘。 信里详细写着塔里木盆地的潜在油区,还画了简易构造图:“此处地层与松辽相似,若条件允许,可优先勘探”。 谢学锦看着信,想起1966年那个夏天——父亲吞安眠药前,曾把木箱钥匙塞给母亲,说“这里面有祖国需要的东西”。 时间倒回1955年,松辽平原的勘探帐篷里。 谢家荣趴在煤油灯下,修改松辽盆地构造图。 苏联专家刚来过,丢下一句“陆相地层出不了大油,别做无用功”,就带着设备离开了。 他却没放弃,把美国产油区的地质资料贴在帐篷壁上,逐页对比:“他们有密西西比河盆地,我们有松花江盆地,凭什么不能有油?” 队员们劝他“别跟专家对着干”,他却扛起钻机,踩着没过膝盖的雪,去实地验证自己的判断。 那天他冻得腿都僵了,却在岩芯样本里发现了油迹,连夜在构造图上标注:“此处有生油迹象,重点钻探!” 1959年9月26日,谢家荣在办公室接到大庆油田的电话。 “谢老!松基三井出油了!工业油流!”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哭腔。 他手里的钢笔“当啷”掉在纸上,赶紧抓起外套往油田赶。 到了钻井平台,看着喷涌的原油,他蹲在地上,摸着滚烫的输油管,眼泪掉了下来——为了这一天,他等了整整四年,被质疑了无数次。 当晚,他在构造图背面写下:“1959.9.26,松基三井出油,陆相生油论得证”,字迹里满是激动。 1964年,谢家荣的书房成了“批判对象存放地”。 有人把他的学术著作堆在地上,说“这些都是反动理论”;有人抢走他的地质标本,骂“研究石头就是不务正业”。 他却偷偷把《中国矿床学》手稿藏在床板下,每天凌晨起床整理。 母亲吴镜侬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别写了,命重要”。 他却摇头:“这手稿里有找油的关键数据,丢了,以后祖国找油就难了。” 有次批斗回来,他嘴角流着血,还坚持补全手稿里缺失的公式,说“差一个数,都可能让勘探走弯路”。 1966年8月23日深夜,谢家荣坐在书桌前写“找油信”。 窗外传来批斗的口号声,他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 信里,他没提自己的遭遇,只详细写了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地质特征,还标注了可能的油藏位置:“这些地方若能勘探,或能再出大油田”。 写完信,他又给母亲写了张字条:“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然后吞下一整瓶安眠药。 第二天,母亲发现他时,他手里还攥着那封未寄出的“找油信”。 三天后,母亲在同一张床上,留下“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追随父亲而去。 1991年,谢学锦把父亲的“找油信”和构造图,交给了大庆油田陈列馆。 那时,黄汲清已经在回忆录中为父亲正名,“大庆油田发现归功于谢家荣陆相生油论”的说法,终于被认可。 开馆那天,谢学锦站在父亲的展品前,对着前来参观的地质学生说:“你们爷爷一辈子就想给祖国找油,这些信和图,是他留给你们的‘寻宝指南’。” 有学生问他“谢老后悔吗”,他摇头:“你爷爷说过,能为祖国找油,死也值了。” 如今,谢家荣的“找油信”和构造图,在大庆油田陈列馆里静静陈列。 每年清明,都有地质工作者来这里献花,对着展品轻声汇报:“谢老,塔里木油田又发现新油藏了,您的理论没错”;“松辽盆地又打出高产井,没辜负您当年的坚持”。 谢学锦虽已近九旬,仍会带着父亲的手稿去高校讲课,把“陆相生油论”的故事讲给年轻一代听。 那封未寄出的“找油信”,字迹虽已泛黄,却像一盏灯,照亮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路。 有位科学家,哪怕身处黑暗,心里装的始终是祖国的地下宝藏; 他的生命虽已落幕,却用手稿和信念,为后人留下了寻找光明的方向。 信源:面对不敢面对的历史 ——缅怀“文革”中被逼自尽的地质学家——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