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婚之夜,男人图女人的身子,女人却盼男人早点死。半夜,女人悄悄跑到男人工作的矿山,埋下诅咒的纸,只要男人出事,她就能拿到抚恤金。哪知男人真的遇难,面对巨额抚恤金,贪财的女人却一分没拿。 这故事的主人公,叫她刘翠兰吧。上世纪90年代,一个被父母用几头猪的彩礼,嫁到山西矿区去的女人。她男人叫李大壮,人如其名,膀大腰圆,除了下井挖煤,脑子里就没别的事。 他们的婚房,就是矿区边上那种土坯房,风一吹,墙上的报纸就哗哗响。新婚之夜,李大壮一身酒气,眼里放着光,那光刘翠兰懂,是欲望。但刘翠兰心里是冷的,比矿井下的石头还冷。她不是嫁给一个人,是嫁给了一座山,一座随时可能塌下来的煤山。 那时候的矿工,说白了就是拿命换钱。今天还一起喝酒吹牛的工友,明天可能就成了一墙之隔的遗像。刘翠兰的爹,就是个老矿工,最后人没上来,只上来半个安全帽。所以她怕,怕得要死。她恨,恨这种看不到头的日子。 这种恨,慢慢就扭曲了。她开始盼着李大壮出事。这不是因为她恶毒,而是因为这是她唯一能看到的,逃离这座大山的“机会”。 拿到抚恤金,回娘家,或者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于是,她在一个没月亮的晚上,偷了李大壮的一根头发,用红纸包着,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他的生辰八字,埋在了矿区的废渣堆下。那不是诅咒,那是一个绝望女人给自己许下的“愿”。 三个月后,矿上瓦斯爆炸,李大壮的名字,出现在了遇难名单上。 矿长带着人来送抚恤金,厚厚的一沓“大团结”,足足三万块。90年代的三万块是什么概念?北京那时候一套小院子,也就这个价。所有人都觉得,刘翠兰这下熬出头了。 可刘翠兰看着那笔钱,就像看着一堆烧红的炭,哆嗦着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我不要。” 在场的人都懵了。她疯了吗? 她没疯。恰恰相反,在那一刻,她比谁都清醒。 咱们聊到这,暂停一下。你可能会想,这是人性的光辉?是良心发现?我觉得不全是。这是一种更原始的恐惧,是对“血钱”的恐惧。 钱这个东西,很奇怪。它能买来一切,但它也有自己的“气味”。用汗水换来的钱,花着踏实。但用人命,尤其是被自己“盼”来的命换来的钱,它会烫手,会咬人。 刘翠兰埋下的那张纸,就像一个心魔。当“愿望”成真时,那笔钱就不再是钱了,而是她杀死丈夫的证据。她拿了,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凶手。这份心理负担,比贫穷本身要可怕一万倍。 刘翠兰她代表的,其实是那个时代无数矿工家属的缩影。她们的生活,就是一场赌博。男人下井,是赌命;女人在家,是赌明天。 那时候的煤矿安全生产,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根据一些解密的行业档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咱们国家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一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十倍。有时候一个大矿难,一个村子的青壮年男人就都没了。剩下的,就是一群寡妇和孤儿。 所谓的“抚恤金”,在当时更像是一笔“买命钱”。 给了钱,这事就算了了。这背后,是对生命的漠视和践踏。刘翠兰不要那笔钱,也是在用自己最卑微的方式,对抗这种漠视。她是在说:我男人的命,不是这三万块钱就能打发的。哪怕,她曾经巴不得他死。 这事儿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当她真的可以用钱来衡量一条命的时候,她才发现,命是没法用钱来衡量的。 咱们再把视线拉回到现在,现在社会,我们很少再见到刘翠兰式的悲剧了。安全生产标准高了,保障制度也健全了。但那种“诅咒”和“期盼”,换了种形式,依然存在。 你刷刷手机看看,多少年轻人在网上转发“锦鲤”,希望能“一夜暴富”?多少人投身币圈、股市,用全部身家去赌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这和刘翠兰埋下的那张红纸,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一种自己无法掌控的、偶然性的事件上。这背后,是同样的焦虑和对现实的无力感。 刘翠兰赌的是一条人命,她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守住了心里的底线。而现在很多年轻人,赌上的是自己的未来和信用,一旦输了,面对的可能就是一辈子都填不平的坑。 从盼着丈夫死,到拒绝巨额抚恤金,刘翠兰这个女人,其实给我们上了一课。 她让我们看到,人性是多么的复杂。一个贪财的人,也可能会被良知唤醒;一个绝望的人,也可能在最后关头选择尊严。 她让我们明白,有些钱,拿了,可能会毁掉你的一辈子。 据说刘翠兰没要那笔钱,在矿上给李大壮守了三年孝,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没人知道她去了哪。 她的人生,从一场错误的婚姻开始,以一场人命的代价终结,最终,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获得了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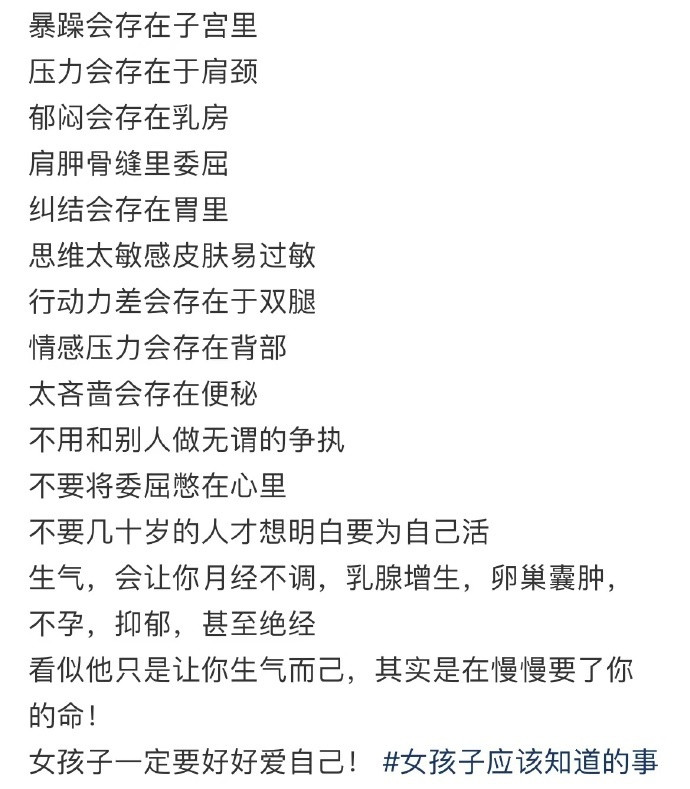






用户18xxx42
写的什么狗屁文章,既然知道嫁旷工危险,为什么要嫁?刚开始又想老公出事收抚恤金,后来又说不要